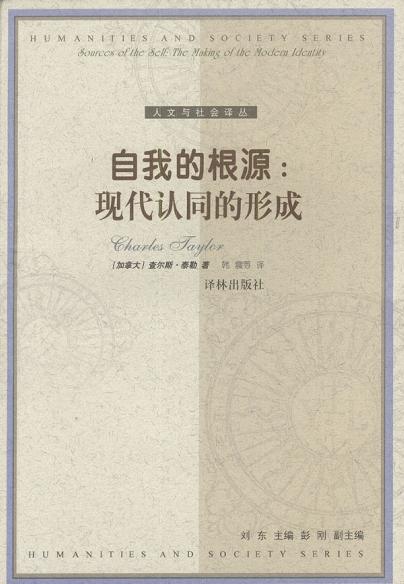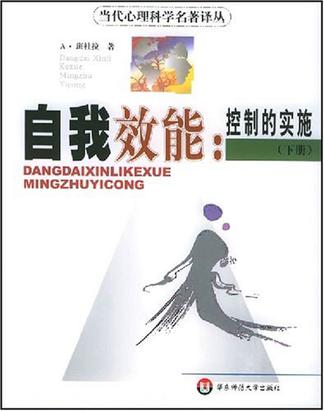自我的根源
(加)查尔斯・泰勒
简介: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社群主义主将查尔斯·泰勒的代表作,被誉为“近二十五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本书讨论了整个西方思想关于自我、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表达的作用等方面的观念史,勾画出现代性自我形成的过程。本书认为现代人继承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观,是现代性境遇中自我把握或定义“善”的结果。
序 言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一度陷入困境。这件事花了我数年时间,而且对于这本书应当写些什么,我也屡次改变主意。这种情形持续了很多年,对应该如何切入问题,我曾数次改变看法。这部分地是由于熟知的原因,好长时间内我吃不准我想说什么;部分地是由于好高骛远的进取心本性,即试图明确表达和写出现代认同的历史。用这个术语,我想标示出整个系列的(大部分未表述出来)关于什么是人类的主体性的理解:这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
但是,我也想表明: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这种认同的理想和禁令——使什么突出和使什么遮蔽——是怎样形成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认识论和我们的语言哲学的。被假定为从对某种自我既没有也不应当闯入的领域的严肃考察所取得的学说,实际反映出来的那种帮助我们构成我们这种认同的理想,要比我们认识到的多得多。我认为,这显然适用于从笛卡尔到奎因的表象的认识论。
另外,我们的认同这幅肖像注定要用做现代性新理解的出发点。这就是说,这个问题由于已经包含近三个或四个世纪的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并且因某种原因使这些变化进入焦点,继续使我们着迷。诸如福柯、哈贝马斯和麦金太尔这样主要的当代思想家们的著作,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其他人,尽管没有明确地谈及这个问题,也以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假定了问题如何而来的某种图式,即使这是对待过去的思想和文化不予考虑的一种态度。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着迷。如果不能掌握这一历史,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自己。
但是,我发现我本人对当今流行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并不满意。有些是乐观的,以为我们正在攀登新的高原;另外的观点展示了一幅衰退、失落、遗忘的画面。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不正确的;两方面都忽视了我们境遇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抓住那些给我们现时代以特征的伟大与危险、宏大与卑微(grandeuret misere)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点。要理解现代认同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首先是要理解,就我们所有人都试图摆脱它来说,我们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其中;其次是看到,我们围绕着它所作的那些左右摇摆的片面性判断是如何肤浅和偏颇。
但是,我认为,除非我们弄清了关于自我的现代理解是如何从人类认同的较早情景中发展而来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本书试图通过描述其起源,来界定现代认同。
我们把注意的焦点放在认同的这三个主要侧面上:首先,现代的内在性,即作为带有内部深度存在的我们自身的感觉,以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联结性概念;其次,由现代早期发展而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作为内在道德根源的表现主义本性概念。在第一侧面中,我要对从奥古斯丁到笛卡尔和蒙田,再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进行探索;在第二部分,我的论述从宗教改革起,经启蒙运动,直到它的当代形式;而在第三部分,我的描述从它在十八世纪末叶的起源开始,经过十九世纪的演变,直到它在二十世纪文献中的表现形式。
第二到第五编,是这本书的主体,它阐明了发展着的现代认同的这个图景。论述是分析和编年的结合。但是,因为我论述过程的整个路线是要标明自我感和道德视界之间、认同与善之间的联系,我感觉到,在没有关于这些联系的某些初步讨论的情况下,我就不能进行这项研究。由于在当代居支配地位的道德哲学试图掩饰这一联系,所以,这项研究看起来更有必要了。为了弄清它们,我们必须从多种意义上,正确评价善在我们的道德观点和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准确说来,这却是当代道德哲学所极难于接受的。因而这本书的开篇部分就试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自我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状况,在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我随之加以利用。那些十分厌烦现代哲学的人,可以跳过第一编;那些厌烦历史的人,如果不经意地拿到了这部著作,也就不必读其余的部分了。
正如我已指出的,对于我们能够以比通常更富有成果和更少片面性的方式把握现代性的现象来说,整个研究只是一个序曲。在这本部头已经够大的书中,我没有篇幅再描绘这些现象的全面的替代性图景。我将把这个任务,连同对现代认同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联系的分析,留给以后的著作。但是,我试图在结论一章中阐明,什么样的结果从浮现中的现代认同的故事中产生出来。简明地说,就是这种认同在道德根源中比它的谴责者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但是由于其最热情的辩护人贫困的哲学语言,这种丰富性被弄得看不见了。现代性急需从它的最无条件的支持者那里解救出来——一个文化史上或许不是没有先例的尴尬处境。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在结论中,我试图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实施拯救是重要的,甚至是迫切的。
这本书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在此期间与全灵学院及整个牛津大学,还有麦吉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兰克福大学及耶路撒冷大学的同事们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这些同事包括詹姆斯·塔利、休伯特·德雷福斯、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简·鲁宾、于尔根·哈贝马斯、阿克塞尔·亨尼思、米夏·布鲁姆利克、马丁·洛—贝尔、豪克·布伦克霍斯特、西蒙·钱伯斯、保尔·罗森堡、戴维·哈特曼和居伊·斯特劳姆萨。受劳伦斯·弗里曼和蒙特利尔本笃会修道院的邀请而进行的“约翰总追思”讲座,为我提供了阐述我正在试图集成的现代性图景的宝贵场合。而且随后的讨论,也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如果没有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度过的一年,我就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我非常感谢克利福德·格尔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和迈克尔·瓦尔策,这既是因为这一年的研究,也是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在研究所的不可比拟的气氛中所进行的有价值的讨论。我同样想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是它提供的资助使这一年的研究成为可能。
我感激加拿大文化委员会资助我伊萨克·基拉姆研究奖金,它使得我可能享受另外一年的假期。事实证明这是极端重要的。我也感谢麦吉尔大学准予学术休假,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提供学术休假奖金,它们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手稿。
麦吉尔大学向我提供了帮助修改手稿和准备索引的研究资助,我谨致谢意。
我非常感激梅特·约尔特对手稿的评论。我应当感谢阿尔巴和米丽亚姆的宝贵的建议,感谢克伦和比茜亚使我接触了有关存在的不熟悉的方面,还就更新了的实用主义感谢比塔。我还应当感谢葛蕾塔·泰勒和梅丽莎·斯蒂尔,是她们帮助我准备了手稿的最后定本以便出版,也要感谢旺达·泰勒所做的校对和索引。
我感激代表迈克尔·B.叶芝和麦克米兰伦敦有限公司利益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和A.P.瓦特股分有限公司允许我从W.B.叶芝的《在学童之间》引用一些诗行,此书重印自理查德·芬纳兰编的《新版W.B.叶芝诗集》,一九二八年版的版权属于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一九五六年的修订版版权属于乔治·叶芝;感谢新方向出版社准许我从《人物:伊兹拉·庞德诗集》引用伊兹拉·庞德的《在地铁车站》,此诗集一九二六年的版权属于伊兹拉·庞德,由新方向出版社重印(1949);感谢费伯—费伯有限公司及漫话印书馆准许引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最早文本的一节诗,其一九四年版本的版权属于W.H.奥登,重印自爱德华·门德尔松编的W.H.奥登的《英语奥登:诗歌、随笔和戏剧作品,1927—1939》;还感谢漫话印书馆准许我引用斯蒂芬·米切尔翻译的R.M.里尔克的《豹》,其一九八二年版本的版权属于斯蒂芬·米切尔,重印自《兰纳·玛丽亚·里尔克诗选》。引用策兰《铭刻》(“Weggebeizt”)、《无半截树林》(“KeinHalbholz”)和《光线》(“Fadensonnen”)中的诗句,经苏尔坎普·魏拉格的准许重印自《选集》(Gesammelte Werke,II)(1983);这些诗的英译本一九七二年、一九八年、一九八八年的版权属于迈克尔·汉堡,经佩尔塞出版社和铁砧诗歌出版公司的准许,重印自《保尔·策兰的诗》。引用夏尔·波德莱尔的内容出自《恶之花》,其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年的版权属于新方向出版社,经新方向出版社的允许而重印。所摘塔杜茨·鲁热维奇的《在生活中间》和奇比纽·赫伯特的《石头》的内容,经作为万丹—道布尔戴—德尔出版集团一个分支的道布尔戴出版社的允许,引自切斯瓦夫·米沃什选编和翻译的《战后波兰诗歌》,其一九六五年版本的版权属于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 后 记
查尔斯·泰勒的这部著作在西方有极大的影响,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时,美国教授曾向我推荐此书。回国后,我也曾撰文介绍泰勒的思想。因此,当刘东先生和刘北成先生让我翻译此书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下来。粗略地阅读时,我只为泰勒对“现代性”的深刻分析所吸引,但在翻译过程中,才意识到自己承担了一个几乎是无法胜任的重担。泰勒的著作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文字也非常晦涩难懂,并且在行文中夹杂大量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词,这增添了很多的困难。好在有许多朋友帮忙——如杨共乐先生和郭小凌先生,替我译了全部希腊语词——才勉强完成了这个任务。
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两次阅读了译稿并就译稿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清华大学的彭刚先生为此书的翻译、出版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前言、第一编、第二编、结论和索引部分,由我本人翻译,第三编由乔春霞、彭立群翻译,第四编由李伟、彭立群翻译,第五编由王成兵翻译,三、四、五编的法、德语部分也由我来翻译,全书由我来统稿并校译,有些地方作了较大修改。因此,此书出现的错误,首先应由我来承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韩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