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泥湖年谱
《乌泥湖年谱》简介: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长江水利规划设计院的乌泥湖宿舍,这里的十幢小红楼里居住着一群或从海外学成归来、或出自国内名牌学府的水利专家,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下,为着举世罕见的三峡工程而来。他们一个个才高八斗、神采飞扬、温文尔雅、自命不凡,期待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十年中,他们的性格一点点地消损,他们的豪情一点点地泯灭,他们的良知被逼到灵魂的死角,他们的傲气被扫荡殆尽。不仅他们向往为之献身的三峡工程遥遥无期,他们自己也早已风华不再、心绪黯然。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他们更是如同惊弓之乌,心惊胆战、无所依傍,只有听凭极左政治的狂风暴雨任意摧残。 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对于许多读者并不陌生,例如,苏非聪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划为“右派”,他清高而又脆弱的个性使他无法忍受这不白之冤、飞来横祸,他断然辞职,举家返口农村,娇柔的太太、弱小的女儿和他一起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林嘉禾善良正直、教子有方,但他的“右派”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不被信任,大学毕业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更令他雪上加霜、百日莫辩。这个诚实单纯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身陷囹圄。党员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皇甫白沙,也未能逃脱“右派”的命运。他的儿子皇甫浩同样因父亲的“问题”不被大学录取,只得到偏僻山区插队。他在劳动中被牛踢伤,因救治不当而死。皇甫白沙曾经对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坏的预料,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当儿子的死讯传来,他痛不欲生,悲愤地想,我是杀死儿子的凶手,当年我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主持正义呢?我没有失去良心,却断送了自己的儿子!小说的主要人物丁子恒,一向小心翼翼、谨慎少言,又蒙命运垂青,侥幸通过了一场场劫难,保全了家小,保全了自己。然而在小说结尾的1966年,当他看着绝望的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他感觉自己也己经死去。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活着与死去有什么两样? -

风景
《名家中篇小说典藏:风景》主要内容:我极其感澈父亲给我的这块血肉并让我永远和家人待在一起。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听见他们每个人都对着窗下说过还是小八子舒服的话。我为我比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安宁而忐忑不安。 -

春天来到昙华林
昙华林,武昌旧城一个汇聚了历史所有沧桑的地方,单是这个名字,就可以窥见光阴留下的烙痕。而方方,居武汉四十余载后,终于将目光渐渐聚集于此,一长串故事在这个让人无法不感怀的斑驳背景下上演,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春天来到昙华林》,方方最新的一篇小说。读过眼前总掠过一幕幕画面,这画面与《断臂山》片首那撩人心魄的吉它声混合着,冲击着,竟让我一瞬间无法自拔。很相似的创作手法,不动声色地铺陈,象小溪缓缓地流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汹涌却无法安寂。爱,静得有些忧伤,一丝丝沁入骨髓,随生死终完成一生的相陪。爱与生死,两条线,交织着汇集,定格于一场宏大的死亡祭奠。 文章开始就是一个平常却打动人心的画面:春天,老墙上的一茎草芽,炉子的青烟,华林母亲熏出的泪,一个个镜头摇过,平静地掠夺着心底的震颤。而结尾处,同一个场景再次出现,一岁翻过,物是人非,母亲的“泪流得更长”,心底的震撼更巨。但于常人,没有切肤的伤痛,“人一走,记忆也走了,而且一去不返”,“只有春天年年记得来一趟”。 华林生于昙华林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正是昙华林可以让他用镜头代替着语言,用胶卷透视着心灵。嘉诺撒教堂,唇齿间摩擦过,韵味悠长的一个名字,象昙华林一样有着某种异域风情的诱惑。或许正是一个象征,从华丽到废弃,从绚烂到悄无声息,如风雨剥蚀后生死之光影定格。然而,也是昙华林,这个如今“杂乱而肮脏,满目疮痍”的地方,让华林只能在逼仄的空间里成长,只能更为关注的是内心深层的东西。他是瘦小的,一切向内,所以才会如此热爱着摄影,从一个小小的取景框中探视着人生,观察着世界。 相比昙华林,清江是如此地美丽和开阔,土家人豪放的秉性也不足为奇,所以谭华霖是阳光且阳刚,健康而干净的,象正午一览无余的骄阳,光芒万丈。是的,光芒万丈,华林在心里一直用着这个词,所以他心里才会滚过无法自持的激动。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华林在发现自己心中的秘密后,内敛而煎熬,甜蜜又痛楚。一切都是淡淡、徐徐地前进着,从春的明媚到冬的惨淡,按部就班,一一展现。 月夜,清辉泻了一地,朦胧,模糊,悸动,泪流。爱的真相和盘托出,等待的是两尊雕像,静默而迷离。阴影里,注定一切不能成真,惆怅下,一切疼痛变得不堪。这是两个东方人的断臂山,更深沉,更无言。这也并不是断臂山的翻版再现,没了律动,更让人心痛。躲避与退缩,爱终于翻下山坡。 于生死,我们总是畏惧的。华林在幼年时痛丧爷爷时就种下了一个心劫,直到来清江后,遭遇土家人迥然的生死观,才慢慢开始改变。土家人说:“人不是活就是死,只有这两条路。走不通这条就走那条。”所以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所以死亡可以用“跳丧”渲染到极致。说这话时,谭华霖正与华林走在雨夜谭水垭湿滑的小径,“声音大得压过了江水拍岸的涛声”。华林却说:“人是有感情的,就算走另一条路,走了就等于永别,感情上会痛的。” 这是两个民族对于死亡不同的认知和碰撞,我们汉族人总把死亡当作永别,而许多民族会把死亡认定为只是去了另一个相通的世界,所以面对时,我们会把悲伤放大到天黑地暗,而他们会用最原始的姿态热热闹闹地迎接,两种心态,其实影映在生活中也是天地之别。但死终究是令人愀然的,华林死了,谭华霖号哭得惊天动地,他突然明白:“死人并不快活。死人也绝不是从这一界到另一界那样简单。”那么死,究竟是什么?究竟该以怎样的面容相对才算真正的从容? 跳丧,小说中的高潮,篝火熊熊,鼓点阵阵,歌师的喊唱狂放震心,尖利或粗犷,象刀子一声声刺痛在心里。爱缠结着死亡,在山啸般狂放中渲染到极高处。眼前晃过歌师翕合的嘴唇,谭华林额上的汗滴,华林太师椅上安详的微笑。但我心里翻滚着的其实是华林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一辈子跟着你。 光阴是一去不返绝不重复的,只留清江水缓缓流向远方。爱是让人暖洋洋的东西,即便生死的距离。 -

桃花灿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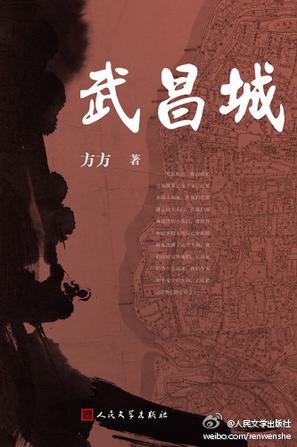
武昌城
《武昌城》叙述的是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一段历史。小说以两个青年人陈明武和马维甫为主线,讲述战争对老百姓生活的摧毁,以及战争中人的成长、毁灭和重生,讲述一段城墙永久的消失和一段历史永久的定格。与书写乱世人生的其它小说不同,方方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自在状态的世俗烟火,没有以回望的姿态对旧日的时光进行历史的喟叹,相反,小说的叙述平实而冷静,掩藏了历史的价值判断,而充分尊重其模糊性:所有的毁灭中都包含着重生,而所有的重生又都孕育着死亡的因素。因而,《武昌城》的故事反而成了一个浑然自在的天成状态,而所有人对于变故来临而产生的应激反映都只不过是寻常的逻辑,都包含了世代的永恒真理。或许,小说的故事发展和人物逻辑都略显老套,但其记录历史的方式、解读历史的态度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贯穿了历史与现实的潜在规则。 -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了这样一个“蚁族”艰辛奋斗的悲剧故事:山沟里的涂自强是家乡头一个考上大学的贫寒农家子弟,带着村民们盼他“当大官”光宗耀祖的殷切期望,带着乡亲们用零钱帮助凑上的部分学费,他一路徒步打工来到武汉读书。大学四年,涂自强一方面勤工俭学,一方面为节省用度不敢回家。正在他拼命苦读想要考研时候,家乡传来噩耗:涂自强父亲因为村子在上面“没人”,遭遇祖坟被修路破坏的变故,急气而亡;母亲因老屋被暴雪压塌,屋毁受伤急需照料——涂自强只得放弃考研,将母亲接到武汉同住,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他四处奔走谋职,艰难度日,过着典型的“蚁族”生活。由于母亲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谋生又历尽艰辛,涂自强积劳成疾,在安顿好母亲之后默默死去。 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