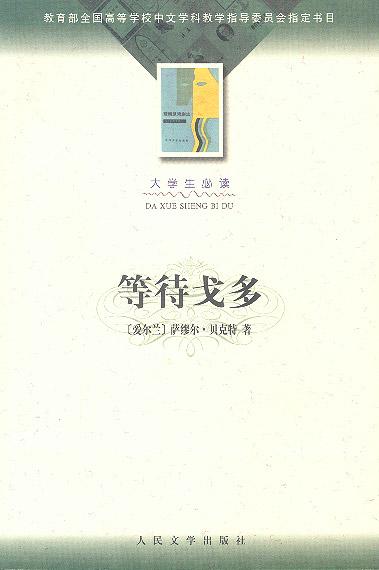贝克特肖像
(英) 詹姆斯 诺文森 文,约翰 海恩斯
1953年,《等待戈多》在巴黎首次公演,观众反应相当冷淡。评论家玛丽亚·曼内斯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比它更糟的了。”甚至有演员演完后说:“我一点都不懂。”但是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再加上罗伯·格里耶等名家的推荐,傲慢的巴黎人接受了这一反戏剧的探索,这部戏剧接连上演三百余场,轰动一时。
事实上,巴黎人在鼓捣“贝克特在卡赛尔”国际研讨会,把贝克特在德国的细枝末节拿出来磨粉切碎时,他们已经是在吃利息了,而中国人却还没有把贝克特存入银行。1983年,《等待戈多》首演过去30年之后,国人才开始从一本《等待戈多》的译作认识了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爱尔兰作家。
上世纪80年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建斌偷偷地把两本书放在兜里,随时拿出来翻翻。一本是《哈姆雷特》,另一本就是《等待戈多》。事实上,等待戈多的不仅仅是陈建斌,那时文学青年大多在不约而同地等待着自己的戈多。
林兆华说:“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等待亦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他说,那时他也在等待戈多,他的戈多,有一段时间是房子,又有一段时间是演出的机会,还有的时候只是等待本身。“贝克特是典型的爱尔兰作家,从小接受传统严苛的宗教教育,天然导致了他极端的反叛,所以他作品中的颠覆力量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冲出一切桎梏的心理不谋而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认为。
“这些年,贝克特很少被中国读者接受,这和他的译作比较少有直接关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介绍说,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等待戈多》之外,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收录了贝克特的《逐客自叙》,还有就是《美好的日子》、《终局》,这两部剧作的翻译都只在《外国戏剧》这样的专业杂志上露面。
尽管如此,在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年轻导演们还是从《等待戈多》中看到了一丝丝曙光,“国内先锋戏剧标志性作品《车站》是被《等待戈多》刺激出的,这一点,谁也无法回避。”北大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罗田表示。
孟京辉的贝克特情结
1991年夏天,很热。在中央戏剧学院里,200多位同学穿着印有贝克特瘦峻面孔和高耸灰发的T恤衫,在人群中他们显得格外突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神气的文化优越感。
中央戏剧学院四楼的小礼堂里,《等待戈多》终于上演了,孟京辉自信地说:“在此之前,从没有导演这样冷静地为国人介绍过贝克特。”孟京辉说这句话是有根有据的,早前上海演出过《等待戈多》,但却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解释贝克特,有看过沪版演出的人回忆说“从导演动机就很可疑,用现实主义解释不了象征主义的。”为尊重原著与译者,孟京辉请施咸荣为剧作担任文学顾问,施咸荣还为全体演员上了一下午的课,与他们分享自己对《等待戈多》的理解。
“不华丽,不绚烂,残酷,诗意,幽默,还有暴力,包括语言的暴力和暴力本身的暴力。”孟京辉以如上的词语概括他的《等待戈多》,“尽管如此,这些风格都是在不违背贝克特主题基础上的变化。”孟京辉强调。
包括余中先在内的很多观众在经过数场戏剧的洗礼后,除了依稀地保留一点点震惊,大多已渐渐淡忘这场轰轰烈烈的演出,但有一个人却以另一种方式保持着自己对这场戏的怀念。这个人就是《等待戈多》当时的主角胡军。《等待戈多》后来又在柏林演出过四场,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胡军默默地走上舞台撤台,他将布景———巨大的印有三女神的门帘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自己的包里。直到有一天,孟京辉在胡军家的墙上才意外地与它重逢。
1998年贝克特与中国的热恋期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次真正意义上演出的《等待戈多》,其影响力却远远小于它的号召力。贝克特与中国的热恋期直到1998年才到来。
《等待戈多》似乎是一块有着魔力的试金石,但凡是导演,就无法逾越也无法回避。
林兆华执导了《三姐妹·等待戈多》、任鸣执导了女性版城市版与时俱进的《等待戈多》。前者在令国内外剧评家震惊之余也赢得一定的称赞,“复调的结构将契诃夫的传统与贝克特的颠覆交织纠缠。”而后者则让评论界哗然,被认为具体的指向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完全脱离了贝克特的初衷。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03年,传来一个令人期待的消息,孟京辉将执导100个人“等待戈多”。遗憾的是,由于非典,此戏被无限期地推后。
“将人类孤独的标本泛滥成群众运动,一定是件充满想象力和创作力的事情。”人们期待着,孟京辉也期待着,有的时候他还会找出当年的录像带回味当初的排练。“布景是课堂,开始,大家一起扫地……最后,舞台上一个人都没有。”孟京辉回忆着。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戏剧界就不再有什么人对贝克特感兴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了热情,也许是太多新的事物在吸引大家,应接不暇吧。”孟京辉说。
迟到的《贝克特选集》
贝克特百年诞辰之际,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5卷本《贝克特选集》,这是国内引进贝克特的作品规模最大的一次。策划人陈侗介绍,这套文集收录了贝克特定居法国巴黎后所有用法文写作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文集最重要的是收录了贝克特用法语写就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名者》。这三部小说打破传统,淡化情节人物,只有絮絮叨叨的内心独白。这种写法直接导致了法国新小说派的文学实验。
余中先担任了《贝克特选集》的总审校,他称这项耗时7年的工程为补课。“这些书不可能是畅销书,但它有助于梳理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谱系。一砖一瓦是建不起长城的,至少得花一段时间,一定规模,再回头看,就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余中先坦言翻译的难度很大,“贝克特的主题:荒谬、无奈、流浪、残疾、梦呓反复出现。
而这些主题在萨特、加缪的作品中也有所指,但贝克特最为突出。这是因为他的文学语言、戏剧语言将荒诞的内容与形式做了高度的统一。”意外的是,文集的出版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表示,贝克特写作中无形的文字游戏,包括翻译者都很难理解,一般读者更难体会到阅读的愉悦感,读多了还会变得神经质。
他举例,“在文中他会将god与dog放在一个句中,但上帝变成狗的妙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孟京辉对此的看法是,无限的理解空间恰恰是贝克特的魅力,有更多的人会将可能的意义无限延伸。
至于贝克特还会对当下中国产生什么余温,余中先认为,大概不会有什么影响了。“贝克特还没来得及和我们神交就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采写/本报记者 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