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收入22篇文章,大致以时间为序,以专题形式,论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各阶层与各时期国家权力的互动、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以后者更为精彩。 中国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非走这一步?《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正是通过回顾1903—1953年之间的农村社会历史,试图彻底厘清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和文化结构变迁的内在线索和发展方向。理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推进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隐秘的乡村
阿贝尔的记忆成就了一幅岷山乡村的“清明上河图”,他所描绘的不是诗意的田园生活,而是田园风光下乡村的痛疼和沉沦。在他的记忆里,乡村的一切,如同一幅幅图画……令人伤感的是,阿贝尔笔下的村庄在刚刚发生的5.12大地震中遭到严重地损毁,因此,他的文字已经成为“废墟”上的“档案”。 在阿贝尔笔下,青苔,水葵,草滩,惊梦,1976……这些建构一个人童年的事物,以语言自记忆呈现的时候已经是诗的意象了。诗性,包含了全部的隐秘。 在作者的记忆里,1976年的春天是隐蔽的土豆花、繁茂的扁谷草和隐约的饥饿。土豆花在龙嘴子,在短坑里。紫色。像鸢尾花,像蝴蝶……扁谷草在河岸上,像生错地方的水稻。碧绿。粗糙,富有纤维,非常适宜于水牛宽阔的舌头和机械的胃。我们的饥饿是一个秘密…… 一个人的出生地。河流,山脉,桑田,樱桃树,石墙,老木屋……都是原生态。如画,却带着阴晦,一种艳阳里的隐晦,甚至黑暗。一种失落的遗憾之美。这遗憾里,有时代的涂鸦。记忆与想象终究是要磨灭的。一切永恒只在文本——我们哲学与感官的虚无。 一个村庄的疼痛来自回乡者的气质,更来自村庄本身的伤口与感染。 “我的父亲死了,但癌还留在这个村庄的泥土里。”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要到对岸去\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也涂改着我\我在流动”北岛的诗句成了作者在寂寞乡村生活的想象和憧憬:在有河流的出生地,对岸是一个人向往的唯一的天堂,其意义可以接近“彼岸”。向往也是逃离。 青莲,九寨沟,裸睡,江南,衰秋,北京……都可看成是对岸的种种。只是抵达之后发现,对岸之美已经是被瓦解的了。 -

法兰西乡村主义
法国的乡村,就如同一幅画卷:莫奈激情四溢的罂粟花;塞尚湛蓝明亮的高地;西斯莱和毕沙罗令人眼花缭乱的橄榄树和葡萄藤;以及披着彩虹的山峦、农舍、田庄…… 作者亲历法国各地的乡村、古堡,给我们带来了一次身临其境的视觉之旅。从城市的街道到乡村石子铺成的小路、从迷人的河边到漫山遍野丰富在望的彩色葡萄园、从醇厚的葡萄酒到那遥远的历史故事、从那一道道让人无限遐想的美食到当地热情、纯朴的人情风貌、从那严肃的历史故事到如今发生在乡村、葡萄园里的爱情故事……跟随这轻松的文字,让你真实地坠入法兰西的迷人的浪漫主义中去。 -

失落的乡村
当乡村遭遇城市化冲击,我们如何安放诗意记忆? 《天涯》杂志社编著的《失落的乡村》由韩松落、王十月、胡弦、安黎等当代名家用感性和诗意文字还原乡村记忆。 乡村,一个能够安置人的生和死、身体和灵魂的地方。它是中国人共同的故乡,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生存居所。 《失落的乡村》荟萃了几代人对于“乡村”的记忆与展望,既有对千百年来乡村自然生活的赞美和感叹,又反映了在当下城市化节奏不断加快的情境之下,乡村世界遭遇的冲击以及对人事逐渐消逝的留恋与无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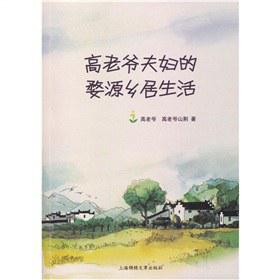
高老爷夫妇的婺源乡居生活
天涯社区4年热帖,讲述了中国版的“永远的普罗旺斯”——一对上海白领夫妇在婺源乡间的生活。 在越来越多都市人沦为房奴车奴卡奴的现代社会,他们放弃都市、耕读于乡野的人生选择,引来无数媒体关注,更赢得万千网友共鸣与热议。 《高老爷夫妇的婺源乡居生活》图文并茂的为我们展现了夫妻二人恬淡自然却充满乐趣的乡村生活画卷。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由高老爷执笔,后半部分为其妻所写,文字质朴自然,记录乡居生活的点点滴滴,平凡温馨,细节饱满而予人启迪。 这些文字与画面,如稻穗上洁净的朝露,如山间清新的晨风,亦如枝头小鸟的自由鸣唱,将给我们视听和心灵来一次美妙的涤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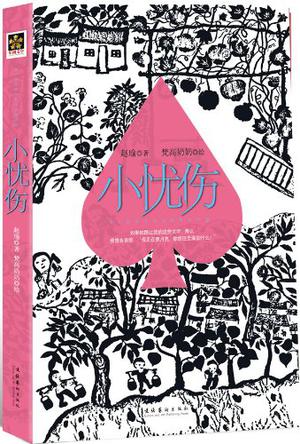
小忧伤
《小忧伤》包括23章趣事,288节时光片段,汇集了70、80后的所有童年情结。玉米地、老水井、牛、磨房、池塘、雪地,这是我们的绝版家园;食物、游戏、电影、动物们,还有恶作剧,童年里到处铺满了欢乐。“我”是一个活泼又善感的孩子,喜欢在一群顽童中做领袖,聪明、爱做梦,很淘气却又有点羞涩。有时觉得孤单,有点小忧伤,但底色都是温暖。 作者用聪慧的眼光,本真的语言,原汁原味地写出了乡村岁月包裹的童年。摩挲这些小而又小的事件,旧日时光恍如梦境。梵高奶奶的36幅画作,朴拙而充满想象力,带着清香的泥土气息,惹起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