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魔鬼作斗争
简介 《与魔鬼作斗争》论述了三位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生活历程,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精神导师倾向,在生活中总是从精神上苛求自己,追求人类精神自由、完美的巅峰状态。 本文选自其中论述尼采的篇章《没有其他人物的悲剧》。 没有其他人物的悲剧 获得存在之最大享受意味着:危险地生活。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是一出独脚戏:在他的一生这短暂的场景里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在雪崩一样坍塌下来的每一幕里,这个孤独的战斗者都独自站在自己的命运那雷雨交加的天空下,没有人站在他身旁,没有人走近他,没有一个女性以温柔的存在来缓和那种紧张的气氛。所有的运动都仅仅由他发出也仅仅跌落回他:为数甚少的几个开始时出现在他的影子里的人物只是以无声的吃惊或恐慌的姿势陪伴他的英雄冒险,渐渐地像面对什么危险人物一样退却了。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近或完全踏入这个命运圈子,尼采总是独自诉说,独自战斗,独自忍受痛苦。他不对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人回答他。更可怕的是:没人听他的。 尼采的这出惟一的英雄主义悲剧没有人,没有搭档,也没有听众:但它也没有真正的舞台,没有风景,没有舞台布景,没有戏服,它好似在思想的真空领域上演。巴塞尔、南堡、尼斯、索伦特、西尔斯—马利亚、热那亚,这些地名并不是他真正的家,而只是他以燃烧的翅膀飞越的道路两旁空洞的里程碑,是冷冷的背景,无语的水彩。实际上这出悲剧的舞台布景一直只有一个:独自一人、孤独、那种让人恐惧的既无言也无回应的孤独,这种孤独像他的思想背负着的、在他的周围和头顶的一座无法穿透的玻璃钟,一种没有鲜花、色彩、声音、动物和人的孤独,一种甚至没有上帝的孤独,一种所有时间之前或之后的太初世界里的冷漠死寂的孤独。但是,使他的荒凉、孤寂如此可怕、如此恐怖而又如此荒诞可笑的是一种不可思议,那就是,这种冰川和荒漠一样的孤独在精神上竟然发生在一个美国化了的、有七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铁路隆隆电报嗒嗒、熙攘嘈杂的新德国,在一种平时总有一种病态好奇心的文化里,这种文化每年向世界抛出四万本图书,每天在上百所大学里寻觅问题,在上百所剧院上演悲剧,但却对这出发生在他们自己中间,发生在他们内部圈子里的最宏大的戏剧—无所闻,一无所知,一无所感。 因为正是在其悲剧最伟大的时刻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德语世界不再拥有观众、听众和证人了。起初,当他还是一个讲台上的教授,当瓦格纳的光芒还使他清晰醒目时,当他最初开始谈论时,他的话还能引起些微的注意。但当他越是深入剖析自己,深入剖析时代,他就越少引起反应。当他进行英雄的独白时,他的朋友们和陌生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他们被他那些越来越狂野的背景变换,被这个孤独者越来越狂热的激昂吓坏了,他们把他独自一人可怕地留在了自己命运的舞台上。渐渐地这个悲剧演员变得越来越不安,这样完全对着空无讲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像喊叫,越来越手足并用,只为能引起一丝反响,或者至少引起一些异议。他给自己的话创造了一种音乐,一种奔流汹涌、狄奥尼索斯的音乐——但没有人再听他的。他强迫自己演一出滑稽戏,强迫自己尖利地、刺耳地、硬生生地开怀大笑,他让自己的句子疯狂地跳跃。他插科打诨,只为了能用艺术性的愉悦来为自己可怕的严肃吸引听众——但没有人鼓掌喝彩。最后他发明了一种舞蹈,一种在刀光剑影中的舞蹈,他伤痕累累、流着血在人们面前表演这种新的致命艺术,但没有人能够领会这种叫闹的玩笑的意义和这种硬装出来的轻松背后那种身负重伤的激情。没有观众,没有反响,这出被赋予我们这个衰落的世纪的前所未有的精神戏剧就这样面对着空荡荡的长椅结束了。没有人哪怕稍加留意,这只在坚强的顶端飞速旋转的思想陀螺怎样最后一次庄严地跃起,最后蹒跚地跌向地面:“死于永恒之前。” 这种“与自己同在”、这种“面对自己一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活悲剧的最深层意义和惟一神圣的苦难:从来没有思想如此巨大的丰富、感情如此膨胀的疯狂面对世界如此巨大的空无,面对这种金属般难以穿透的沉默。他从来没福气得到一个出色的对手,所以这股强劲的思想意志只得“向自身挖掘”,只得借“挖掘自身”从自己的胸膛和自己的悲剧性灵魂中获取回应和异议。不是从世界中,而是在血淋淋的撕裂中这个命运狂人像赫拉克勒斯撕下内萨斯衬衫一样从自己的皮肤上撕下那种燃烧的热情,只为能够赤裸着站在最终真理面前,站在自己面前。但是包围这种赤裸的是怎样一种寒冷、围绕这种精神的高声呐喊的是怎样一种沉默、覆盖这个“谋杀上帝的人”的是怎样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的可怕的天空,现在,由于没有对手发现了他,他也再难找到对手,他只好向自己进攻,“毫不留情地做认识自我的人、做自己的刽子手吧!”被自己的魔鬼驱逐出自己的时代和世界,甚至驱逐出了自己的本质的最边界, 被不知名的狂热震动, 在锐利冰冷的寒箭前颤抖, 我被你追逐,啊思想 你这不可名状的、蒙面的可怕思想!他有时以极度惊恐的目光回望时会不寒而栗,因为他发现他的生活已经把他抛离所有生存着的和曾经生存的东西那么远了。但这样一种超强力的起跑已经无法再回头:他在完全清醒的意识下,同时又在自我陶醉的极度兴奋中去履行那种由他热爱的荷尔德林为他预示的恩培多克勒的命运。 英雄的风景中没有天空,宏大的演出没有观众,沉默,越来越强大的沉默包围着精神孤独的可怕呐喊——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要不是他自己极度陶醉地对此说“是”,且为它的惟一性而选择并热爱这惟一的残酷,那我们一定会把这场悲剧当做大自然众多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之一来憎恶。因为他凭着最深刻的悲剧直觉自愿地、清醒地从安全的生活中建立起这种“特殊的生活”,并且单凭勇气的力量向众神发出挑战,要在自己身上“试验人类在其中还能生活的危险性的最大强度”。“你们好,魔鬼”尼采和他的语言学朋友们在一个大学生式的欢乐的夜晚用这样一句亵渎神灵的欢呼宣告了自己的力量:在鬼怪出没的午夜时分他们把满杯的红葡萄酒洒向窗外巴塞尔城熟睡了的街道,作为向那些看不见的幽灵的祭礼。那只是一个用深刻的感觉来推动自己的游戏的绝妙的玩笑:但魔鬼们听到了这声欢呼并跟上了这个邀请它们的人,直到这个一夜之间的游戏变成了一场命运的壮丽悲剧。但尼采从来没有阻止过这种可怕的要求,这种要求有力地抓住了他并且带着他飞驰:锤子越是有力地凿在他身上,他意志的坚硬石块就越发出愉快的声音。在痛苦这块烧得通红的铁砧上,随着每一次双重的敲打,那用以给他的精神包上一层坚硬的盔甲的公式被锻造得越来越结实,这是“人类之伟大的公式,对命运的爱;即人类不想要别样,不想向前,不想后退,不想躲入任何永恒之中。对必然的东西不仅仅是承受,更不是隐瞒,而是热爱”。他对力量这种热情的爱的歌唱声以奔放的气势压过了自己痛苦的喊声:瘫倒在地上,被世界的沉默压碎,被自己撕碎,被所有痛苦辛酸浸蚀,他却从没有举起过双手,命运最后只好放弃了他。只是他还祈求更多的东西,更强烈的苦难,更深刻的孤独,更完全的痛苦,祈求自己能力的极大丰富;他不是在抗拒中,而是在祈求中,在英雄一般的庄严祈求中举起了双手:“被我唤作命运的我心灵的天意啊,你在我之中在我之上请保护我,留给我—个伟大的命运吧!” 谁知道如此伟大地去祈求,谁就会被听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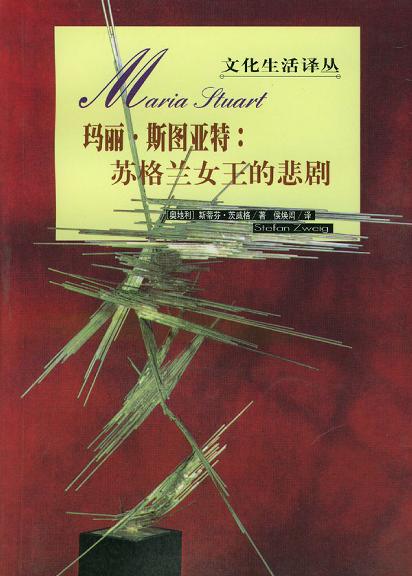
玛丽·斯图亚特
任何一件文献,尽管它的悠久历史经过周密的考证,尽管它是货真价实的归档材料,却保证不了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允。同一件事,在同时几位史家的记载中,却有南辕北辙的出入。此种情形在玛丽·斯图亚特一例中似乎尤为彰明较著。在这里,每有谴责,必有辩解;每有一个“是”,必有一个“不”同它颉颃,两者各有文件为证。 真理和谎言共生,事实和虚构并存,难解难分,以致实际上每种观点都可以做到言之成理。如果你想证明玛丽·斯图亚特预闻了谋杀亲夫,有几十份证词可以供你使用。如果你想支持对立面,证词也不成问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的颜料。传流至今的材料既是如此芜杂,倘若再掺入政治偏见或者民族主义,那就更成了彻底的蓄意歪曲。人处在争论生存还是毁灭的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之间,都抗拒不了诱惑,非得参加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确认此是而彼非,或诋毁此而赞美彼。这是人的天性。倘若像这桩公案,列位著作家多半各有归属,分别属于交锋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是势所必然。总之,新教的著述者把一切罪过都诿之于玛丽·斯图亚特,而天主教徒却归罪于伊丽莎白;英格兰人除了少数例外,都把玛丽描绘成杀人犯,而苏格兰人则把她说成是受害者,一身清白,横遭卑鄙的诽谤。关于“首饰箱信件”,争论更多。一些人赌咒罚誓说它真,另一些人指天誓日说它假。一句话,在这件事上,连鸡虫得失的事情都带有派性的色彩。所以,一个既非英格兰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超然于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或许能够比较客观而无成见地评说一番;一个有热烈的兴趣而无派性偏见的艺术家,或许更能够理解这出悲剧。 即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断言他所知道的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种种行状都是不容置疑的真情,那也是过于大胆,叫人不能原谅。其实,他唯一能把握的,只是某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而至于他以他的全部智力和良知认为客观的观点,也难免带着几分主观性。史料成了一本糊涂帐,他只能从糊涂帐中去探究真相。当时诸人的叙述如此看牴牾扞格,故而他对于这桩公案,在每一细枝末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小心谨慎,在某些情况下,最最老实的做法莫如在他的裁断后面打上个问号,承认玛丽·斯图亚特这一或那一事迹至今茫无头绪,无可钩稽,大概永无大白于天下的一日。 因此,作者向诸位奉献这部试作时,抱定宗旨决不采录刑讯及其它威吓和暴力手段逼供而得的证词:实事求是的人决不会指望和依靠屈打成招的口供,把它当作可信的材料。间谍和使臣(这两者在当年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同样如此,经过极其过细的选择才偶见于本书;本书作者 对每一份报告都采取存疑的态度。倘若本书作者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的“首饰箱信件”真实可靠,那是他把种种情状再三斟酌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参照了内在性格方面的因素。凡是文献中有两种相反说法的,本书作者对每种说法都要追溯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必须选择其 中之一,总是酌量这种或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这是本书作者的根本准则。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本身并不是个谜。它的矛盾仅仅表现在表面的发展上,内在的本质却是完整的,从头至尾都是鲜明的。玛丽·斯图亚特属于那种给人印象极深、能迸发出强烈的喜怒哀乐而又为时极短的情感的少数女性,属于那种光辉灿烂而昙花一现的女性,不是那种逐渐凋谢而是仿佛只在一种激情的熔炉中一次燃尽的女性。 二十三岁以前,她的感情始终像水波不兴的溪流;而往后,从二十五岁开始,她的感情也并未汹涌澎湃。唯有那短短的两年,风暴骤起——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成了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又气势磅礴的悲剧,类似《奥瑞斯忒亚》①。唯有那两年,玛丽·斯图亚特作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两年的狂飙使她超越了自己,在不可遏制的冲动中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扼杀了她心中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仍活在诗歌和争论中,却又只能归功于她的激情。 内心生活异常浓缩,全部都是绝无仅有的瞬间爆发,这决定了玛丽·斯图亚特各种传记的形式和节奏。艺术家的任务是再现这条直上直下的曲线,并且表现出它的独此一家的个性。所以,她一生的前二十三年以及被囚禁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与她悲惨的激情喷 薄而出的两年时间相等。作者如此剪裁,但愿诸位不以为恣肆。人的一生中,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吻合。对于心灵,唯有感受的充实方能作为计时的尺度:人的感受不像冷冰冰的日历,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从内心计算逝去的时光。在感情的陶醉中,怡然地挣脱了束缚,受到命运的福佑,人能够在一瞬间淋漓尽致地领略人生;尔后,弃绝了激情,又沦入一片空白,苦挨着永无尽头的岁月,伴着憧憧幻影,陷入荒漠般的空虚。正因为如此,往日的生活中只有那些紧张激动的瞬间才留下了痕迹;正因为如此,生活唯有浓缩成瞬间,唯有通过瞬间,才能够真 实地描叙出来。一个人,唯有烯发出精神力量,于己于人才算真正活着;他的心灵唯有燃烧至白热,才能成为看得见的形象。 -

心灵的焦灼
他,就在你心中最感动的地方,茨威格,一位绝对令你无法平静的人。他有一种力量,逼使你面对自己的内心。在他生前,他已经是世界上“被翻译出版得最多的作家”。这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尽管先我们而去了,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的还将时时产生震荡…… -

断头王后
本书是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之一,出版后曾轰动欧洲。 玛丽·安托瓦内特天生丽质,却成了母亲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15岁远嫁法国,与当时还是王储的路易十六结为夫妇。 路易十六性格软弱,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她不能履行丈夫的责任,并由此放任安托瓦内特的任性胡为以作为补偿。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安托瓦内特为了排解不幸婚姻带来的苦闷,终日沉迷于打扮、跳舞、赌博中,并耗费巨资修建行宫,左右国王、干预朝政,被讥讽为“赤字皇后”。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中,安托瓦内特的轻率和政治上的幼稚使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置于狂飙的巅峰,最终难逃厄运。 茨威格对这位薄命红颜跌宕起伏的人生给予深深同情,力图把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来描写,使她的悲剧性更具有感染力,更能打动人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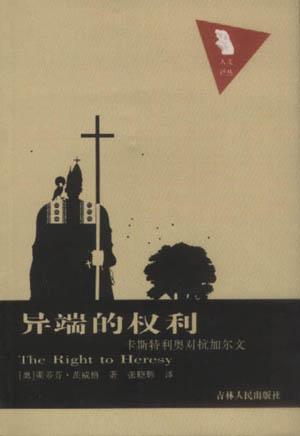
异端的权利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

昨日的世界
几十年前,茨威格是在对他不利但又极具他们那个时代特征的环境下来写自己这些回忆的。因为在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他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象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茨威格自己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他自己脑子里的记忆。不过,他们那一代人已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掉的一切从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恰恰是他的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吧。因为在茨威格看来,人的记忆力不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