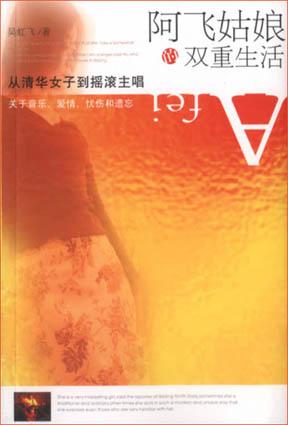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吴虹飞
本书收录了吴虹飞三年来名人访谈录的精华。32位活跃在各界的名人中,既有著名作家、学者、出版家,也有新锐派导演、音乐人、编剧,权威与独到并举,风格与时尚共进。吴虹飞的提问拒绝传统与平和,她坚持以单刀直入、独到另类的方式,叩问人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展露他们人性中的欢喜与悲伤、波澜与坦荡……
这个不务正业的“幸福大街”乐队的主唱吴虹飞,为了让自己得到更满意的对“幸福”的回答,一次次以记者的身份去出击那些“好玩” 的人物……吴虹飞自己也属于“好玩” 的人,于是“好玩”对“好玩”,文字便闪了光。
——主持人 白岩松
吴虹飞是一个很“笨”的记者。有些记者只要问几个问题,就能编出一篇长文章来。她不是这样的。也许正是因为“笨”,有些不容易采访到的人,却坐到了她面前。
——国家围棋队总教练 马晓春
我隐居十年,但从2004年底开始被媒体频频“骚扰”,而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吴虹飞的记者。当时她知道我不见记者,便给我写了一封信……原来这个在清华拿了好几个学位、出版过小说,还是摇滚歌星的“重量级人物”,小时候竟然是我的读者!这自然让我很受用、很麻醉。
—— 作家 郑渊洁
毕业前,阿飞很认真地对我说,她要唱歌,还要写小说,还要……然后就如愿出了专辑和小说集,以及这本访谈录。唉,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就想像一下她那种略带坏笑、又不失真诚的诡异神情吧。
——《武林外传》编剧 宁财神
另 类
郑渊洁:一个著作等身的文盲
我小时候胸无大志,最大的理想是当掏粪工。那时媒体宣传一个叫石传祥的劳动模范,他的职业是掏粪工。我当时是他的“粉丝”。小学二年级时,老师出命题作文《我长大了干什么》,我就写了我长大了当掏粪工人。班上的同学大都写长大了当科学家什么的。没想到老师把我这篇作文推荐到校刊上刊登。我估计可能是全市就我一个学生想长大了当掏粪工,老师是担心几年后北京没人掏粪,粪流遍野,赶紧用刊登作文立此存照的方式和我签约。
郭德纲:非著名相声演员
日子是稀里糊涂过下来的,老天爷的脸是变幻无常的,什么叫“绝处逢生”?他心有余悸。自己不过是想吃相声这碗饭而已。他已经有些波澜不惊的架势,铿锵说道: “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现在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马晓春:钢琴上的围棋九段
马小讲了个关于弹琴的故事:有一个朋友的朋友,要弹琴给我听。我于是礼节性地听了一曲。他弹完后,我礼节性地拍了一下手,结果那个人大受鼓舞,又接着弹了一曲,我只好又鼓掌。他于是又弹了一曲,我又鼓掌,于是他又弹了一曲,结果我们就这样一个鼓掌一个弹琴,浪费了很长时间……从此,他轻叹说,我就再也不去任何一个弹琴的聚会了。
宁财神:恶搞武林
作为一个朋友,宁财神是很可爱的,很负责的,作为一个谈恋爱的人,宁财神是很浪漫,甚至很纯情的,而作为一个编剧,宁财神是很敬业的。作为一个丈夫,宁财神会尽量避免单独和姑娘相处的时候,他,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高敏:这样的梦太美好
当运动员的时候目标就是得冠军。现在,就是一天三顿吃饱了,不要有事烦我,这比什么都好。我拿奥运冠军和我现在的快乐是一样的。小时候你买了一根冰棍和你长大了买一个电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快乐。这样的梦太好,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潘石屹: 我是相信命运的
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世 纪
吴清源:大师的简单
家道中落,14岁漂渡东瀛。彼时日军横扫中国和东亚大陆。乱世浮云,他孤身在日本,以匹夫之力,顶八方责难,在十次十番棋中,迎战全日本最顶尖棋士。1939年到1956年十几年间,他凭擂手君临天下,无人与之比肩——那是空前绝后的“吴清源时代”。
沈昌文:我忏悔我的不美
可能因为有这类不堪的阅历,我现在年过七十,依然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 骑一破旧“永久”,出入酒吧,口说broken English, 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不亦乐乎!
周传基:不要做好莱坞的干儿子
我活到这把年纪了,没有任何负担,也不用养家,只要饿不死就行。我的愿望就一点,中国能真正的拥有一个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国民族电影风格。
单田方:不爱说书反说书
话说我们那一家子呀,一个有出息的也没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叔叔、舅舅、大爷,三亲六故没一个当官的,也没那本事,都说书。
别看我生长在那个家庭,耳濡目染,受环境的熏陶,我对说书厌烦,不喜欢,讨厌。
黄永玉:好玩的老头儿
不管作品好坏,我能够告慰自己的,就是没有浪费时间。我朋友问我,你死了在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就开玩笑说,我死了,你就帮我刻上:“真累哟!”
何兆武:自由散漫的欣赏家
幸福的理由,总是要对前途怀着美好的希望。那个时候生活虽然困苦,可是回想起来,只觉得精神生活上是很愉快的。二十来岁的时候,很年轻,没有来由的,对于前途总有一种很朦胧的憧憬,觉得将来战后的世界是幸福美好的,所以生活的基调是美好的,虽然日本飞机每天来轰炸,却从来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
郑敏:战争中的诗与思
做中国的诗人很痛苦,在自己的诗里我写道,“我有一双空中的眼睛”,无论是战争,还是文革,无论是被抄家,还是陪斗,无论如何的动荡,总是有另外的我,理智地看着这个世界。我想这是哲学赋予我的。
赵宝煦: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五十年来,我忝为师表,一直不能忘记两句古语:“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不能满足于做“经师”,而是努力做“人师”。当时联大是以“民主堡垒”而著称。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西南联大出来的学生,对民主的诉求,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无法磨灭的印记。
书 写
余华: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这个当年试图通过写作来“自救”的“愤青”余华,如何在20多年的写作中,回归了传统并且达到与现实的和解?他是否有过困惑、感伤、压抑、犬儒,甚至言不由衷?我们试图以最大的诚意,探讨《兄弟》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影响和牵扯,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当代知名作家的访问,穷究来自历史和心灵的反省,以及疼痛。
贾平凹:守住灵魂的侯
棣花村文墨颇深,到了那千万不敢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朱文:什么是爱,什么是垃圾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朱文展示了他的机智,敏锐和配合的笑容,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后他就消失了。我忽然有些狐疑,是不是所有的,1960-1970年代生人的导演,都要给人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理解,对经验的剖析,都带着一种有着适度骄傲,有着尊严的个人痕迹。他们这样无声感动着某一代人,或者少数人,以及未来可能的大多数人。
格非:平人的潇湘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音容举止,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个,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合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
万方: 父亲曹禺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说过,我的这些女儿里面,你最象我。大概我是家里唯一写作的人。我的长相很象父亲。现在年龄越来越大,就发现自己有些地方和父亲越来越像,但我知道我和他是永远都不能比的,因为他23岁就写出了《雷雨》来。
学 识
李银河:我一直渴望爱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性这方面的观点算是比较激进、前卫。我愿这些研究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同时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们有所帮助,帮助他们去挑战陈旧、迂腐的性观念。
邹承鲁:牛胰岛素缔造者
虽然胰岛素的全合成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集中那么大的力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究竟是否值得?如果把这样大的力量用在其他方面,对我国生物化学的全面发展是否更加有益?对此我始终怀疑。但无论如何,我自己始终保持了对这个也许是最小的蛋白质的兴趣。
张维迎:改革是一种“气”
改革是一种“气”,一种气势、精神,或者理念,而非仅仅是一种方案。如果没有这样的气势和理念的话,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我从来不害怕跟人争论,1000个人有1000个声音。我们求同存异。但我感到很悲哀,这种悲哀在于: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缺乏共识,甚至是缺乏共同的语言。
朱大可:我最关心人的自由
陈平原:惟愿一辈子读书
李陀:读书使我误入歧途
钟鸣:诗人和他的博物馆帝国
博物馆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诗,耗费5年时间。
站在博物馆前,诗人钟鸣豪迈地说,“这是我的博物馆帝国”。他旨在以中国“南丝绸之路”为依托,收集汉代到唐宋的佛像雕刻。
赵汀阳:我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最想做而不会做的事情是:造原子弹,当将军,或者当数学家、科学家、刺客、特务。还有,我羡慕有功夫的人。
风 格
张 楚:也许音乐不该有那么多意义
我希望来听音乐的人是懂得享受音乐的。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表达当作一种信仰。甚至有时候与事实不符,也会拿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保障。可是事物发展得太快了,在这过程中,其实生活已经多出来特别多的空间,让自己考虑在人生中应该做些什么。
贾樟柯:“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超人,可以超出时代的束缚。事实上我们无法摆脱中国的文化宿命。我们总是在时代的阴影里生长。我们的作品里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
田壮壮:神话、信仰和敬畏
我已经年过半百,很难改变我所喜欢的事情。我只是心一条:我要拍能够打动你的东西。
最快乐的是保持心里的安静。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求的。
宁浩:只想拍好看的电影
《疯狂的石头》是一部具有浓重黑色幽默气质的现代喜剧,在荒诞的情节中营造合理的生活逻辑,充满内地电影罕见的勇气和乐观精神。它的特质和导演宁浩是一致的:年轻,无负担,轻装上阵。
何勇:不想再依靠音乐活下去
依然有着青春期的孩子,在长高,荷尔蒙有时太多了,就拿起电吉他,前仆后继。那是青春的热病,象天花,总是要这样挥霍过的,后悔的,放弃的,然后就好了,回到办公室里。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微笑着说,我当年也是搞过乐队的。你会想,青春多么相似,可是他们都没有象他们三个人一样。他们没登上过辉煌舞台就被纳入西服里,笑容可掬。有些是摇滚明星,有些是普通人。命运是很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