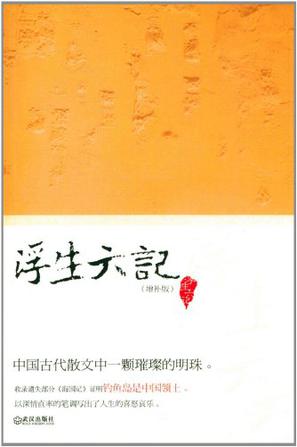浮生六记(汉英对照)
沈复
前 言
沈复出生于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苏州,当时正是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他做过政府文员,会画画,偶尔经商,也遭受过爱情悲剧。在其四十五岁左右时开始描述他的“浮生六记”,而且,自从这“六记”于十九世纪被发现以来就一直让中国人愉悦不已。
尽管《浮生六记》远不止此,但在中国人心目中它是一篇爱情故事。就其本身而论,在一个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篇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因为尽管《浮生六记》的确是关于沈复和他的妻子芸娘的爱情故事,但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与沈复狎妓、妻子想替他找妾这些事情共存并生,相互交织。
《浮生六记》是一份有价值的社会文献,书中对歌伎这一角色的描写就是一个例子。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歌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惟一与之相对应的人是妓女。但歌伎在中国是受人尊敬而且也值得尊敬的,她们的性也决不一定是可以用钱买到。正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所叙,歌伎常常比她表面上侍奉的那些男人更加独立和有权威。《浮生六记》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和猜测,这些改变虽小却意义重大,从而使《浮生六记》成为对西方人而言很重要的一本书。
中国读者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别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想到,直至最近,包办婚姻在中国都是非常普遍的。即使是现在,父母的巨大影响,经济或社会的巨大压力在婚姻伴侣的选择时依然存在。
因此这样一本源自帝国文学传统的、盛赞忍耐和浪漫爱情的作品当时极易成为,而且以后一直是中国读者喜爱的东西:这本书最近刚在中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而且也是中国几十年来出版的重要的关于爱情的书中的第一本。
沈复在这本书里向我们描述的他和妻子的生活,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最大胆直白、情真意切的。他给我们描摹了一幅关于芸,他的舐犊之情和他的妻子的精美图画。芸的生活窘迫,但她能淡然处之。沈复关于她的肖像,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对一位妇女生活的最现实的纪录,沈复在对他妻子的描写中,注入了极大的柔情。
这本书中引人瞩目的大胆直白之处远不止于此。当然清朝时的官方文学告知我们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是少之又少。小说、戏剧及神话传说的确让我们对这些有所了解,但往往又拘泥于故事情节的细微之处,以至于无暇顾及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的。《浮生六记》的确讲述了这方面的大量细节,同时又设法避免了许多在西方读者看来是繁复晦涩的东西,而这些在当时的许多中国大众文学作品中是很多见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沈复在传统的中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不是大学士却是一位学者。
以沈复和我们的标准,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失败者。在官场上,他最大就是一位很有权势的朋友的幕友,这是清朝许多不走运文人所充当的角色。他不是一个好的画家,生意也做得不好,常常债台高筑,在书结尾时他似乎已完全被他的家人疏远。
然而,尽管大多时候他是一个牺牲品,为人正直的他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正义。出于对同僚不义行为的憎恶,他辞去官职,同时,他又非常有绅士风度,没有告诉我们那些让他不快的行为。一个大人物要强迫农家女子做自己的小老婆时,他救了她,让她回到父母身边。他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而结果常常是让他付出代价。
如果说沈复在许多方面都不成功,他的许多失败是与他所在的阶层——衙门里的幕友相关的。衙门中的幕友这个职业自身几乎就是一个失败。
幕友这个职业的产生和中国行政管理的独特之处有关。首先,有这样的一条规则:异地为官,即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纵观后封建时期的中国各朝,这是标准的做法,以确保官员在管理本区事务时不受当地亲友的影响,从而做到公正。
第二点是源于这样的观点:政府官员必须首先是学者,然后才是官僚。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为很小的一群人管理,他们在初次上任之前,在行政管理方面毫无训练,他们对税法的了解不比对千年来诗歌的了解更多。
因此,中国典型的地方官在为官一方时,常常发现自己对当地几乎一无所知——的确,他可能伤心地发现自己甚至对当地的语言都不知道——只是对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律法及风俗习惯有些微的了解,而他竟然是要按照这些律法及风俗习惯来行使自己多重的管理责任。他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这种帮助他在幕友那儿可以得到。
幕友受过教育,又有专业技能,是地方官在学者的伦理道德与帝国政府面对的现实之间架设的桥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将幕友分为七类专业:刑名,钱谷,征地,挂号,书启或书禀,硃墨或红黑笔,账房。尽管《浮生六记》中没有明确的陈述,但沈复似乎是专攻律法的,是七类中最地位显赫的一个。
幕友几乎为地方官起草所有的文件。他们为他提供建议,几乎处理所有的公函,帮助组织庭审,替地方官起草回复上峰的询函,而这些行为起先很可能就是幕友建议的。幕友的好坏可能成就一个地方官,也可能毁了他的前途。幕友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幕友同时又具备非官方的身份。除了很短暂的一次失败的实验,清朝从来就没有正式承认过他们的存在。他们受雇于地方官——不是政府——由地方官招募而来,报酬也是出自地方官自己。幕友的酬劳丰厚。瞿同祖估计说,他们是衙门里惟一能自食其力的工作人员,而且受人尊敬。无论何时沈复记录自己为某一地方官效力,他总是说是被邀请就职的,这并非是他的矫饰之词。一旦受聘,幕友的地位就远非仆人能比,愤而辞职绝非稀罕,而且,如上所言,沈复本人就不止一次这样做过。
幕友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来自何方呢?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必须如此,以求胜任——大部分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参加过科举考试,因为那是当时教育制度的自然结果。如果他们通过了考试——有一些当然是成功了——他们自己就进入了仕途,不会做幕友了。
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拒绝,或被拒绝进入仕官阶层,他们曾经为了仕途的最高点而学习,最后却连最小的官职都没有。
这种处境一定非常痛苦。幕友在中国伟大的诗人和治国者的传统里长大,却不得不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做别人游移不定的手下,他们惟一的领域就是衙门职员那处于阴影中的世界,他们惟一的权力来源于他们的主人,而对于主人怀有一定的嫉妒心理,这也是非常自然之事。
在思考沈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了然于胸,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表面上看来,沈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或许我们最难理解的是他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力养家糊口,表面的原因是,这么做可能与他自己的定位不符。例如,妻子病了需要求医问药,他就开了一爿卖画的小店——他承认这只能维持她所需药物的部分开销——而不是(我们必须残酷地注意到)去找一份虽然地位较低,却可能为他提供比较稳定收入的工作。
这样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沈复自己列出来的,尽管他不像我们刚才做得那么直白。那么沈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无赖呢?广大读者自有公断,但我们确实认为,在做出判断之前,有几点需要考虑进去。
的确,沈复非常浪漫,喜欢梦想,常常在自我欺骗的怪圈中迷失方向。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沈复所受的教育就只是为了让他在生活中充当仕官的角色,沈复所在的阶层中没有人接受过除了这种教育之外的其他训练。的确,在我们看来,沈复在那种教育与他的生活毫无关系之后还念念不忘,但或许他只是认为这种教育可能带给他的美好前景,或者较其他人更沉迷于附庸风雅之中。在一个更加实际的层面上,值得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他决定找其他的事情做,什么样的职业适合他;或者,就此而言,他那一手遮天的父母会同意他从事怎样的职业。
尽管承认他个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在我们看来,沈复无力承担责任原因并非在此。他用以艰难度日的只有他理解的那一套既定的规则,他的悲剧就在于这些规则使他难以为继。正是这同样的悲剧,在他的这本书写成后的几十年里,又开始在他所有的同胞身上重演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本书原稿残缺,《浮生六记》中的最后两记在本书的手稿被发现并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首次出版时就遗失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书局在上海出版了据称是一个叫王均卿的人在苏州发现的全本,而且在台湾这种版本已经印行了数次。但世人皆知全本中的这两记是伪作,是从其他作者的书中抄来的。此译本的附录三有相关伪作的细节。除了这些信息之外,我们只有以沈复自己说这本书写于1809年来证明了。
这本书的特点在翻译时有些挑战性。沈复本人也承认,他写作不总是明晰直白的。这本书中有些暗指不清,有些几乎无法理解。有时所言事实前后抵牾。沈复关于书的概念和我们当今的概念也有很大差异。《浮生六记》不是我们现在所习惯的按时间顺序写就的记叙文章,相反,沈复选取了不同的题材,讲述自己人生的方方面面。这本书的本意是以六个不同的层面构建了一个人的“浮生”,每个层面与其他任一层面几乎毫无关联。我们希望沈复有过渡性文字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我们希望他提供合乎逻辑的解释,他常常只字不提。文中的句子不时兀自独立,缺乏连贯。因此,本书是供人掩卷沉思的,而且以我们的标准,要细细阅读。书中有许多未言明之处。但是,书中的言说无不饱含那个时代的生活特点。沈复作为一个没落家庭的不安定分子,给我们留下了一幅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生动画卷,这幅画卷常常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地方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
如果这样的作品以前都没有引起译者的注意,那就不正常了。林语堂在1953年先译出了这本书,在《天下月刊》和《西风》上连载。林译的本书曾以多种版本出版。
先行者应该得到我们无比的敬意,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将《浮生六记》完整地译成现代英语还是有可能的。通过大量(我们希望不要过量)的注解和地图,这个译本会将沈复的描述更加完整地展现在现代英语读者面前。沈复为彼时彼地的读者而作,而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希望为这部作品所作的一切,能有助于它存活于当代西方读者心中,正如它的作者希望它存活于自己的同辈人心中一样。
我们努力为读者提供全译本,用余国藩先生的话来说,“对原作最大程度地明晰的忠实”。但是,对我们译本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谨怀着对原作的敬意,欢迎这些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