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文学印象
-

呐喊与流言
《呐喊与流言》收录论文、书评及讲稿共35篇,大部分是作者近年新作,也有一些十几前的旧文。以论题分类,大致可分“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重读文革”及“阅读香港小说”三个部分。“呐喊与流言”不仅是我对自己专业(现代中文文学)重新思考的关键词,也可以勉强用来交代我自己近年来的工作。《呐喊与流言》中第二部分从《重读“文革”(思考笔记)》到《革命·历史·小说》的八九篇文章,都是拙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哈佛学术丛书,2000)的补充和发展。啰里啰嗦不厌其烦地讨论“文革故事”如何在当代中文文学中被叙述,也算是我的“呐喊”吧(虽然声音不大喉咙沙哑也没什么人要听)。《呐喊与流言》最后部分有十来篇讨论香港小说的文章,则可以显示我对流言形态市民文学的浓厚兴趣。在西西、黄碧云、李碧华、王良和、昆南、也斯等人笔下的食色“流言”之中,我看到了另一种形态的“呐喊”。当然,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些讨论乃至散布“流言”的方式,虽不在《呐喊与流言》范围之内,但对待“呐喊与流言”的态度却是一致的,集末附录的讲演稿算是一个注解。 -

输水管森林
《输水管森另》为“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一辑之香港卷,收14篇香港小说,包括西西的《浪子燕青》、关丽珊的《青鸟》、潘国灵的《我到底失去了什么》、陈洁心的《铁轨上的掠影》等。 -

一九四九以后
《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讲述了当代文学六十年的风流云变。现代中文文学到了一九四九年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和分流。中国大陆出现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文人身份与干部体制、作家协会与国家机器关系复杂,此消彼长。从“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宣传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矛盾主线。台湾在日据五十年后建设了“国语的文学”,由“反共文学”到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再到“世纪末的华丽”,不少佳作树立了当代中文文学的标准。而香港文学从“左右战场”到“本土性”自觉,再到“九七”“后殖民”书写,同样自成一派风景。转眼六十年过去,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当代中文文学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与成就,此其时也。 -

许子东讲稿-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二
《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许子东讲稿(卷2)》大致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五篇关于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文和评论,其中《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和《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都是2010年刚刚完成的。《物化苍凉》是提交岭南大学一个研讨会的论文。《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最初用英文写,是在UCLA一个讨论课的论文。写作此文时常在洛杉矶的Westwood Blvd.与Rochester Ave.路口找免费停车位,转来转去边打腹稿。万没想到张爱玲最后寓所正在那附近。她在那个公寓去世数日后才被发现,没有家具,只有一些纸盒和一堆衣服(纸盒里有从未发表的英文小说原稿)。后来才惊讶看到,我去打印论文的Kinkos复印店和常用的邮局,都出现在纪念张爱玲最后日月的照片中。另一个吊诡的巧合是我在上海南京西路重华新村前后住了20多年,很晚才在张子静的回忆录中得知张爱玲是在重华新村的沿街住所看着解放军进城的……当然,我的文章与这些巧合并无直接关系。 第二部分是四篇有关郁达夫的论文。《郁达夫创作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是我在华东师大硕士论文的一节,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文学评论》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一文则从未在期刊上发表过。《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当年就有争议,所涉及的话题至今恐怕仍缺共识。《浪漫派?感伤主义?零余者?私小说作家?》一文有四万多字,写了大半年——郁达夫读了很多外国小说,做这方面的研究也追得比较辛苦。这几篇文章都写于80年代,这次除了修改注释格式,文字上甚至局部观点也有修订。最近才听说,我的第一本书《郁达夫新论》1984年在浙江文艺出版时,编辑铁流、李庆西及所有编辑室成员都要看清样签字,为这本当时看来既有新意也有风险的新人新论共同承担责任。这本书后来获奖且印数过万,浙江文艺遂出版“新人文论丛书”。“丛书”的“新人”们——黄子平、陈平原、赵园、刘纳、王晓明、程德培、蔡翔、季红真、南帆等,现在大都是学术名家,甚至即将退休——然而,学术出版的文化环境竟没有大的变化。80年代的课题,也还是今天的课题。“民族”与“性”仍是国人在现实与虚幻(网络)的主要“郁闷”(郁达夫的苦闷?),所以,我以为自己这几篇旧文,似乎仍然可以再读。总之现代作家我有文章专论的,就是郁达夫和张爱玲。我也很关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但作家论所打下的基础,我后来一直没有后悔。《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许子东讲稿(卷2)》第三部分收了五篇讨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写于1989年我出国游学之后。各有不同的具体写作原因,或因为编书,或因为开会,话题也颇“多元”,但论述方式又不无相同之处:似乎都要列出几个不同的理论、形象、作品、意象或书本,辨异中之同,察同中之异。背后有意无意,或者都有些一直坚持的结构与方法?自己也不太清楚。 第四部分是四篇关于香港文学的文章。写这些文章既是因为编书(三联版“香港短篇小说双年选”)的原因,也是出于教学的需要。有感于香港“文艺小说”相对寂寞,还曾和王安忆、王德威(后有陈思和、黄锦树)一起为上海文艺编过“三城记小说选”。其实,从边缘看中心,研究过程也另有收获。 《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许子东讲稿(卷2)》附录了三篇讲座录音,其中有些话题在前面的论文或有触及,但“话怎么说”也决定“说什么话”,表述方式不同,意旨联想也很不一样。重校本卷稿子,竟连贯了二十多年读书生活。这才意识到一个人可以用来做事的时间原来这么短。自我溢美就是回首往事,不怎么会因过去的文字而羞愧;苛刻而言也是学业不够与时俱进,方法境界不够扩展。在文体上倒是有些变化:以前的论文是书面文体,近期文章尤其讲座文字较多口语。书名是“讲稿”,意为讲座与文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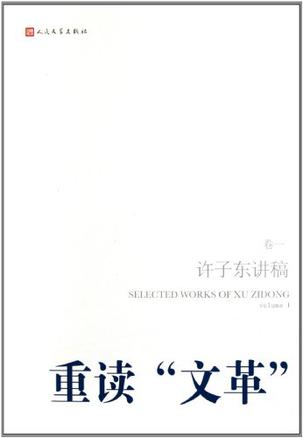
重读"文革"
《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在《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有不少批评,缺陷疏漏当然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内容……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我想,于私,是个人记忆。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九评、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亲切的目光:“别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声、下放干部告诉惊讶的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一次不杀他”……怎么办呢?生死在这个时代,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山崖旁路很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