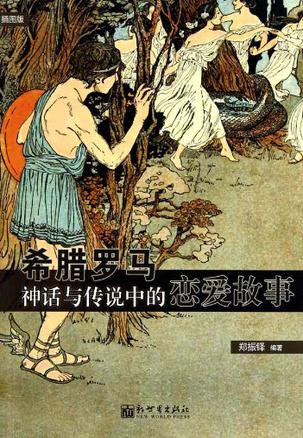废纸劫
郑振铎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藏书家,一个爱书胜于自己生命的文化名人。抗战期间,他留在上海孤岛数年,为国家抢救古籍,使之不致遭受战火或流落国外,他所抢救下来的图书,其文化意义之重要性,仅次于敦煌石窟与西北汉简的出世。本书所选文章皆与“失书”有关,所谓“失书”,实为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文化之劫难,因此书名取《废纸劫》。郑振铎先生的《废纸劫》是一个书痴的絮语,也是普世爱书人的共同密语,更是一个民族对拯救文化之劫难的振聋发聩之语。
《废纸劫》所选郑振铎文,是作者对书、对文化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呐喊。在作者生存的特殊年代,甚至就在当下社会,“书”遭受着“废纸”般的劫难,本书为我们当下的阅读增加一种声音,再把这种声音放大,让更多的人于此书中寻到自己甚至这个民族的文化天籁。
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
——郑振铎
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甚至要说,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可能重新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以弥补。
——止庵
梁文道:任何失书之人都该看看郑振铎先生的《废纸劫》
“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甚至要说,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可能重新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以弥补。”谨以此书呼吁当今中国文化之复兴!
失书(代序)
梁文道
有一位朋友在香港搞民间书展搞了好几年。与困处室内人声鼎沸的官办大型书展不同,他喜欢在露天空旷处晒书,任一家大小如游园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绿草,所以不叫它书展,但称之为“书节”,意思很好。去年书节,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请几位读书的名人公开所藏,拿十本“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出来展示。承蒙不弃,忝列名人,于是挑了又挑,干脆凑足十一本给他。两个月后,才知道我那十一本书连同他人的藏品一并给盗去了,不余半本。朋友当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觉得无所谓,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给我一张失书名单,并保证替我一一购回。购回?我想他们大概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吧。德里达有本悼友文集,书名改得好,《死亡,每一个世界的消逝》。同样地,对于爱书人而言,每一本书的失去也都是一个世界的消逝。
收到部分偿书之后,就更证明了我的担忧。且看柏拉图对话集之《苏格拉底的申辩》,我失去的那本是上世纪古典学名家柏奈特(John Burnet)翻译的《Euthyphro,Apology of Socrates,Crito》,英文希腊文对照。与他们替我补回的那个今人新译版根本是两回事,这是不懂行情。再看《胡适文存》,我那四卷本是民国七十二年的台湾远东社翻印,不算什么好版本。可原书精装四册,朱红封面,是伴我成长的启蒙书,如今独遗首册,又能去哪里寻回呢?《百年孤寂》英文版当然买得回来,然而我借出的是2006年英国Folio Society精印重制,装帧雅致,插图秀美,虽非签名首版,其价值也非一般市面通行者可比。其余各书若非昔年师长赠赐,就是别有故事。比如说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我在加州柏克莱一家老书店买的,那家令人难忘的老店现在已经停业了。那本周作人编的《明人小品选》,曾经塞在背包里伴我走过长江蜀道,旅次中不时翻阅辄有所得。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当年买它的时候,我既没听过这位大家也不知道这部名作。但在洛杉矶的阳光底下,商场喷泉反照出的彩虹旁边,我打开了它,书里的欲望之城Isidora的甜美清泉与明艳色彩不只异常地相类于身边的环境,同样地华丽,同样地虚幻;这本书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看法。这十一部书中的折痕,字行间的画线,一切一切全都消失了。每一本书的失去,果然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
任何有过这种惨重损失的人都该看看郑振铎先生的《废纸劫》,乃知失书有其大小,自己的珍藏尽散为小,整个文化的泉源断绝是大。正如止庵在《废纸劫》台版序文所言:“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没错,这的确是要感动的,因为这段话说明的正是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一种精神传统:不忍往圣所传尽散于吾辈之手,乃有兴灭继绝之志。
伏生一介书生,以身犯险,最终虽“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然而就是这二十九篇使得齐鲁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奠定了汉儒乃至于后来整个中国思想传统的基础。当年伏生把书藏在墙里,本是件多么不起眼的小事,可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又是个多么伟大的成就呀。更重要的是就算伏生也料想不到他偷偷藏起来的那些书日后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吧,他就只是凭一股感觉,一股不忍之情,把那些书埋在砖土之中,再看它们渐渐消失眼前,也不知日后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它们是否还能重见天日。但这一刻,他唯一要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些前人的遗产避开秦火,期诸后人,交托历史。
郑振铎先生是位大藏书家,一生努力考掘中国俗文学史,编辑过的书刊不尽其数,翻译了《国际歌》的歌词,还发明了“漫画”一词。可是就像止庵兄所说的,他毕生最大的成就或许还是在抗战期间抢救文献的艰难工作。
那时候,炮火中郑先生不知失却了多少私人藏书,其中“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而他醉心的清人文集收藏竟有“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但他最介介于心的,不是数十年心血的沦亡,却是对不起古人。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人家要不是弃笔从戎,就是写些鼓舞士气的爱国文章,一生爱书如痴的郑先生却还在念着收书藏书。眼看国家将亡,同辈友人也多不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觉得他无聊。可是郑先生一方面看见许多珍稀古籍正不断流入外人之手,觉得以后中国人竟要到了外国才看得见中国书是荒谬的奇耻;另一面则不断目睹战火之中被焚成纸片的文献飞舞成灰,他如何不慌,如何不急?
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藏书计划,转而为国收书。“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一开始靠的是个人力量,和北方书商抢书,人家背后要不是财雄势大的外国图书馆,就是正在搜寻各地方志的日本人(郑先生认为这些日本人有战略的野心,目的是规划行军路线和未来的长期统治),他怎抢得过人家呢?有一回他在市面看到一堆好书,也不管阮囊羞涩,硬是全部要下,“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
接着那几年里,他先是以一人之力为国救书,后来才得到重庆方面的支援,大手入市,把当时中国图书由南往北流的趋势逆转过来,尽收民间一切有价值的珍本,为文化存一丝命脉。虽有钱买书,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为避敌人耳目,有家不归,老在朋友处挂单,身上永远有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耳目永远留意街角的阴影和背后突然响起的脚步。买书,要秘密地买;庋藏,要秘密地藏。等到把书偷运出去了,又要挂心战火会不会波及海运的路线。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记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自己的珍藏付之一炬固然可惜,但若有了更大的眼界,胸怀就不同了。
相比之下,我不见了几本书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坦白讲,对于那趁乱在书节中窃去书本的人,我反而发不出什么脾气。不是因为我觉得“雅贼”特别可以原谅,而是因为我对他有点期盼。我猜他费这番周章,应该还不至于把赃物拿去当废纸卖吧,我希望他能好好看看那些书。例如《胡适文存》,曾经启蒙过我,后来束之高阁,隐蔽蒙尘;现在在他手上,又会带给他些什么呢?就算他不看,转卖给旧书商,它也总有面对另一个读者的一线生机吧。
我曾经养过一条肥肥胖胖的可爱金鱼,叫做多多,名字的来源是《芝麻街》里Elmo的金鱼多乐希(Dorothy)。我曾经还有一幅多多的铅笔画像,夹在我喜欢的一本书里当书签,任何时候翻开都能看到多多的样子。后来,多多死了,而那张书页里的图画如今则随着书本散失在一室书堆之中,欲觅无从,不知去向,恍如一尾在海中迷路的鱼。木心《同情中断录》的序言,就只是短短一句触目惊心的话:“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其实书亦何尝不是如此,我曾拥有,我曾读过的书,在我的生命中都只是行过而已;行过,走了,无所谓完成,亦无所谓终结。藏书与藏书的失散,有时候真是不太重要的。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汐湖,终有流出冲散的一天,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本来就非我所有。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且还有再用的价值,堪比器官捐赠。至于我所宝爱的那几本失书,这就叫做回归大海,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在我有限的见识与生命里,它们行过,如此而已。多多走了,重新加入这第三行星的能量循环。它的画像却还在,囚禁于一本迷路的书。我还能再见到这条鱼吗?不知道。或许未来的某天,他和夹藏他的那本书会一起释出,离开我这座小小的汐湖,游进书摊之中。甚至及我身后,他会出现在另一个读者的眼前,那人虽不知这尾鱼的来处,他却早已摆脱了名字的束缚,兀自摆尾,可爱如昔,与书同在,一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