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史
本书是作者在1930年代初为高级中学的学生所写的一本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的编写,还颇重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这也是吕先生的一贯主张。编教科书,自不宜羼入议论;历史的有年代,犹地理有经纬线;历史、地理两科,关系极密。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中国书籍,向分经、史、子、集四部,这原不过大概的分类。读史地图、年表、系谱,都是读史者当备的书,所以本书中不再附入。 本书共分六编。第一编绪论;第二编上古史;第三编中古史;第四编近代史;第五编现代史;第六编结论等。 -

日本史记
通用名《大日本史》。是17—19世纪日本诸侯水户藩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从上古神话记述到南北朝终结,内含本纪七十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共二百四十三卷。百代史事汇聚一书,日本古代文学名著、影视剧多可在本书中找到历史背景和情境描绘。 本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名著,水户学的基础之一,对日本历史进程和精神文化遗产影响深远: 明朝灭亡后,遗民朱舜水流亡到水户藩,本书主修者藩主德川光圀深加礼之,深受中国儒家思想浸淫,本书编纂举水户藩全藩财力,二百余年修成,故事精美之外,其正统思想,后来演变为“尊王攘夷”,对后来的幕府倒台,明治维新起了动员作用。 本书前半铺陈宫廷、朝臣生活,后半武家崛起战争场面,人物鲜活,行事奇异,性格多样,场面壮阔,读之忘倦,可读性非凡,虽效仿中国史法,体例甚至有所创见。 本书用明治三十三年本为校点本最初的录入与校对依据。以明治三十九版为覆校,改正了底本明显的错讹。只对明显的手民误植以及易于引起误会的通假字、异体字,根据其他版本与资料略做更动。原书引用的大量日本古歌均原文移用,标点使用力求谨慎简略,原书双行夹注,一律改为脚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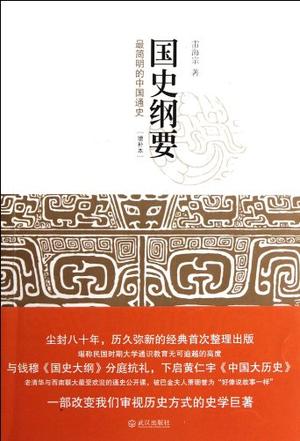
国史纲要
《国史纲要(增补本)》由雷海宗所著,原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教材,讲授对象主要为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因其广博而不失精细的特点,受众多学生的追捧,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无论史学观点还是编纂方式,《国史纲要(增补本)》均不同于其他通史,特别与当时盛行的“考证派”大相径庭,反映了作者一向重视综合和通识的治史特点,尤其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期,逻辑严密,脉络清晰,成一家之说,无疑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佳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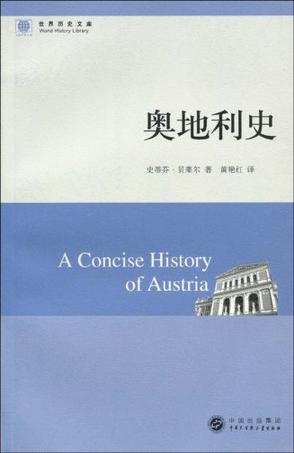
奥地利史
《奥地利史》内容简介:现代奥地利是个繁荣的中欧小国,但它有一段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远远超出它如今的国境线。史蒂芬•贝莱尔以引人入胜、全面深入的阐述追溯了奥地利非凡历程中的诸多变迁:从作为德意志军事边区到王朝世家的建立,从成为帝国皇室家族到建立中欧大帝国,从失败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到德国的一个地区,再到成功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奥地利的特性和遗产及其多姿多彩的源泉构成了一幅多层次的画卷。这是一段充满反常与另类色彩的故事,是探讨欧洲历史的另一面的力作,它并非以更为清晰的民族叙述方式给出方便的答案,因而更切合于今天的世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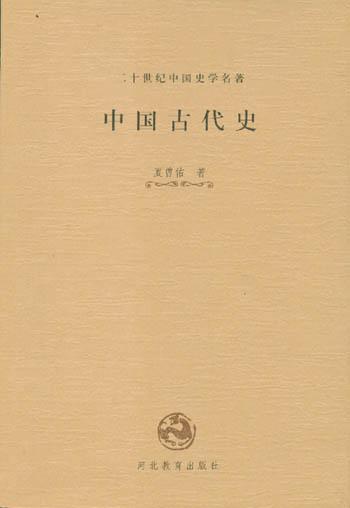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
20世纪初,夏曾佑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在夏曾佑之前,国内已经有人用新观点、新体裁写出了新式的中国通史。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更大,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旨在系统地展示上个世纪的史学成果,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奉献给读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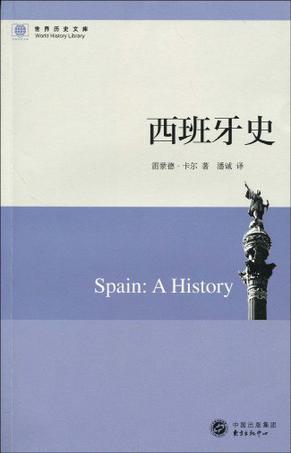
西班牙史
在一代学者的手里,尤其是一代西班牙学者的手里,西班牙的历史正在经历拨乱反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摒弃了西班牙例外论,现在人们认为应当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的历史。 要解释西班牙的“落后”及其与欧洲繁荣的北部国家之间的鸿沟,没有必要追溯宗教裁判所制度,而正是后者切断了西班牙与发达国家繁荣和进步的基础——知识和科学的成就——之间的联系。而启蒙运动一旦打开欧洲的窗户之后,反动派们建构了又一种不相上下的正义的传奇:西班牙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才衰落的,因为路德宗的继承人和伏尔泰、卢梭的信徒们毒害了西班牙天主教的精华,而这种精华是西班牙身份的标志和伟大的基础。在与自由主义对垒的过程中,正义的传奇成为早期佛朗哥主义宣传的知识重心。西班牙被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继承人和那些寻求保存传统西班牙的天主教精华的人们,当作斗争的意识形态战场。在修正的历史学家们看来,这种摩尼教式的、两分法的“两个西班牙”的视野,是自由主义者和反动派们出于政治目的,玩弄的形而上的建构。在经济史家那里,两个西班牙的意识形态则摇身一变,成了相对繁荣的和乡村贫困、停滞的西班牙,他们称之为‘二元经济’。 历史学家否认天主教教会具有压倒一切的社会和知识影响力,至少最近,两个西班牙的观念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修正主义的观点也不认为,西班牙的历史缺乏争议之处。数量庞大的摩尔人的社会、文化的后果和影响深远的犹太人及其被驱逐的后果,是一个仍然存在着争议的话题。更近的来说,对于这个在19、20世纪被当作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处方,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经济史家多有论争。现代历史学家们完全摒弃的是,浪漫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的视野,因为后者为了能保存——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在追逐物质繁荣时失落的——人的、精神的价值,故意拒绝进步。对于183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及许多他们的继承人们,标志性的英雄是唐吉柯德。对于他们来说,西班牙的历史不应该用客观的因素解释,而要用某些有关西班牙人心灵的洞察来解释。现代历史学家们能够接受的是小说家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的看法,一半有关西班牙人灵魂的无谓揣测都是外国人发明的,另一半是西班牙人自己干的。 修正主义的史学原封未动的观点认为,西班牙历史的关键之一是其多样性。这篇介绍的目的是划出多样性的地图,检查这种多样性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动因和后果。 直到20世纪,大多数西班牙人仍在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他们工作的状况则由土壤和气候的互相作用和由土地的租金决定,后者由历史遗留下来的。 西班牙的多样性反映在西班牙农村的风景线和建筑上。安达卢西亚的单一种植橄榄的哈恩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种植农场雇工都生活在镇上,周边的乡村在旱季很荒凉。1793年一个法国旅游者这样写道,大土地所有者占据统治地位,就像狮子在它居住的林子里,吼声赶跑了所有想要接近它的人或动物。在巴斯克省份加里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乡间点缀着村落和农场。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冲突。家庭农场稳定的地区保守,倾向于信奉天主教。19世纪的安达卢西亚农村,由于农民要求没收、重新划分大地产,成为混乱不止的重镇。当工业化使得新式工厂开始吸收贫穷的农民的时候,这些在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农业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整体而言,他们直到1950年代才完全变化过来。 西班牙是个庞大的、正方形的国家,这里中央高地海拔高度约2000英尺。由于某些山区的坡度是欧洲之最,公路和铁路建造起来花费很大。从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上来说,西班牙的中心区域失去了支配性的地位。这是向古典时代的回归,当时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吸引人口、活动和生产。还有另外一种向着古典时代的回归。罗马时代的西班牙丰富的矿藏资源曾经吸引过投资。西班牙只是不出产质优价廉的煤炭资源,而这是工业革命最必需的原料。1830年代,似乎只有马尔贝拉(Marbella),现在石油酋长国的操场和欧洲高尔夫球场,可能成为繁荣的钢铁工业中心。但由于缺乏廉价的煤炭,钢铁工业中心转移到了北方。1870年代的时候,毕尔巴鄂附近的铁矿使得西班牙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出口所获得的利润和换回了廉价的威尔士煤炭,使得毕尔巴鄂成为了西班牙最大的重工业中心,因而吸引了潮水般涌入的来自卡斯提尔的贫穷农民工。 一百年以后,杰拉德布伦南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西班牙迷宫》(The Spannish Labyrinth)前言里写道,对于西班牙,正常的状态是,它是小的、互相敌对或老死不相往来的共和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历史上的某些伟大的时期(哈里发时代、再征服时代和黄金时代〔Siglo de Oro〕),这些渺小的中心会由于共同的感情或思想的影响,一致行动;而当来自上述思想的冲动衰退之后,它们仍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 罗马对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强加的统治,创造了泛西班牙的概念,把西班牙作为单一的政治实体。哥特人国王至少在理论上,是罗马人的继承人,因此他们统治着的是个单一的王国。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天主教对阿里安异端的胜利,主教们给予了西班牙单一的宗教。对于西班牙民族主义者们来说,罗马天主教与国家本身是同质的。佛朗哥的《幕后的主宰者》(eminence Grise)成书于1970年代,里面提到,卡雷罗·布兰科将军说过,西班牙要么是天主教的,要么就啥也不是。 摩尔人的侵略破坏了这种统一性。西班牙分裂为两个政治、社会体系,两种文明:摩尔人的南部和基督教的北部——尽管,正如晚近的历史学家强调的那样,文化边际在两者之间是可渗透的,有时候允许很多的文化交流。可不论是基督教国王,还是摩尔人都难以战胜地方主义势力的向心力。科尔多瓦式地分裂为塔伊法小国家。尽管有着卡斯提尔的帝国使命,仍旧是陷于地方内部的战争状态。天主教国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创造的不是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学到的现代民族国家。卡斯提尔和阿拉冈王室之间的联合,是由他们1469的联姻而创造的。因为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是联邦制的君主制,条件是君主个人的权威和他们对特权的尊重。地方宪法联邦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巴斯克省份和包括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在内的阿拉冈王室领地以准独立的状态,他们有自己的地方议会。新教的支持者们把腓力二世当作绝对主义君主。当他越过自己的王国,向阿拉冈议会收取税收的时候,他自己可不是这样想的。 在必要的、有效的、中央集权的马德里政府和当地传统的力量之间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是1931年到1936年之间的第二共和国的波旁君主制和1975年之后的立宪君主制的任务。中央施加的压力多一点,就会酿成地方的叛乱。由于过度征税,腓力二世的卡斯提尔臣民抱怨他们承担了过多的帝国花费,因为他们作为特权的特权,使得阿拉冈和加泰罗尼亚躲避的税收都落到了他们的肩膀上。腓力四世的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1587—1645)寻求通过把加泰罗尼亚置于卡斯提尔的习惯制下,以分摊这种负担。他遭遇了加泰罗尼亚人1640年的叛乱。哈布斯堡的君主只得屈服。1714年之后,波旁王室重操旧业,废止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特权地位。他们得到的还不如奥雷维德的多。最为坚决的中央集权者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雅各宾派,因为他们把西班牙历史形成的地区划分为法国模式的省份,制定了一部全西班牙人共同的宪法。巴斯克省份和加泰罗尼亚为了维护失去的地方自由,采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以维护他们非卡斯提尔的语言和要求地方自治为基础。尽管1931年到1936年的第二共和国授予地方自治的权利,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佛朗哥将军继承了19世纪激进的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废除了地方自治地位、压制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文化,结果使得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成为难以压制的势力。佛朗哥死后,新民主在1978年的宪法中得以恢复。欧洲最非中央集权化的宪法,在这三个巴斯克省份信仰基督教之后,“自治国家法”授予巴斯克地区像加泰罗尼亚地区一样的地方自治的权利。慷慨的地方自治打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因为就加泰罗尼亚而言,分离主义只是一个较弱小的运动。令人不快的地方自治并不能令数量多得多的巴斯克激进民族主义者满意,他们诉诸于埃塔恐怖主义,把他们愿景中的独立巴斯克国家强加给西班牙及其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