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与世界
什么是现象学?从字面上看,“现象学”(phenenomenology)即有关现象的学问。但大千世界,现象纷纭。有物理现象如万有引力,有天文现象如流星雨,有化学现象如化合与分解,有生理现象如消化不良,有心理现象如单相思、白日梦,有社会现象如贪污腐败,甚至也有超自然现象如通灵术……每个现象领域都有自己领域的研究专家,于是而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通灵学家等等。那么现象学家研究哪门子现象?除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心理现象、超自然现象外,难道还有一门专供现象学家研究的秘而不宣的现象?“秘而不宣的现象”一词本身就有语病,现象之义即宣示出来的东西,说秘而不宣的现象就等于说不宣之宣,自相矛盾,昭然若揭。 仿佛只剩下了一条出路:现象学家研究的是现象总体即世界。哲学不就是世界观吗?现象学不就是一种哲学吗?现象学就是一种世界观,而且研究世界现象。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结论。然而现象学运动中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明确反对所谓的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时下将哲学等同于世界观已成“常识”,据说,世界观即是对世界之总的“看法”,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的“概括”与“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社会科学的成果、思维科学的成果都是“理论成果”,对理论的“概括”与“总结”则是理论的理论,而且通常是最蹩脚的理论。理论已与现象隔了一层,理论的理论与现象则是隔了双层。将现象学与世界观划等号差不多等于从石头里取水,两不相干。 “现象”之为“现象”,即是显现出来的东西。依海德格尔的考究,“现象”一语出自希腊词Φαιυομευου,该词由动词φαiυεοθαι派生而来,而后者的意思就是“显示自身”(显现)。因此φαιυομευου等于说:显示着自身的东西。而“学”之为“学”就是“让人来看”。“学”一语出自希腊词λοros,原义即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及的东西”。现象学于是便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 于是,现象学成了一门“看”的学问。“看”就有个“看法”问题,现象学被作为一种方法即是“看的方法”,这个“看法”很简单即“如实看”、“如如”。本世纪初的哲坛充斥着“回到康德去!”(新康德主义)、“回到黑格尔去!”(新黑格尔主义)、“回到托马斯去!”(新托马斯主义)之类原教旨主义式的口号,唯独胡塞尔一声“回到实事本身去!”之大音(BackToThingsThemselves)至今仍然有所回荡。回到实事本身去,即是如实看。然而如实看知之甚易,行之艰难。人们不是往往在声称如实看的时候,恰恰看到的只是他的一偏之见,只是一些理论,只是一些个人的利益与兴趣吗?一叶障目与盲人摸象的人往往也是那些把如实看挂在嘴头叫得最响的人。于是便有一个如何如实看,如何回到实事本身去的问题。在胡塞尔便有了一套如何如实看的方法论训练,如现象学悬搁、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等。然而它既然是一套“方法论”,便仍不免是一种“理论”而非现象,因而也不免被掌握着“如实看”法宝的其他现象学家所“悬搁”、“还原”。现象学的“如实看”遂变成了一种“如是我看”。 因“我”之不同,“如是我看”的东西也因之不同。在“回到实事本身”的总看法下,产生了不同的“亚看法”。在胡塞尔那里,回到实事本身,即“诸原则之原则”,那就是:“每一种源始所予的直观都是知识合法性(Rechtsquelle)的源泉,在源始形式的(好似在其机体的实在中)‘直观’中直呈自身的东西,只应该如其给出自身的那样,并且只是在它直呈自身的限度内被接受。”①于是,对胡塞尔而言,回到实事本身便是回到源始直观、回到明证性、回到纯粹意识;然而,同样打着回到实事本身大旗的海德格尔却根本不买胡塞尔的直观的帐,“直观”是“远离源头的衍生物”,“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植根于生存论的领会”,“只有存在与存在结构才能够成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而只有当我们获得了存在与存在结构的鲜明概念之后,本质直观这种看的方式才能决定下来”。②而胡塞尔“如实看”的还原法也由回到Noesis-Noematic的意向结构变成了由“存在者转向其存在”。③回到实事本身在海德格尔这里便成了回到存在本身。而在梅洛-庞蒂的哲学中,“回到实事本身,就是回到先于知识、知识一直在谈论的世界”,④于是回到实事本身在梅洛-庞蒂这里便成了回到知觉、肉身化的知觉。他一方面声称“现象学只有通过现象学方法才能通达”,①另一方面又断然宣布,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法“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彻底还原是不可能的。”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回到实事本身这句口号颇具讽刺意味,在不同的现象学家那里,对实事的理解竟是如此之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回到实事本身差不多成了回到每个现象学家的理论的代名词。 胡塞尔藉其回到实事本身的“如实看”而发现了先验意识之领地,他曾以发现“应许之地”的摩西自命,也一度希望后继者会进入这片应许之地有所耕耘与收获。然而,他的哥廷根的弟子们一古脑地忙于“对象”这一“实事”的描述,而与他本人的进一步的期待拉开了距离,他曾一度寄予厚望的约书亚——海德格尔则在“实存”的“实事”中越走越远。他不无伤感地感慨道:“作为科学、作为严密的、必然真实地严密的科学的哲学——这一梦想结束了。”③他在致Welch的信中黯然写道,统一的现象学运动并不存在,所谓的“现象学运动”对现象学的“如实看”方法(还原法)茫然无察。④ 没有一个统一的现象学运动,这不只是胡塞尔一个人的看法,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一书中明确告诉我们:“在现象学研究内部,对现象学的性质及其任务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即便这些在界定现象学性质中的差异能找到一个相同点,这个如此获得的现象学概念——一种平均化的概念——能否将我们引向有待选择的具体问题是值得怀疑的。”①梅洛-庞蒂不仅认为在诸现象学家中难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对于现象学的认识,即便对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也很难找到一个唯一的标准:“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第一部著作发表后的半个世纪后依然问这个问题看来有些奇怪。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现象学是本质的研究,依照此,一切问题都等于去发现本质的界定:例如知觉的本质、或意识的本质;但现象学也是将本质置还于实存之中的一门哲学,它并不期望在‘实际性’(facticity)之外出发获得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它是将自然态度下产生的主张悬置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先验哲学;但它也是在反思开始之前,世界作为不可剥夺的在场总是‘早已在那儿’的哲学,它的一切努力都围绕着重新达到与世界的直接与源始的接触并赋予该接触以哲学的地位。它旨在探究成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但它也提供对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时间及世界的叙述。它试图如其所是地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而不考虑其心理学的起源以及科学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可能提供的叙述;但胡塞尔在其最后的著作中却提出一门‘生成现象学’(geneticphenomenology),甚至提出一门‘建构的现象学’(constructivephenomenology)……”②而利科则干脆表示:“整个现象学并不只是胡塞尔,但他多少是其中心”,“现象学就是胡塞尔的工作以及由之而产生出来的异端之总体”。①如果在现象学家中,对于现象学本身是什么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谈论现象学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而且,谈论现象学运动的合法性又是什么呢?施皮格伯格在其经典性的《现象学运动》中给出了两条界定现象学运动范围的标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方法的采用”,自称是现象学家的人必须是明确或不明确地使用以下两种方法:“(1)作为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最后检验标准的直接直观(其意义尚待阐明),对这种直观应尽可能如实地给以文字的描述;(2)对于本质结构的洞察,这是哲学知识的真正可能性和需要。”②由方法上去界定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符合现象学运动这一实事,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一书的“导论”中也明确主张,“现象学一语”乃是“一般科学的哲学的方法之名称”,①又说,“正确地看,现象学是一个方法的概念”。②利科也曾说过,现象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还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多样实现,而胡塞尔不过是运用了其中的几种”。③将现象学运动界定为围绕某种方法而展开的哲学运动,对于厘清现象学运动的范围无疑是一种严谨而有效的做法。施氏以此为标准确定下具体的现象学人选后,依国家或地区以及人头一一对不同的现象学家的思想加以考察,并在最后一编中以“现象学方法的要点”为题对整个现象学运动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概括,算是为现象学运动找出一个“最小公分母”。这种做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失是好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几近完美的做法。但从哲学史的角度去看,又不能不说有很大的缺憾。因为方法毕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每一个现象学家之所以都愿意将现象学视为一种方法,无非是因为它可以为我所用,用来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而且目的(或者说问题)本身对方法有一限定的作用,你总不可能用研究木头的方法去研究白日梦。 因此现象学家之所以共同选择了现象学的方法,也说明,他们要处理的问题有某种相近性或相关性(当然是在一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如果单纯以方法为中心去研究现象学运动,那么,对于这场运动所要处理的问题、④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一种思想上的相互激荡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一种真正现象学意义的“精神空间”——现象学运动本身正是在这个精神空间中展开,并不断地扩展着这个空间的范围——便无从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在这一精神空间开展的现象学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话”(有声与无声的对话),以及在种种“对话”中所形成的“合声”(或者说趋势、潮流)更是难得一显了。 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对现象学运动的研究,我把描述现象学运动的“精神空间”定作自己的研究目标。当然具体写起来,难免犯下“眼高手低”的毛病,而且,由于学力与时间之不逮,很多重要的问题(如时间性问题等等)、很多重要的人物(如舍勒等等)都没得到讨论,即便讨论到的人物与问题,其探讨之力度与深度也难免有火候欠佳之嫌。我把它抛出来,更多地是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与赐教。 是为绪言。 -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九辑)
现象学的哲学与方法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以“面对实事”的思维态度和“工作哲学”的解析风格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以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现象学精神,如今已在人文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是中国(两岸三地)现象学和哲学研究界第一次合作努力的成果。它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进行现象学的探讨。它要回答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什么是现象学精神?它能否以及如何与中国人文精神相结合? -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well known as the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and as the teacher of Heidegger, was unable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framework of a classical metaphysics of subjectivity. Supposedly, he never abandoned the view that the world and the Other are constituted by a pure transcendental subject, and his thinking in consequence remains Cartesian, idealistic, and solipsistic. The continuing publication of Husserl's manuscripts has made it necessary to revise such an interpretation. Drawing upon both Husserl's published works and posthumous material,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corporates the results of the most recent Husserl research.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roughly following the chr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thought, from his early analyses of logic and intentionality, through his mature transcendental-philosophical analyses of reduction and constitution, to his late analyses of intersubjectivity and lifeworld. It can consequently serve as a concise and updated introduction to his thinking. -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In this fresh translation of five lectures delivered in 1907 at the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Edmund Husserl lays out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knowledge, indicates the requirements for its solution,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troduces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of reduction.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this text affords a unique glimpse into the epistemological motivation of his work, his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central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s that will later go by the names of '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 the 'noema', and the like. As a teaching text,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is ideal: it is brief, it is unencumbered by the technical terminology of Husserl's later work, it bears a clear connection to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s formulated in the Cartesian tradition, and it is accompanied by a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hat clearly spells out the structure, argument, and movement of the text. -

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
本书立足于国际舍勒研究界,首次尝试在伦理思想史的大背景下,结合康德、胡塞尔和当代自身意识理论等思想,系统重构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的现象学伦理学。全书基于对相关思想家的原著、部分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以及大量研究文献的仔细分析,着力展示了: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是现象学的,以及这一现象学伦理学的系统形态。 本书的上篇在康德、胡塞尔的思想背景下研究了舍勒的静态的、抽象的本质性现象学;下篇则在当代自身意识理论的视域中研究了舍勒的动态的、具体的人格现象学。而这两个方面分别构成了舍勒现象学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两个层次(质料先天主义和价值人格主义)的基础。根本上,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既包含以探寻价值的现象学-存在论本质为主要论题的现象学“元伦理学”,也包括以回答苏格拉底问题为任务的现象学的“规范伦理学”,前者奠基于静态的本质描述现象学,后者则奠基于动态的人格现象学。“元伦理学”构成了舍勒质料价值伦理学的基础,“规范伦理学”则代表着质料价值伦理学的最终归宿。 就细节方面而言,本书首次系统梳理了休谟、康德、波尔扎诺、胡塞尔、舍勒以及石里克等在质料先天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传承与争执,等等);在汉语学界,本书也首次在传统自身意识理论的框架下系统谈论人格问题,首次讨论了自身感受问题以及自身感受与人格的关系问题;本书还在汉语学界首次研究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波尔扎诺转向问题,等等。 从总体上来看,本书以现象学的元伦理学和现象学的规范伦理学两个视角来看待舍勒整体的伦理学,同时,以静态和动态现象学的双重奠基来谈论舍勒质料价值伦理学的这两个部分,并系统概括舍勒现象学的基本理解、基本特征以及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在国际舍勒研究中首次做出的尝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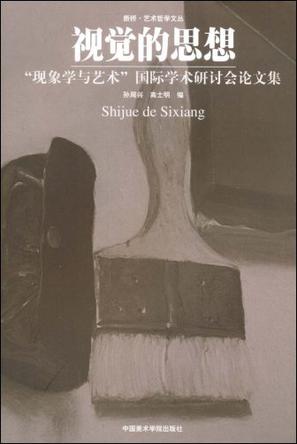
视觉的思想
《视觉的思想:“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18日至1O月21日,中国杭州)的论文集,收录了会议的大部分论文(另有七篇文章构成一组,收入《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六辑,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次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现象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德、法、日等国家和地区的近五十位哲学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代表主体是中国学者,会议工作语言是汉语。 与以往的现象学哲学会议或者一般哲学会议相比较,本次会议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这是国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家与哲学家的聚会。如通常所见,艺术家倾向感性,哲学家趋于理性,虽然在今天的思想视野里这个说法已经大成问题了,但从这两类人的举止行状、思想方式、表达风格上看,这个差别恐怕仍旧是存在的。我作为本次会议的学术策划人和组织者,事先一直怀着一种担心,恐怕两方面弄得不可开交。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这两类人还是可以交流的,也表明艺术与哲学之间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 其二,本次会议是在杭州市印象画廊里举行的。在一个地下的画廊里搞一个艺术一哲学的学术会议,以后会不会有我不敢说,但至少在我们这里是前所未有的。会议主办者在画廊里做了一个名为“大地上——具象表现绘画艺术展”的展览。华裔法籍著名艺术家司徒立先生甚至专门从巴黎弄来了一批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予以展出,加上中国美术学院具象表现绘画工作室的几位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画展。置身于绘画艺术的背景里讨论艺术现象学的问题,味道自然有点特别。 因为有了上面两点,本次会议就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也是一次有趣的大会。据我所知,本次会议所收论文的数量在历届现象学年会中也是名列前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