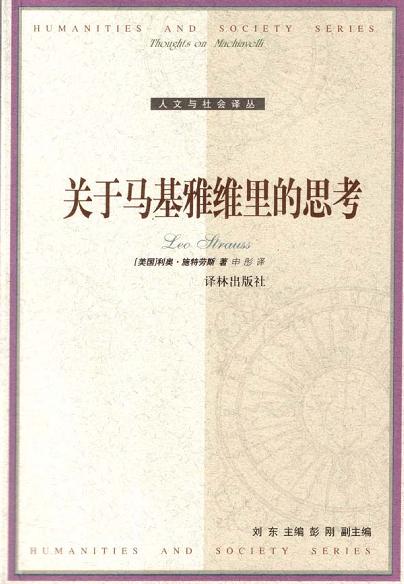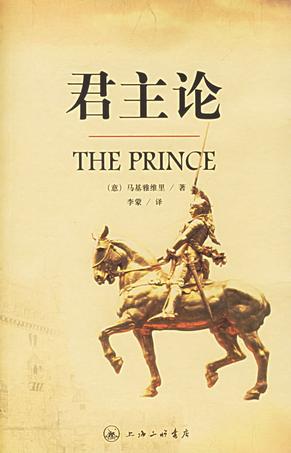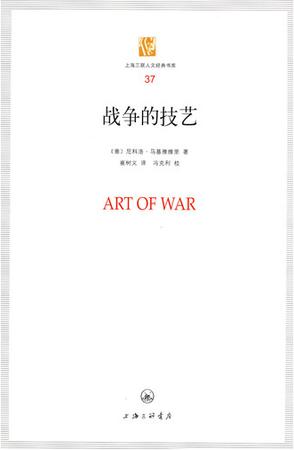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国]利奥·施特劳斯
简介:
在本书中,利奥·施特劳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精细入微的考察,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作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传授雅恶的第一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拯救祖国与拯救自身灵魂之间的矛盾抉择,构成了有着明显价值判断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
前 言
我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53年秋季那个学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四个讲座,本书就是那四个讲座经过充实的稿本。
我感激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主席杰罗姆·G.克尔文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机会,得以陈述我对马基雅维里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也感谢沃尔格林基金会在文书誊写方面所提供的慷慨协助。
本书第二章曾经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57年3月号)发表过。
利奥·施特劳斯
伊利诺斯,芝加哥
1957年12月
引 言
假如我们承认,我们倾向于同意关于马基雅维里传授邪恶这个老派的简朴观点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是在危言耸听;我们只会使得我们自己暴露在敦厚质朴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嘲讽面前。确实,还有什么别的描述,能够适用于一个鼓吹如下信条的人:希冀牢固占有他国领土的君主们,应该对这些领土原来的统治者,满门抄斩;君主们应该杀掉他们的敌手,而不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蒙受掠夺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已被铲除的人,则不可能这样做了;人们对于谋杀他们的父亲,与丧失他们的祖传财产相比,忘却得更快;真正的慷慨宽宏在于,对于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于他人的所有物,慷慨大方;导致福祉的不是德行,而是对于德行与邪恶加以审慎的运用;加害于人的时候,应该坏事做尽,这样,对伤害的品味瞬息即逝,伤害所带来的痛苦也就较轻,而施惠于人的时候,则应该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地赐予,这样,恩惠就会被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得胜凯旋的将军,如果惧怕他的君主可能会鸟尽弓藏,恩将仇报,那就可以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发起叛乱,以惩罚君主的背恩忘义;如果一个人,必须在对人施加严重的伤害与对人施加轻微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定夺的话,他就应该选择施加严重的伤害;一个人对于他所图谋杀害的人,不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我要用它杀死你”,而只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这是因为,一旦有枪在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假如千真万确,只有一个邪恶的人,才会如此堕落,在公共领域与私人交往中提倡明火执仗的强横行径的话,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邪恶的人。
马基雅维里确实并不是表达类似上述观点的第一人。这种观点属于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它们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但是,马基雅维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哲学家,不惜将自己的名字,同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公然联系起来,以至于他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作为这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代名词。他恶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弃义背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卡利克勒斯和特拉西马库斯,秘室晤对,阐发邪恶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柏拉图笔下的人物;古代雅典的战争使节,在米洛斯岛普通民众不在场的情势下,宣扬同样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古典思想家隐秘地、而且怀着明显的厌恶态度所揭示的那个腐化堕落的信条,马基雅维里明目张胆地、欣然自得地加以宣扬。古典思想家假口他们笔下的人物所讲的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话,他无所忌惮,以他自己的名义公然道出。只有马基雅维里一个人,敢于用他自己的名字,在一本书里,阐发这个邪恶的信条。
尽管如此,无论这个老派的简朴判决,可以是多么真实,然而它却都不是囊括一切、详尽无遗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瑕疵与不足,为我们时代的饱学之士们所提出的那些更为精致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我们被告知,马基雅维里远非居心叵测,刻意传授邪恶,他其实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或者是社会生活的一位讲求科学方法的研究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我们可以考虑,趋求时尚的学者们,究竟是否没有比老派的简朴立场,远为可悲地步入了歧途;或者说,被趋求时尚的学者们所忽略的问题,究竟是否不比被老派的简朴立场所忽略的问题,远为重要,尽管被那些精致的看法所无视的某个重要问题,高尚质朴的人们确实可能并未给予充分恰当的说明,因而作出了错误的阐释。这不会是如下那种情况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即“一点肤浅的哲学”所铸成的大错,在不谙哲理的大众那里,却不会发生。
将马基雅维里这个思想家描述成一位爱国者,是混淆视听的一个误解。他其实属于一种类型独特的爱国者:他对于拯救他的祖国,比对于拯救他自己的灵魂,更为牵肠挂肚。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前提是在祖国的位置分量与灵魂的位置分量之间,作出全面的权衡。正是这种全面的权衡,而不是爱国主义,才是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正是这个全面的权衡,而不是他的爱国主义,为他造成了显赫声誉,使他桃李满天下。他的思想的实体内涵,不是佛罗伦萨,甚至也不是意大利,而是普遍适用的。它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着的人们,而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涉。将马基雅维里视为科学家,至少跟将他视为爱国者同样混淆视听。讲求科学方法的社会生活研究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作出“价值判断”,可是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中,则充斥着“价值判断”。他对于社会所作的研究,属于规范性的。
但是,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的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所以对于自身的爱,往往倾向于变得关注自身的为善,或者关注对于善的要求的遵循。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在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诉诸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无法使我们妥当地处理一个只是貌似邪恶的事物;这样做只会使我们混淆是非,看不清真正的邪恶。
至于研究社会生活的“科学”方法,它的很多倡导者,将它的源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那里;这种方法随着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人所赖以定位取向的道德界限的抽象化而出现。这样看来,所谓“科学”分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在于道德上的麻木愚钝。这种麻木愚钝,与腐败堕落不能等量齐观,然而它必然要强化腐败堕落的力量。在芸芸众生的小人物那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这种道德愚钝,归因于某些才智禀赋的不存在。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这个宽厚慈悲的解释却无法成立,他太深思熟虑了,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太慷慨大度了,不可能不把自己做的事,向他的理智的朋友们加以承认。
我们如同很多前人那样毫不踌躇地宣称,而且我们随后将要试图论证,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不道德的,也是无视宗教原则的。我们并熟知学者们赖以支持与此相反的论断所引证的论据;但是我们质疑他们对这个证据所作的阐释。撇开某些其它考虑不谈,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太容易心满意足了。他们满足于关于马基雅维里是宗教的朋友的说法,原因是他强调了宗教的实用性和不可缺少的属性。他们对于一个事实,完全不加注意,即他对于宗教所作的褒扬,只不过是我们可以暂且称为他对宗教真理的全然漠视的另外一面而已。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自己,即使不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吸引人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民俗传说,也往往是把宗教仅仅理解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部类而已,更不要说那些对宗教笃信的人们了,他们满足于宗教所被赋予的任何表面上的裨益。对于马基雅维里关于宗教的判断,以及他关于道德的判断,这些学者之所以作出错误的阐释,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他们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所作的表面上客观超然、虚怀若谷的研究,其基础在于他们对他的原则采取固执教条、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们之所以看不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邪恶性质,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传统的继承者,是因为他们,或者他们导师的已被遗忘的导师们,已经被马基雅维里所腐蚀。
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从所有的实践意义上来说,这都意味着,除非我们为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复活西方世界的前现代遗产,既复活《圣经》的遗产,同时又复活古典遗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对马基雅维里作出恰如其分的把握,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面向未来,去观察一个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的、新异陌生的马基雅维里,而不是从今天的视角面向过去,观察一个业已古老的、业已成为我们中一员的、从而几乎是道德上善的马基雅维里。这个过程,即使只为了掌握一种纯粹的历史定位起见,也是必需的。马基雅维里所熟悉的,是前现代思想:前现代思想发生在他之前。他不可能熟悉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思想,是在他身后才出现的。
这样我们就认为,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尽管依然不够充实,但是确实决定性地优越于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精致观点。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而且恰恰如果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他的学说是恶魔的学说,他本人是一个魔鬼,我们也依然不能不铭记这样一条深刻的神学真理,即魔鬼其实是堕落的天使。认识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恶魔性质,意味着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认识到一种品第极高的、扭曲堕落了的高贵。当克里斯托弗·马洛将如下这个说法追溯到马基雅维里身上时,他其实是看到了这种高贵:“我认为除了愚昧无知以外,不存在任何罪孽。”马洛的判断,可以在马基雅维里本人于他的两部伟大著作的献辞中谈到他最可珍贵的财富时所作的表示那里得到印证。我们对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抱同情态度,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简朴观点是健康有益的,而且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予以认真重视,我们就不可能对于马基雅维里身上真正令人钦羡的品格素质,作出恰如其分的应有认识:他的思想的勇敢无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广阔,以及他的语言的优美雅致。能够帮助我们窥见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的,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鄙夷轻怠,也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漠然不顾,而是从那个简朴观点出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升华。阻碍着我们理解任何事物的,莫过于对彰明较著的事物,对事物的表面,采取想当然的态度,或者采取看不起的蔑视态度。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而且只有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所赞助的一系列讲座中,来讨论马基雅维里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国家,奠基于明显与马基雅维里主义相对应的原则之上。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世界上最为闻名遐迩的国度的缔造者,其实是一个同室操戈的弑弟罪犯:政治上的伟大,其基础必然在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罪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托马斯·潘恩的说法,那么旧世界所有政体的源头,都来自这个描述;它们的源头,都在于扩张征服与僭主暴政。但是,“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的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理论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着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的蔓延。”这个判断,远远没有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经不再为美国所专有,然而美国仍然是自由的堡垒。而当代的专制暴政,其源概出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概出于关于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原则。美国的现实与美国的理想密不可分,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懂得与之截然对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就不会懂得美国的体制。
但是,我们对于一个事实不能视而不见,这就是,问题其实比它在潘恩及其后继者的表述中所显现的,更为错综复杂。马基雅维里可以争辩说,美国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国度,不仅归功于它习以为常地坚守自由与正义的原则,而且同时也归功于它偶尔为之地背离这些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对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际,应该作出蹊跷的重新阐释。他可以得出结论说,诸如此类的事实为他的如下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就是,如果没有诸如雷慕斯被他的兄弟罗慕洛斯所谋杀那样的事件,就不可能造就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公民社会。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更应该有必要对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作出恰当的理解。
我们可能已经假定,马基雅维里是政治思想脉络两大根本抉择其中之一的倡导者。我们确曾假定,根本意义上的抉择确实存在,它们是永恒的,是自有人类以来就与之俱存的。这一假设,今天经常被人否认。我们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恒的抉择。他们会争辩说,恰恰是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为他们否认永恒问题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马基雅维里的问题,是一个新异的问题;它跟此前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根本不相同。这个论点,如果经过恰当阐发,就可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分量。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它只不过证明:永恒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确信的那样容易接近,那样容易触及,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对这些永恒的问题予以面对和正视。我们对于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作的批判研究,其终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重新发现这些永恒的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