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
跟传统小说不一样,在《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里,故事情节不存在,空间被最小化(发生在他的房间里)。这是布朗肖对自己的呢喃,或者更确切地说,布朗肖的对象是一个陌生的“我”。否定喧嚣的世界,作家抹掉了“我”,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意图。布朗肖写作《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仅仅是为了使之成为一个文本,成为一种文学。 这部小说的时间参照是不存在的。布朗肖寻找的是“另一个时间,一个更古老、古老得可怕的时间”。这种时间的不存在性导致了写作的重复,同时也导致了现在的不存在和“这一次的不存在”。 所以会发生什么呢?我确实想过回避,想要卸下重负托付给他人吗?更确切地说是不让自己看到那个陌生人,不去打扰他,抹掉他的足迹,从而使他所完成的事能够分毫不差地完成,从而使这件事不是为了始终处于事件边缘、事件之外的我而完成。它的发生应该像电闪雷鸣般爆发、轰响、神圣,而我能做的只有无限地接近,抓住其中的不确定,维持这种不确定,坚持住绝不退让。是在以前吗,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那个像哨所的小房间里,在那里,已经消失的我却远没有感到从自身解脱,反而觉得有义务保护这种消失的状态,维持这个状态,从而使之延续下去,永远延续下去?不就是在那儿,在不属于任何人的极度悲伤中,我被赋予了以第三人称谈论自己的权利? -

等待,遗忘
遗忘自哪里开始?记忆自哪里结束?思考遗忘,让人意识到思考自身之开始的不可能。思考遗忘就是思考记忆。这种辩证将等待置于显而易见的地方。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对话中,什么也没有说,一切都消失了。 ……“小说”、“叙事”和“批评”在布朗肖的世界里不断减弱,使得在《等待,遗忘》里仍被容许说话的只有语言本身——那不是任何人的,既不是虚构的,又不是反思的,不是已被说出者的,也不是仍未被说出者的语言,而是“在它们之间,像这片有固定空旷的地方,事物在它们潜在状态的蓄聚”。 思想静默的迷途,在等待中从自身回到自身。 通过等待,离开思想的事物回到已成迷途的思想。 等待,是不失去方向的迷途之地,是没有游荡者的颠沛流离。 -

最后之人
《最后之人》是布朗肖在文学版图上设置的又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迷宫,是他思想的转折点。向“零度写作”的转变是通过对“最后之人”的叙述实现的。“最后之人”是尼采意义上的末人,他以一张毫无表情的脸面对着黑格尔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与大循环封闭之后的历史境况。在上帝死去之后,对死亡和终结本身的描述是对残剩之物的肯定,不再有否定,在那里,一个人在场却已没有任何人了;在那里,甚至死都是不可能的,知识已是对不可能性的经验,是非知识了! 自从这个词得以受我运用,我即表达出一直以来我心中对于他的想法:他是那最后之人。事实上,他与其他人几无任何差异。他是比较隐淡,但并不谦逊,不说话便显得专横。或许应该默默地将某些想法套用到他身上,再由他自己将之轻轻地甩弃…… -

福柯 / 布朗肖
-

死刑判决
布朗肖是出了名地晦涩难懂,然而这部可以被笼统地贴上后现代主义标签的作品,却很可能是布朗肖十余部小说与叙事作品中最容易进入的一部。它有可辨的情节线索,有主要人物,甚至非常奢侈地,还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二战开始前后,法国巴黎。更诱人的是,它有一个自传体框架,包含着一个爱情故事、悬疑故事、神秘故事,或许也可以说是一个带有哥特气息的恐怖故事。如果认真起来,你还能从中读出政治寓言和圣经叙事的痕迹。那些喜欢接受挑战的读者也不会失望,因为这篇叙事仍然具有很强的先锋性。作为布朗肖的第一部“récit”作品,它开启了布朗肖对这一独特文学体裁的实验,继续着他对于“纯小说”梦想的探索。事实上,在布朗肖的所有小说与叙事作品中,《死刑判决》或许是迄今吸引到最多评论与研究的一部,足见作品的魅力和它在布朗肖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每当坟墓向我敞开双臂,一个强大的念头都会在我心中升起,把我带回到生命这一边,是什么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是我的死亡发出的冷笑。但要知道,我即将前往之地,既无劳作,也无智慧、欲望与争斗;我将进入之所,无人进入。这就是最后一搏的意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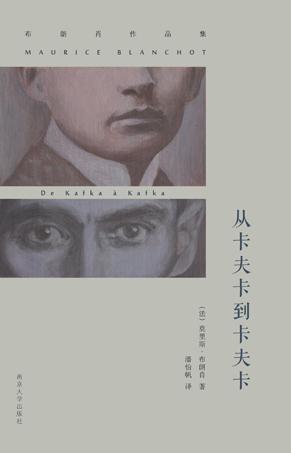
从卡夫卡到卡夫卡
《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汇集了13篇布朗肖论卡夫卡的文章。从卡夫卡开始,到卡夫卡结束,这是一部向文学大师卡夫卡致敬的书。卡夫卡对布朗肖的影响在布朗肖的著名文论《文学空间》里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当写作成为“祈祷的形式”,毫无疑问写作是出自其他形式的,即使在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界的视景下,写作已经停止成为作品,卡夫卡在宽恕的时刻认出了文学的追寻者,并且明白不应该再写了——一个字也太多! ……卡夫卡想毁掉其作品,可能是因为他认为那必会倍增众人的误解。在此混沌的研读过程里,我们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就是映射在某些残篇、未尽作品之上,被所识与被所掩的部分光线,因而,总是更加加剧了那些作品的分裂,最后碎裂成细尘那般大小,如同总是与道德脱不了干系的遗作,在面对这类多半遭到长篇大论的评论所侵袭的寂静之作,这类成为可以无限发表题材的未刊之作,这类沦为历史注脚的永恒之作时,不得不扪心自问,是否卡夫卡自己,早就在辉煌的胜利中,预感到同等程度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