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高者
《至高者》是一部向自身叙说并且转向小说自身的小说。它不断地否定自身,重构自身。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的首要需求和焦虑验证了一种自我的追寻。他试图抹掉自己的犯罪证据。他的话语主要是存在,一种归属于大众的感觉,一种对世界和律法的惊异和崇拜。他经常有一种介于梦幻和现实之间的生病的印象,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垂死的感觉。在他遥不可及的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这种垂死的感觉会一直陪伴(折磨)着他。这部小说也因此是一次对真实的追寻。 -

灾异的书写
布朗肖晚年思考了“奥斯维辛”,但他独特的思考在于把它当作灾异或灾变事件。中性意义上的灾异还不是灾祸,灾异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在灾异中,只有灾异如同解体的星际在警醒着,“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它并不考虑存在还是非存在” 。它只是拒绝与抵制一切现成之秩序。而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所有的面容只导致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每个人已成为集体的匿名的脸,人甚至害怕自己的面容,集中营没有位置给面容。 ———————————— 为何所有的不幸,完结的、未完结的,个人的、非个人的,现在的、永远的,有这样一个暗示,并不停地提醒它,被载入历史却又没有日期的不幸,一个已经缩小到几乎从地图上擦除的国度,然而它的历史却超越了世界历史?这是为何? -

来自别处的声音
《来自别处的声音》汇集了布朗肖晚年所写的几篇重要文论。论路易-勒内·德·福雷的诗歌的卓越文章将诗人从被遗忘的作家队伍里拉出来,并且阐明了这位诗人及其作品的价值。福柯写过一篇名为《外界思想》的文章,论及布朗肖的虚构作品。《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以半虚构、半评论的形式对福柯的友谊做出了回应。 这声音不在“此地”(此地是他乡),而是来自“别处”。布朗肖以旁观者的姿态经由外部来反思自身,对其他作家、哲学家的评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 当未知对我们质疑的时候,当话语向神谕借声音——这声音不谈论此刻,却迫使倾听之人竭力摆脱现状,以求回归自己,仿佛还未成就的自己——的时候,这话语往往偏执、傲慢、苛刻,无视我们,将我们从自己那里夺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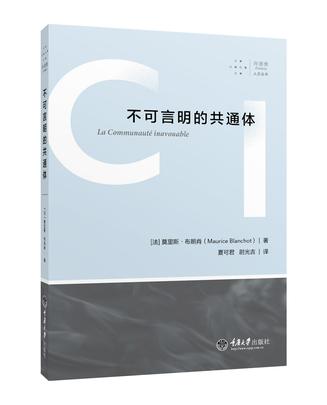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
编辑推荐: •本书是当代法国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莫里斯•布朗肖的晚期代表作。 •在这本小书里,布朗肖直面“共通体”(又译“共同体”)这一貌似简单、实则繁复的思想,他紧随南希、巴塔耶和杜拉斯等人的思考,以其一贯的幽晦风格对此展开了最为澄澈的言说。 •如其标题所言,此书保持着某种不可言明的特点。如若必须对此展开言说,我们该使用什么样的言语?布朗肖认为,“这是这本小书托付给其他人的问题之一,与其指望他们做出回答,不如让他们选择把它带在身上,或许还拓展它。” •它物理体量上的小,与它思想容积上的大,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意义上,这本小书同时也是一本“大书”。 内容简介: 一方面,《不可言明的共通体》所回应的共通体的迫切要求正在这个世界里遭到遗忘,甚至这一遗忘的后果也难以察觉;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源于一个隐秘的共通体,那既是书文的共通体,也是爱的共通体。阅读共通体的书写,首先就面对着共通体的缺席。然而,至少为了试着在黑暗中没有方向地向着这一共通体接近,有必要倾听几个不愿言明自身的模糊的声音。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否定的共通体”,下半部分为“情人的共通体”。如同布朗肖的绝大部分写作,这本书表面上也充当了另两位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论:让-吕克•南希的哲学论文《非功效的共通体》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记述《死亡的疾病》。但根本的问题,共通体的问题,就像在南希那里,首先指向了乔治•巴塔耶。在这场无形的谈话中,巴塔耶首先以隐晦的姿态,提出了共通体的要求。在“二战”期间的“无神学大全”的写作里,巴塔耶再次提出了与迷狂体验有关的“交流”的问题,并在手记里留下了让南希和布朗肖着迷的关于共通体的明确定义:“否定的共通体”。虽然南希对巴塔耶的研究重新点燃了共通体之思的火花,但这个可以说从巴塔耶文本的裂隙中寻得的定义依旧神秘。围绕着这一定义的晦暗光芒,布朗肖再次把共通体引入了外部的黑夜。 杜拉斯的记述就被这个黑夜笼罩、包围,并且,男人和女人达成的情人的共通体,就暴露在这夜晚的时间下。布朗肖试图在此证实的,恰恰是这个浸没了共通体的黑夜所具有的力量,因为这力量在消解个体成员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巴塔耶意义上的真正的共通体:共通性的丧失也是共通体的铸成。为了理解这看似悖谬的论断,为了进入共通体的这极为陌异的关系,有必要唤起列维纳斯的观点,恢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根本的不对称性。只有他者的死亡能让“我”走向共通体的敞开,只有走向绝对他异的外部,把自身交给无限的黑夜,“我”的有限的孤独才不会一个人承担。 共通体总在铭写秘密的友谊。巴塔耶的友谊,他自己最早为《有罪者》一书定下的副标题,纪念着他同那些没有记录名字的朋友们的友谊;布朗肖的友谊,他为1971年的文集所定的标题,向包括巴塔耶在内的朋友们发出了敬意(并且,正是纪念巴塔耶的文章决定了这个题目)。而这本小书,凭借其批评的工作,再一次召唤了布朗肖同巴塔耶、同杜拉斯、同列维纳斯、同南希的多重友谊。情人(amants)的共通体,不也是友人(amis)的共通体吗?因为共通体就是爱(amour)的见证,虽然这爱也飘散在逝者的笑容和生者的泪水当中,在缺席的沉默者和到场的言说者之间,触摸那不可穿透的永恒之夜的界线。 -

未来之书
布朗肖以一种充满激情和焦虑的学识向我们谈论了普鲁斯特、阿尔托、布洛赫、穆齐尔、亨利·詹姆斯、萨缪尔·贝克特、马拉美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甚至是将来某一天的最后一位作家。《未来之书》汇集了布朗肖为复刊后的《新法兰西杂志》写的文论,这些文论被包括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等在内的新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固定阅读,对后来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始终在路上,始终已成过去,始终在场于某个开始——陡然一下让人屏住呼吸,但却铺展开来似一场回归,似永不停息一再开始——歌德说:“哎,在前世里,你大概是我的姐妹或是我的妻子。”——这就是叙事要走近的事件,它虽颠覆了时间关系,却显示了时间,让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这是叙事本身的时间,用转变叙述者时间的方式进入叙述者时间,在这变化的时间里,在想象的同一时间内,在艺术试图实现的空间形式中,种种殊异而短暂的迷醉同时而生。 -

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是犹太人名,布朗肖的好友列维纳斯的弟弟就是名叫亚米拿达,他在布朗肖的这部《亚米拿达》出版前不久在立陶宛被德国纳粹杀害。除此之外,也有叫这个名字的圣经人物。亚米拿达这个名字的含混性将布朗肖的小说人物保持在一种本质的无名状态之中:亚米拿达没有名字。 只有在这最后一个房间里,在整栋房子的最高处,黑夜才会完完整整地发生。它总是那么美丽,带给人平静。可以不需要闭上眼睛就舒服地释去白天无处安放的倦意。同样令人着迷的,是从外部的黑暗中发现自己内心长久以来用死亡叩击真相的相同的黑暗。这黑夜有些特殊之处。它既不伴随着睡梦,也不见预兆般的念头来偶尔取代幻想。它自己就是一场辽阔的梦,非它所覆之物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