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太阳,向光明 :朱厚泽文存,1949-2010
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深刻洞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症结 本书是一位卓越思想家的文集。1949—2010 年间朱厚泽留下了大量文章、讲话及访谈录,本书从这些文稿中汇集了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经济工作、文化及宣传工作、环境问题、二十世纪至今人类社会进程的思考,探讨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路径,以及对全面深刻的改革和长期持续发展的忧思。 当下语境,时代命题,历史眼光,洞见发展的症结所在,明白清晰的语言表达, 诸如这些方面都使得本书具有极高的价值。 -

十億民工進城來
決定中國未來興衰的關鍵,就在城鎮化! 中國城市擴張有多快? 中國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都市人口增加了兩億,平均每年增加約一個澳洲的人口。到2030之前,中國還會有三億農民走向城市,相當於一整個美國的人口。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高達十億,地球上每八個人就有一個住在中國城市裡。 一百兆商機的未來! 據估計,因為城市人的收入與消費均是農村人的三至四倍,中國城鎮化(即城市化)將可以帶來一百兆台幣的商機。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曾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然而,如果稍有差遲? ──肆意擴張的城市將併吞中國有限的耕地。 ──巨量人口與車輛將癱瘓城市交通。 ──地方政府因為無力負擔社會福利而破產。 ──官商勾結土地兼併造成上萬農民流離失所。 ──中國的經濟會因城鄉失衡而陷入停滯。 ──極度的貧富差距會導致政治動亂。 ──空氣汙染瀰漫人口超過百萬、千萬的大城。 ──無數外觀毫無美感、樣式千篇一律的冰冷城市。 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 一個富裕而穩定的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將會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穩定力量,但一個個破產、騷亂、擠滿憤怒的失業人口的中國城市,將是人類的災難。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說,「21世紀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有兩項,一是美國的科技創新,二是中國的城鎮化。」 中國的農村與城市,農民、民工與都市人口究竟將何去何從?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威脅還是機會?《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中為你深度報導分析。 【精采內容】 城鎮化是中國必走的路 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移動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也是必然的政策目標。 對個人來說,城市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更舒適的現代化生活、與更新潮的娛樂與消費。在本書中,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指出,以2010年的重慶為例,城市居民的可消費金額是農民的三倍,差距高達一萬三千人民幣。 這也是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至今,五億中國農民選擇進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討生活的主因。可悲的是,僵化、嚴厲的戶口制度逼使他們只能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在城市裡享有醫療保險或退休福利的民工不到20%;他們的子女能唸公立學校的人數不到40%。但是,他們還願是前仆後繼地來到現代化城市,只因為這裡收入更高…… 另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也是一個中國政府樂見的現象,並名之為「城鎮化」。儘管媒體都大幅報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已經太過擁擠,導致嚴重的交通癱瘓與空氣汙染,且過度的城市投資已經造成諸如鄂爾多斯「鬼城」等泡破經濟的前兆,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人口竟然還不夠! 其背後的策略考量是:中國只有全球7%的可耕地,卻得養活20%的人口。為了提高農地使用效率,中國政府不得不大力推動城鎮化,目標是在2030年前,繼續將兩億五千萬農民移入城市,將城鎮化比率推升到65%以上,使城市人口達到十億之眾。果真如此,中國每戶農家的耕地將增加到一公頃。根據日本與台灣的經驗,每農家有一公頃耕地是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 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就任記者會上就宣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城鎮化的負面後果 然而,城鎮化工程背後隱含了無數的難題與危機,其中有的已經爆發,譬如: 1. 空氣汙染:符合WHO所訂二氧化硫與二氧化氮標準的中國城市不到20%。 2. 交通堵塞:北京已有五百萬輛私人轎車,北京人花在通勤上的時間全球第一。 3. 投資氾濫與城市的無度擴張:在1980至2010年間,中國城市新區擴大三倍有餘,但同期間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20%。 4. 工業區擠壓住宅區導致的房價飆漲:在2006至2008年間,工業用地占了所有新城市建設用地的45%,住宅用地卻只占20%。 當然還有不少尚未爆發,但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潛伏危機。譬如,地方城市為了加速開發以催高經濟數據(這是在中國官場升官的重要指標),經常過度借款、盲目投資,中國銀行業的壞帳總額很可能將於2014年達到兩兆人民幣…… 土地兼併與左右之爭 當然,所有危機與弊病當中,最怵目驚心、駭人聽聞的還是土地兼併的問題。無論是為了私利還是公益,中國地方政府為了建設城市常無情地驅離在地農民。作者指出,自地方政府於1990年代開始收購農地以來,每年有約二十萬公頃遭徵收,已有四千萬到五千萬農民失去土地。2011年十二月在廣東烏坎村爆發的官民衝突,就是在這背景下誕生的…… 從土地問題切入,我們進一步看到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財產權。西方觀察家與中國的改革派人士無不極力呼籲賦予老百姓更完整的財產權保障,讓老百姓能夠自由地買賣他們的土地財產,才能避免官員的剝削。然而,另一批同樣關懷底層民眾福祉的左派思想家卻擔心,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前,鼓勵老百姓自由買賣土地只會陷民於水火之中,並合理化了奸商與貪官對農民的欺詐……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化的問題極度的複雜,任何片面的觀點都不足以一窺全豹。所幸,《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一書中試圖對中國城鎮化做出比較完整、客觀的報導。 「鬼城」不足為懼 唐米樂有記者的敏銳觀察,也有學者的冷靜分析。他一方面讚嘆中國政府已達到的驚人成就,譬如在中國城市裡我們幾乎找不到在印度或南美大城裡那種慘不忍睹的貧民窟(感謝嚴厲的戶口制度)。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在絢麗的城市光彩之下,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且就算在城市裡,也有多達兩億五千萬的中國城市居民缺乏基本的保障。他們遭受歧視,過得沒有尊嚴的生活,且屢遭貪官汙吏欺壓。改革絕對是必須的。 除了提供全面、持平的介紹之外,作者也不乏驚人之洞見。儘管吳敬璉、陳志武等中國權威經濟學家都已憂心忡忡地指出,「鬼城」的出現象徵了投資氾濫的中國經濟即將出現泡沫,唐米樂卻大膽斷言,以中國人口規模之巨、城市住房需求之殷,「鬼城」現象只會是暫時的。唐米樂估計,中國的住房根本建得太少,「大約還短缺七千萬個單位。」 中國城鎮化的成就與難題究竟何在?它會是一個危機還是希望?全球經濟是否能夠從十億的中國城市居民口袋中獲益?唐米樂的大膽樂觀有沒有根據?讀者可以從《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獲得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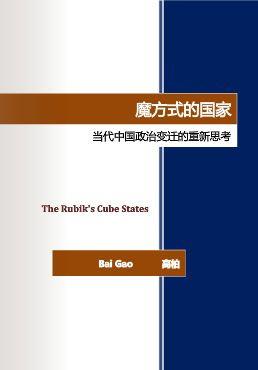
魔方式的国家
在本书中,高柏清楚地梳理了解释“中国谜题”的三种流派:崩溃论、民主化论和延续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可以被看作是魔方式的六面体,一旦一面被打破,则会出现全盘的支离破碎的景象。这六面是:威权主义国家、掠夺式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统合主义国家。 -

山寨中国的终结
中国能否通过创新,走出长期经济放缓的困境? 雷小山认为可以。 毫无疑问,雷小山并不是唯一认为中国企业正在步入创新阶段的人。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把4家中国企业(联想、小米、腾讯和华为)纳入其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的50家企业榜单。 雷小山认为,中国如今将开启创新之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而过去它之所以没这么做,也主要是还不需要。 在《山寨中国的终结》中,雷小山写道,在一个基本商品供应不足的国家,发展最先进技术的动力往往不足。如果靠山寨就能赚钱,谁还会去关心技术创新?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 在赢得向国内消费者提供基本商品的战役后,如今,中国企业被迫转向创新。由于供应基本商品这颗“低垂的果实”已被采摘,这些企业不得不开始在中国或国外市场攀爬价值链的更高端。 那么,这些转型的中国故事是个例,还是全局?创新力和个人主义是否正在亚洲崛起? 在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为了获得贴近事实的观察视角,雷小山与普通消费者、公司高管、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创始人,甚至是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而言,唯一确定不变的,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快速改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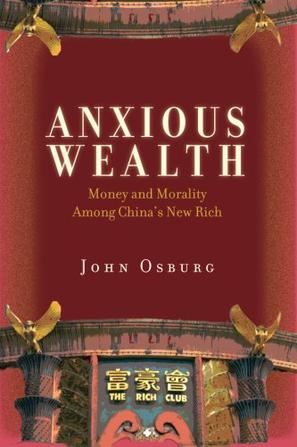
Anxious Wealth
Who exactly are China's new rich? This pioneering investigation introduces readers to the private lives—and the nightlives—of the powerful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redefining success and status in the city of Chengdu.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three years, anthropologist John Osburg accompanied, and in some instances assisted, wealthy Chinese businessmen as they courted clients, partn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Drawing on his immersive experiences, Osburg invites readers to join him as he journeys through the new, highly gendered entertainment sites for Chinese businessmen, including karaoke clubs, saunas, and massage parlors—plac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ater to the desires and enjoyment of elite men. Within these spaces, a masculinization of business is taking place. Osburg details the complex code of behavior that governs businessmen as they go about banqueting, drinking, gambling, bribing, exchanging gifts, and obtaining sexual services. These intricate social networks play a key role in generating business, performing social status, and reconfiguring gender roles. But many entrepreneurs feel trapped by their obligations and moral compromises in this evolving environment. Ultimately, Osburg examines their deep ambivalence about China's future and their own complicity in the major issues of post-Mao Chinese society—corruption, inequality, materialism, and loss of trus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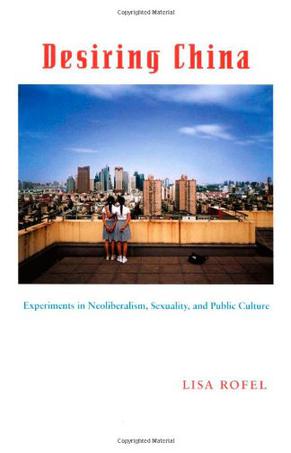
Desiring China
Through window displays, newspapers, soap operas, gay bars, and other public culture venues, Chinese citizens are negotiating what it means to be cosmopolitan citizens of the world, with appropriate needs, aspirations, and longings. Lisa Rofel argues that the creation of such “desiring subjects” is at the core of China’s contingent, piece-by-piece reconfigur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to a post-socialist world. In a study at once ethnographic,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she contends that neoliberal subjectivities are create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desires—material, sexual, and affective—and that it is largely through their engagements with public culture that people in China are imagining and practicing appropriate desires for the post-Mao era.Drawing on her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mong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Hangzhou and Beijing, Rofel analyzes the meanings that individuals attach to various public cultural phenomena and what their interpretations say about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post-socialist China and their roles within it. She locates the first broad-based public debate about post-Mao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sionate dialogues about the popular 1991 television soap opera Yearnings. She describes how the emergence of gay identit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reveals connections to a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brings urban/rural and class divisions to the fore. The 1999–2001 negotiations over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 controversial women’s museum; the ways that young single women portray their longings in relation to the privations they imagine their mothers experienced; adjudications of the limits of self-interest in court cases related to homoerotic desi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nsumer fraud—Rofel reveals all of these as sites where desiring subjects come into 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