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
本书以“家庭罗曼史”指称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图像,这种家庭秩序的图像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调。作者借着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阐述这种政治理念;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彻底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呈现给读者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典范之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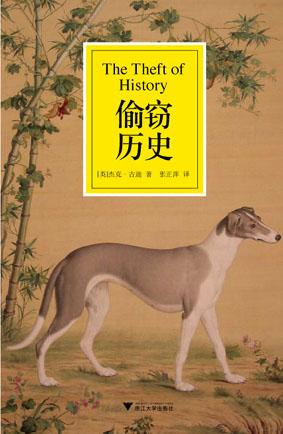
偷窃历史
杰克·古迪教授的作品一直致力于批判无孔不入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目前他仍然在努力进一步扩大这种批判的影响力。古迪教授还检验了西方成就中“偷窃”自其他文明的创造物,尤其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爱。《偷窃历史》详细地讨论了很多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埃利亚斯、还有其他著名的充满争议的学者,如布罗代尔、Moses Finlay 和佩里·安德森。古迪在本书中采用了一种研究跨文化现象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更成熟的基础来评价多元的历史成就,并替代了已过时的、中西方简单差异的方法。该书的读者群包括了历史学者、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范围非常广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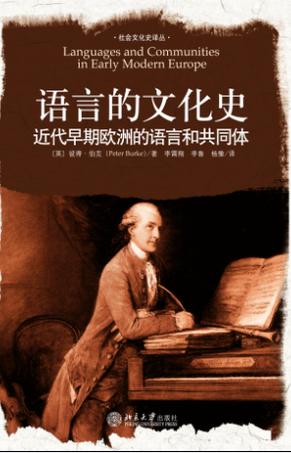
语言的文化史
在本书中,彼得·伯克将带领我们探索从印刷术发明到法国大革命之间欧洲语言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书面的、口头的,不断交融的、彼此竞争的……语言,作者具体而微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代的语言纷乱而异彩纷呈的面貌。 本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地区、教派、职业、性别乃至民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中,语言不仅是区分“他者”的工具,同样也是确认“自我”身份的途径。语言间的竞争同样引人注目。曾经至高无上的拉丁语与逐渐勃兴的地方语言之间、不同的地方语言之间争夺统治地位的竞争构成了始终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的文化潜流,成为近代历史进程中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作为当代第一流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再次展示了他贯通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出众技巧,以及吸纳整个欧洲的宽广视野。无论是对欧洲历史与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关注“语言史”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都能从本书的阅读中的得到启迪与乐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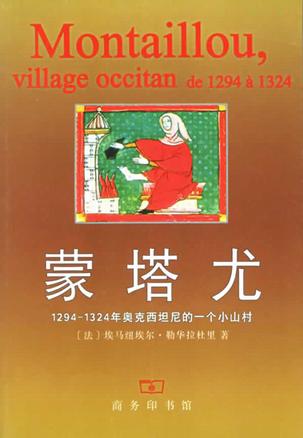
蒙塔尤
转自:http://www.qiji.cn/books/detailed/127.html 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此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像现代侦探一样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 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并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并以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 -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人们通常把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相割裂,而“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彼得·伯克却找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伯克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欧洲1500至1800年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形成后来的那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在独享精英文化的同时也分享着大众文化:“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可能会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仆人。她将唱着民谣将你送入梦乡。因此,大众文化是每个人的文化,对所有的人开放的文化。精英同样有另一种文化,主要是对上层社会成年男人开放的文化。……尽管存在两种文化,但不是一边是大众文化,另一边是精英文化,而是一边是所有人的文化,另一边是部分人的文化。” 本书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把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风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涵盖的空间西起爱尔兰的戈尔韦城,东到乌拉尔山脉,北及挪威,南达西西里;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读者将会看到一个流浪艺人的世界:游吟诗人、小丑、变戏法者、江湖郎中、流浪演员和故事歌手;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故事、戏剧以及节庆的仪式。从大众文化中英雄、恶棍和傻瓜的形象中,读者可以看见不善言辞的群体(工匠、农民、牧羊人、矿工、水手、仆佣、乞丐、窃贼以及他们的妻子与儿女)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如何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塑造。 当上层阶级终于发现大众文化对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的本质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退出大众文化并用精英文化来压制和改革大众文化。本书以拟人化的“狂欢节”和“大斋节”之间的战斗形象地浓缩了大众文化被扑灭的过程。作者的结论是饶有兴味的: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正是在它被扑灭之后又被精英文人和学者当作了“重新发现”的主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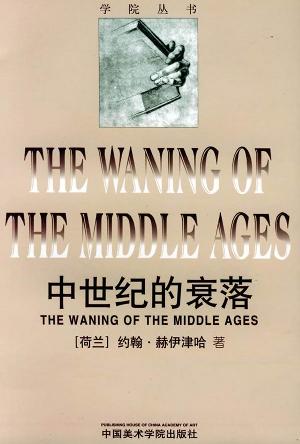
中世纪的衰落
《中世纪的衰落》研究的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是中世纪文明的结束阶段。作者正是本着上述观点,试图真正理解凡·艾克兄弟及其所处时代,亦即试图从它与当时时代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而现实已经证实,那个时代文明的种种形式中所共有的一点,就是它们均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更甚于它们与正孕育的未来的联系。因此,那个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单对艺术家用如此,对神学家、诗人、史学家、君王和政治家也是如此,都应被当作是对过去的完善与终结,而非新文化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