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狐狸洞话语
李欧梵的随笔集。“刺猬型的思想家只有一个大系统,狐狸型的思想家不相信只有一个系统,也没有系统”。简言之,“狐狸”是价值多元论者,“刺猬”则是一元论者。李欧梵以这个譬喻为名,来阐述他在读书时候的一些心得和感悟。 -

再见老房子-祝勇文化笔记
对于一个城市的认识应当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进人城市的空间不是难事,而进入城市的时间则并不容易。因为时间始终在逃逸,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时间的来路和去处,则都隐在黑暗中。而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度量它的长度——是一秒钟,一分钟,还是一小时7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抽象的、时时更换的、不稳定的,而“过去”则是永久的和具体的,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消逝的事物都将在“过去”聚集。 所以,在我看来,所有的城市都是属于过去的——一分钟以前的“过去”,或者一耳年以前的“过去”。时间没有起始点,干是,我们回顾的口光可以无限延长。一座城市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视线延伸得越长,说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想象越是复杂和生动。空间是时间的容器,消失的时间将在城市的空间中留有痕迹。所以,时间和空间可以合二为一。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阅读,应该同时完成对城市时间的阅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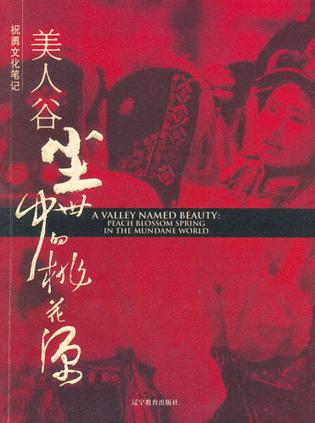
美人谷-尘世中的桃花园-祝勇文化笔记
我觉得自己至今仍然生活在美人谷。我希望自己每晚依然能够在漆黑的木屋里骤饮酥油茶,在早上用冰凉的水洗脸,然后站在“拉吾则”上观看雪山光影的变化。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都包含在美人谷的名字里。是这个名字对我进行最初的煽动,让我前往这个群山环抱、河流交织的云中天堂。此前,我没有关于美人谷的任何知识准备,只是在地图上寻找过它的位置——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古老的康巴地区,大金川、小金川、革什扎河、东谷河和大渡河五条河流交汇之地。河流巳经率先证明了丹巴是一个神异之地。河流是先知,有着充足的阅历与智慧,引导着我们的旅程。我从不怀疑河流的选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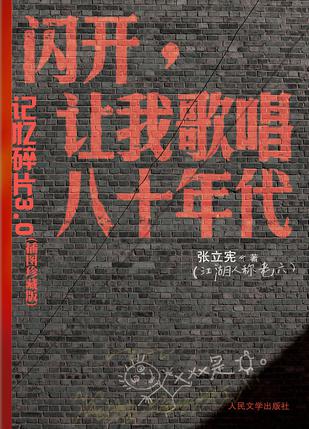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内容简介: 从“饭局通知”到“大脸人生”,从80年代青涩照到“探讨人生”深沉貌 十二幅铅笔线描友情勾勒八十年代回忆 六枚作者新老照片串起二十载北京生活。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2008年4月出版,已逾五载,屡次加印,好评不断。再推出新的“插图纪念版”,一是为了感谢新老读者的厚爱,二是有感于时代的剧变,有感于老六书中所描摹的那个年月,已渐成一曲挽歌。 此时,再次怀念八十年代,其出发点和意义已不只是个人史的回忆,更是为当下的存在寻求信念和暖意。如同老六在新版后记中的发问——在这个纷乱的年代,“我们如何自处?选择怎样的生活?” 这真是一个“大哉问”。时代在剧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经历着非同一般的检验,行走在这个时代中的老六,因为《读库》的结缘,因为个人的选择,共处的是一些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人们——“他们让我看到了在末世狂欢的人群中可以做到沉默,在四周纷纷噤声或跪下的时候可以兀自站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让我看到了抗拒某种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多么悲壮,在这个夸夸其谈的国度里还可以行动。他们在这个怨夫与怨妇充斥的世道里没有申诉个人的冤屈,他们打心眼里爱自己,也爱这个世界,他们的爱是一种切实的行动和勇气,是一种不屑于向你张扬的骄傲和充实。” 插图纪念版除了老六请王增延老师绘制的十二幅插图,还有老六不同时期、不同表情的六张照片。以及一些与“饭局通知“、与新版插图、与人生有关的杂碎文字,以及分量十足的新版后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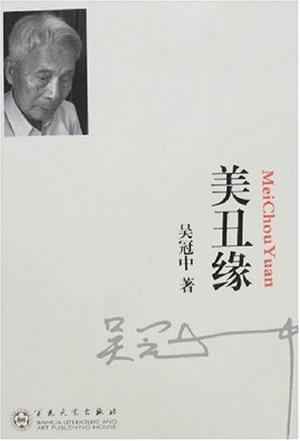
美丑缘
-

译余偶拾
杨宪益先生是中外驰名的大学者。他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译成中文;又将《楚辞》、《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部分《史记》与《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在外国广为流传。本书辑录了杨宪益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 从《零墨新笺》到《译余偶拾》 前面谈过,北碚国立编译馆时期是杨宪益一生中的“高产”期之一。近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王敦叔先生在所著《贻书堂文集》中专辟一章论述杨宪益在《译余偶拾》中的有关中国和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关系史的研究。 朋友要我把过去发表过的文史考证笔记,整理一下,编成一集出版。这些笔记都是旧作。在付印之前,有必要作些说明,交代一下。我开始写这类笔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寄居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辑馆做英译《资治通鉴》工作,同卢冀野、杨荫浏、杨仲子等朋友来往很熟。在他们几位的鼓励下,写过一些文史考证文章,寄给上海的《新中华》杂志发表。在一九四七年把其中的二十几篇编成一个集子,卢冀野兄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零墨新笺》,编入“新中华丛书”,只发行了一版。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又陆续写过一些笔记。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又把这些后写的稿子编成一集,自己出钱印了一本,起名叫《零墨续笺》,分送一些朋友。后来就再没有这种闲情去写这些东西了。有些朋友认为这些考证,虽是我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读书笔记,也许还有些参考价值,要我再编一下,重新付印,因为原来的《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今天已很难找到了。去年有些老朋友要我再写几篇这类笔记,由于他们的蛊情难却,曾写过几篇,连同一些旧稿在报刊上登载过,起了一个新名,叫做“译余偶拾”。 ——杨宪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