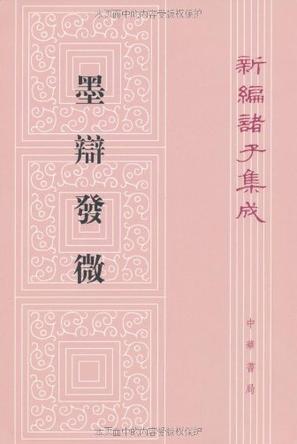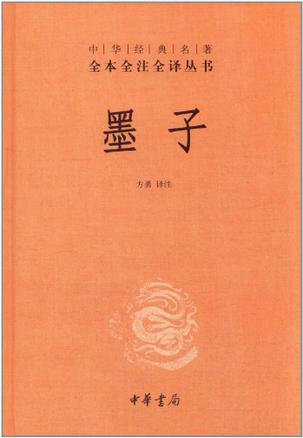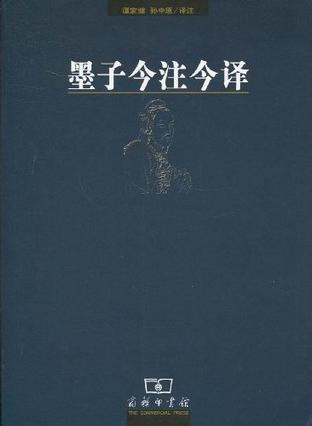墨子城守诸篇研究
史党社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墨学源流、《墨子》书研究的基础上,对《墨子》城守诸篇的结构、作者、成书时代、学术价值,以及与秦汉简牍的关系作了新的探讨。
前言
墨家是东周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学也曾与儒学并称“显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活于春秋战国之际。《墨子》书是墨家学派的著作结集,自墨子时代起,《墨子》的一些篇章就开始成型,西汉后期刘向等人“定著”为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一篇,自第五十二篇《备城门》以下所存的十一篇,内容是讲守城的技术和法令的,一般被称为城守诸篇。秦汉以后墨学衰微,《墨子》书也散失了部分篇章,其间只有晋鲁胜《墨辩注》以及唐乐台为三卷本《墨子》的注释,两书皆已失传。至于明清之际,傅山为《墨子•大取》作注,墨学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出现了许多校注著作,而以清末孙诒让《墨子閒诂》集其大成。清代以来的校注著作,许多都包括有城守诸篇,故对后者的研究,也当自清代算起。
城守诸篇属于《汉志》所说的“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的兵技巧家著作,但《汉志》所列的兵技巧家著作十三家一百九十九篇,至今都已失传。城守诸篇中的兵技巧著作,大概正是由于入了《墨子》,所以才得以流传下来,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岑仲勉先生曾经指出:“《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材料,两者不可偏废的。” 但是,在清代以来墨学的“复活”过程中,由于以下因素的存在,致使城守诸篇的研究一直处于冷寂的状态:一是吴汝纶以来的“伪书说”的存在;二,胡适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就重于哲学,并认为称守诸篇“于哲学没甚么关系”、“不必细读”。梁启超也说,《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是专言守御的兵法,可缓读”,“而且我国学人,向来多偏重玄虚,忽视现实,重文轻武,久成陋习,武备方面,更不值得文人注意”(岑仲勉语);三,城守诸篇为墨家不同弟子各记所闻而成,语言也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文辞古奥,又多军事术语,故意思不容易理解。这个情况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有所改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为《墨子》全书作注的著作,是清代中期毕沅等人所注的《墨子》,毕注于《墨经》、城守诸篇都有很大功劳,其于《墨子》研究具有草创之功。1948年出版的岑仲勉先生《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书,采用了清代毕沅、王念孙以来的校注成果,为了城守诸篇作了全面的注释,使其在至今可以看到的毕沅注释的基础上,基本可以读通。岑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专门为城守诸篇作注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河西、银雀山出土了大量汉简,湖北云梦等地也有秦简发现,这些简牍有许多与城守诸篇相似的内容。另外,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还有大量战国秦汉城址、长城、关隘的的新材料发表,这使对于城守诸篇的重新研究提供了可能。学者们利用这些地下新出的简牍、考古材料,对于东周秦汉时代的城防技术作了很好的研究,如劳榦、陈梦家、陈直、初师宾、李学勤等人,他们对新出材料的利用和研究,都涉及到了城守诸篇,这代表了城守诸篇研究的最新进展。虽然如此,与《墨子》的其他篇章相比较,对于城守诸篇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虽然自清代以来,有许多校注著作问世,在内容校勘、注释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有城守诸篇本身存在有许多讹、脱、衍、倒、借的情况,现在主要的校勘著作——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吴毓江的《墨子校注》、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叶山(Robin Yates)的《被围攻的城——〈墨子〉城守诸篇的重建和翻译》等几种,由于对城守诸篇的成书过程那样的基本问题意见不一,在许多地方,上述诸家还有不同的校勘。我们知道,城守诸篇是墨家弟子各记所闻,最后又由后来汉人编订成书,各篇之内、前后篇章之间,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内容重复的情况,故不应把相似内容轻易连缀。在此方面,日本学者渡边卓的观点是最为精当,他对城守诸篇内部的结构、成书有精审的分析,我们的校勘必须立足于这样的认识之上。其二,城守诸篇乃乃战国人作品,基本遵循着当时的语言习惯,文字古奥;其中又多军事术语,有的攻守设施器备已经失传,对战国军事情况有的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对城守诸篇的内容,至今并不容易完全搞清。从现存的毕沅的注释,到孙诒让、岑仲勉,诸家对于城守诸篇的注释,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起前人,我们可以利用新的考古、简牍资料,弥补某些不足,对城守诸篇难懂的部分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其三,城守诸篇作为存世不多的兵技巧著作,对其内涵的发掘、研究是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个学派的著作,城守诸篇虽然不能完全当作东周军事的实际材料,其中具有理想成分,是墨家对于城防技术的“设计”结果,但城守诸篇仍是研究东周军事的重要材料,是可以适度利用的。对于墨学的源流等等当时的学术状况,也可从中窥见一斑。例如《韩非子•显学》明确记载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当今学者大多以为三派即东方齐鲁宋卫、南方楚、西方秦之三地之墨;城守诸篇的作者,清人苏时学首先把《备城门》等篇与秦相联系,认为乃商鞅辈所为,历经栾调甫、蒙文通、岑仲勉、渡边卓、陈直、李学勤等人的论证,其成书与秦墨关系密切,已无疑问。
当代一些学者,都认识到城守诸篇重要的学术价值,认为其不可忽视,也从不同角度,作了一些相当有益的研究,综观起来,以往的研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缺乏全面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近十余年来,笔者尝试对城守诸篇的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加以探索,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见即将出版的本书的姐妹篇《墨子城守诸篇校注》一书,此书偏重于城守诸篇的校勘和注释。此处呈现给大家的《〈墨子〉城守诸篇研究》,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在对墨学源流和《墨子》书探讨的基础上,对上述第三个方面即城守诸篇的成书、价值作了探讨和发掘。笔者以为,在探讨城守诸篇之时,单纯去谈城守诸篇,而不把其与墨学源流、《墨子》的其他篇章,以及更深刻的东周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是不能察其实质的。同时,新出简牍和考古材料的利用,也应是十分注意的事情。
对于书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深切希望读者能给予批评,以有利于以后更正和学术的进步。
感谢
我是专治秦史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陕西师大上研究生的时候,何清谷先生在课堂上讲过《墨子》城守诸篇与秦的关系,这使我对城守诸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想知道到底与秦是什么关系,可是一直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做这个工作。直到1998年,我下决心要研究这个问题,并从此时开始收集资料。我本不懂文献,对学术史也是一知半解,所以做得很辛苦,许多东西是边做边学的,没想到这个工作竟断断续续做了10余年。其间的2001年,以“《墨子》城守诸篇疏证”为题,被国家文物局立项并资助,使我备感压力和骑虎难下。经过十分痛苦并愉快的磨砺,2006年初稿成,大约50万字,分上编校注和下编考证两个部分,交给国家文物局结项验收获得通过。此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加以修改补充。中华书局的先生们建议我把上下编分开出版,于是就有了《墨子城守诸篇研究》以及姐妹篇《墨子城守诸篇校注》(暂名)二书。
本研究形成如此结果,得益于许多先生的帮助。许多同行一直给我鼓励,使我能坚持把这个课题做完。我曾经去山东滕州墨子研究中心、河南社科院以及鲁山等地访学,实地考察相关遗迹,山东墨子研究中心的李广星;河南社会科学院萧鲁阳;平顶山社联刘耀华;鲁山当地学者郭成智、陈金展、张新河诸先生多给帮助和指教。在资料收集方面,得到了我国大陆田静;台湾地区陈文豪;日本池田知久、鹤间和幸;美国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加拿大叶山(Robin Yates)等先生的帮助。秦俑博物馆秦仙梅女士帮助翻译所有的日文资料。中华书局历史室的李解民、王勖先生给了我许多好的建议,特别是孙文颖女士为出版作了很多工作。对以上人士,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感谢国家文物局和秦俑博物馆对我的研究工作及本书出版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