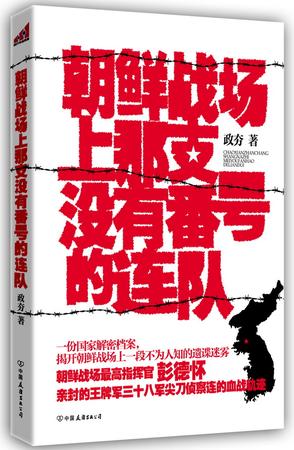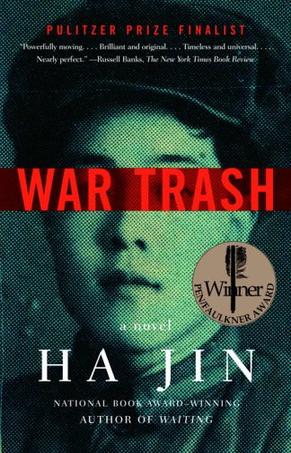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沈志华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
编者前言
200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场震动全球的东亚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或回忆,或评论,或叙史,或争议,从未间断。关於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确如汗牛充栋。人们之所以热衷於研究一场战争,而且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不仅是因为它对1950年代及以後的远东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制约著中国、美国、大韩民国、朝鲜和苏联等一系列国家的对外政策走向;也不仅是因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基础,即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围绕东亚的危机时常困扰著邻近大国的首脑和半岛南北双方的领导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於,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由於种种条件的限制,时至今日,关於朝鲜战争仍然存在著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既有研究者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有尚无法对事实本身做出确切描述的悬案。
研究历史,探索历史事件的谜底,首先应该依靠档案文献。实际上,关於朝鲜战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正是伴随著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而形成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决策的美国军人和政客,如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Ernest A. Gross)、杜鲁门(Harry Truman)的特别顾问哈里曼(Harry Truman)、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John J. Muccio)等。会後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後的观察》一书,[1]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从60年代起,美国国务院分年分卷陆续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70年代中期开始公布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特别是在《1950年,第6卷,远东和太平洋》和《1950年,第7卷,朝鲜》中,[2]载有大量的「绝密」、「机密」和「秘密」文件,使人们对战争期间美国的决策内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英国外交档案也根据保密30年的规定陆续开放。於是,从70年代後期开始,关於朝鲜战争的研究活动便在英语世界开始升温,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仅1981年便出版了4部颇具影响的专著,西方国家随後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朝鲜战争研究热。[3]
然而,严格地讲,对於了解这段历史事实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陆续问世。个中原因就在於,作为战争一方的苏联和中国,其有关战争的历史文献始终隐藏在铁幕背後,直到十几年前,由於中国和俄国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这些秘密才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第二次研究高潮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延续时间长──直到今天尚有新作不断问世;其二是波及范围广──研究者已经大大超出了英语世界。[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期恰逢朝鲜战争爆发40周年和50周年,吸引了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文献不断地披露出来。
1987-199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和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大约300余件);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和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5]此後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周恩来年谱》(1997年)、《周恩来军事文选》(1997年)、《彭德怀年谱》(1998年)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也发表或使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
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chol)、朝鲜内务省副相姜相镐(Kang Sang-ho)、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Lee Sang 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云(Im 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了解内情的前苏联外交和军事官员,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 S. 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格奥尔基.洛博夫(G. A. 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基.波尔特尼科夫(Georgi 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的首席顾问瓦伦丁.索济诺夫(Valentin D. Sozinov)等人。有关这些回忆和采访的文章在俄国、韩国和美国的报刊杂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
这一时期,特别在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性反应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开始大量公诸於世。如果说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完全是经过国家有关机构挑选和编辑後公布出来的,那么俄国档案则几乎都是未经编辑加工的原件。虽然刚开始披露的一批文献是政府有关部门挑选的,但以後更大量的档案则完全是学者们直接从档案馆中发掘出来的。无论在其数量上,还是在使用价值上,都是目前中国相关档案无法比拟的。1994年,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於1949-1953年朝鲜半岛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史达林与金日成、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会谈纪录,中、苏、朝三国领导人之间以及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对外政策档案馆。当时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把其中216件档案(548页)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 Young-sam),[6]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韩文),随後在香港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7]
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专门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数月,又复印了数百页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这批文件的俄文复印件存放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威瑟斯比还将收集到的部分档案(约130余件)译成英文,陆续发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公报》上。[8]此外,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巴加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鲜战争档案,并通过他们的论文或专著披露出来。[9]
目前在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中使用的俄国档案还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根据该馆收藏的文献编写的《朝鲜战争前夕及初期(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主要事件年表》,[10]该文件是由档案文献摘录、缩写或编辑而成,对於战争期间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价值不言自明;其二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影印的一本俄国档案专集,内容全部是关於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报告、函电及相关文件(100多件),对於了解战争期间的中朝方面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针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国档案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和整理了近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於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於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锺,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校对和编辑,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的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余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後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於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收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大大超过了目前散见於国外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档案文件。[11]所以,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
2002年夏天,笔者应台湾陆委会及中央研究院邀请,在台北进行了两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长陈永发先生谈起此事,不想一拍即合。近代史研究所决定正式出版这套文件集,而且就在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
为了便於读者利用档案文献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一、收入本文献集的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经过整理,将这些档案中554件定为主文件,其余100多件作为附件从属於主文件。除极个别文件因无法找到俄文原件而译自英译本外,几乎全部都译自俄国原始档案。附录中列有关於上述档案馆的简要介绍。
二、就其形式而言,这些档案大多是苏联、中国、朝鲜三方领导人及相应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文、会谈纪录,苏共和苏联政府从中央到各主管部门的会议纪录、决议草案、请示报告及情况通报,苏联驻中国和朝鲜使馆与国内相关部门往来的电报、信函等等。除对档案本身进行翻译外,对於收件人在文件上所做的手写批语,凡能辨认清楚的,均在注释中做了介绍和说明。
三、档案整理的原则是:首先尽量确定文件的作者、发件人、收件人以及文件形成或收发的时间,然後根据文件的内容及上述要件明确相关文件之间的关系,最後按照文件形成或发出的时间排列档案顺序。为便於读者理解文件的内容,对主要人物、事件和专门用语进行了注释,编写了〈人物简介〉和〈朝鲜战争大事年表〉,并对整理和翻译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了必要的技术性说明。
四、本档案文献集有两组编号,一是冠於档案名前的顺序编号,以标明各文件之间的时间关系;一是文件右上角的编号(SD*****),是按照原始档案复印件收集的时间前後排列的,与文件内容无关。文件的标题为笔者所加,有些档案原件未标明时间或作者,只能根据其内容或字迹做出判断。有少数文件原作者在起草时加有注释或说明,在文献集中,依原文的表示方式,以随文方括号加以标示或在注释中标明。
五、关於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凡能够查找到的,均以原文附在文件最後;有些文件的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在收集文件时便缺失,限於条件,目前尚无法一一标出。为便於研究者核对原文,笔者已将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原件复制,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五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意者可按照档案编号(SD*****)进行核查。
六、关於地名的翻译。朝鲜的地名翻译最令人头痛,原因是50年代的许多地名,是按日文发音而以朝文表现的,现在又要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实在不易。加上许多地名现已改变,而当时又没有规范俄文拼写标准等原因,尽管笔者曾找来俄文、日文、韩文、英文和中文五种朝鲜半岛的地图,进行核对,并曾多次向韩国学者请教,仍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因此,有些实在无法确定的地名,只得采取音译的办法,并在译文後附上俄文原文。
七、关於人名的翻译。其中比较麻烦的也是朝鲜人名,主要问题是档案作者书写的朝鲜人名,都是根据发音自行拼写的,结果同一个人名在俄文中往往有几个不同的拼法。此外,许多外国人名的中文表达,大陆与台湾差异很大。为解决这个问题,在附录中编排了〈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对照表上标明人名的俄文原文、中文译名,以及英文或罗马化拼写译名(凡无俄文者,为编者所写前言、代序中出现的人名),以姓氏之中文笔画与罗马化分别排序。书中所有外国人名首次出现时,原则上均加入罗马化姓名,如有遗漏,请参照对照表。
八、因参加翻译和编辑的均为中国大陆的学者或工作人员,故名词和用语均采用的是大陆通行的用法,与台湾略有不同,如韩战称朝鲜战争,南韩称南朝鲜等。为顾及台湾以外的华语使用者,经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商议,除一些最常用的地名和人名改为台湾译法(如将「福摩萨」改为「福尔摩沙」,将「斯大林」改为「史达林」等),其余均保留原译文的用语。
此外,藉本书出版之际,笔者必须向那些曾经热心帮助寻找或慷慨提供俄国档案文献的国外同行表示感谢,他们是: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冈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Андрей Соколов)、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前後两任主持人沃尔夫(David Wolfe)和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所长河载平、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现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王晓东、美籍华人学者、佛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Chen Jian)等。此外,韩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金东吉先生帮助笔者对文件中朝鲜人名的中译名和英译名一一进行了校改,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本书得以及早问世,还要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同仁谢国兴、魏秀梅、余敏玲、张淑雅、张珍琳、张秋雯、汪正晟、江玮平、林志菁等。在笔者离开台湾以後,如果没有他们在後期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付出的努力,这部近90万字的著作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付梓,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献集刊出的全部档案文件由沈志华收集、整理、注释,参加翻译的有刘仲亨、徐晓村、王英杰、孙熙、周绍珩、锺舞春、王谊民、章若男、王会朋、刘志青、李木兰、陈云卿、吴安迪、戴怀亮、彭兴中、唐松波、耿保珍、方琼等人,参加校对和编辑的有沈志华、王启星、方琼,最後由沈志华统一定稿。所以,本书当中的一切舛误和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编者与出版者的共同愿望是,希望这部以专集形式出版的关於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有助於推进华语世界对於朝鲜战争、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亚洲冷战历史的研究。
沈志华
2003年2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