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
在福柯打开的新视野中,德勒兹是将疆域拓展得最宽的一位,文学、电影、绘画,不一而足。而这本论培根的作品,是德勒兹将哲学触角引向绘画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可以管窥德勒兹的基本哲学观念,尤其是德勒兹的思想方法。 德勒兹认为-弗兰西斯·培根的绘画以纯粹的形象取代了具象绘画,从而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拯救了形象在20世纪的命运,在他之前,塞尚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探索,而从更广的艺术史角度来讲,这一探索可以上溯到古埃及艺术。这一探索的本质,是用一种具有触摸能力的视觉,取代了纯粹的视觉,其间有哥特艺术与巴洛克艺术曾经偶尔达到了这样的视觉。 -

什么是哲学
德勒兹一生中与迦塔利合写过多部作品,《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和《什么是哲学》是其中的两部。 在《卡夫卡》中,作者强调卡夫卡喜欢用一种称为“弱势”的文学术语,从语言、政治和群体上定义自己,同时又指出,弱势文学是大文学中彻底革命的元素。 在《什么是哲学?》中,作者指出:哲学作为创造概念的活动,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是概念的创造性本质,什么是随之相生的纯粹的内在性、内在平面和概念性的人物。正是通过这一点,哲学区别于科学和逻辑。 目 录 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 第一章 内容和表达 低垂的头和抬起的头——照片和音响 第二章 夸大的俄狄浦斯情结 双重超越:社会三角,动物之变 第三章 什么是弱势文学 语言行为——政治因素——群体因素 第四章 表达的构成成分 情书和邪恶盟约——短篇小说和动物之变——小说和机能性布局 第五章 内在性和欲望 反法律、负罪感和其他——过程、比邻,延续和无限度 第六章 层出不穷的系列 权力问题——欲望、片断和路线 第七章 联接手段 女人和艺术家——艺术的反美学倾向 第八章 单元,系列,强度 卡夫卡所说的两种营养造状态——单元的各种形式与小说的构造——矫揉造作 第九章 什么是配置? 话语和欲望,表达和内容 法汉译名对照表 什么是哲学 导论 问题因而就是 Ⅰ哲学 1.什么是概念? 2.内在性平面 3.概念性人物 4.地理哲学 Ⅱ哲学、科学逻辑和艺术 5.函项与概念 6.前景与概念 7.感知物、情态和概念 结论 从混沌到大脑 法汉译名对照表 译者谨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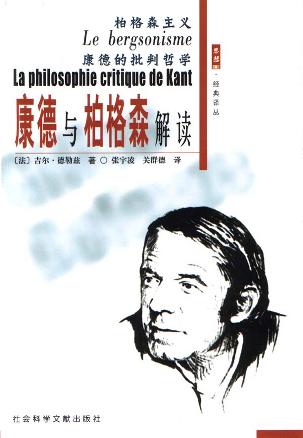
康德与柏格森解读
树的图像可以展示出主导人们认知的模式:井然有序的等级秩序,树枝的多样性从树干的统一性中生长出来,而根部的盘根交错也归于主干。树的譬喻可以归结到统一性、等级体系、线性秩序以及系统的胜利。从赫西俄德撰写的神谱、生物学的物种起源学说、到现代语言学的句型树状图分析--树的譬喻到处都指向形而上的秩序。但是哲学家德勒兹说:"我们已经厌烦树木,再也不能信任树木了……我们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整个树状文化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只有地下的须根、蔓生植物、野生植物和根茎才是美丽的、政治的、可爱的。" 在这里展现出了与树相对立的模式。哲学家德勒兹,这位如此独特且又富有创造力的并且崇尚尼采的人,会以怎样的形式来论述康德与柏格森呢?令人充满期待。 -

萨特的世纪
(序)那天在蒙巴纳斯,人们怀着隐隐的不安,小声地交谈着,久久不肯散去。四月的天空,连光线也像怕冷似地瑟瑟抖动着。无车的巴黎透出一股静谧。人群依依不舍地散去,街区里到处充斥着难以言表的骚动。时时可以见到一些人,脸上带着激动的表情,显得怪怪的。拉斯帕依大道和狄多街上的咖啡馆里,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也有或男或女单独在街上无所事事地走着,也许只是想拖延时间。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也和他们一样,是来参加萨特的葬礼的。开始时气氛像是过节,最后却像一场半途而废的示威游行,只剩下人行道上零零散散的人群。 我还记得,我是沿艾德加·基奈大道,一直走到萨特曾经住过的那幢小房子的;那房子也披上了哀纱。房前聚着一群人,是巴基斯坦人,好像为什么事在那里争论很久了。有个我多少认识一点的苏联异端分子。有外省来的人,载他们来的大轿车就在旁边等着。有个年轻的妇女单独待在一边,大概哭了很久。就像动乱时期一样,工会的人和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秩序,在房子周围临时站了岗,让迟迟不肯离去的路人离开,房前这段碎石路面已经成了圣地。我盯着房子的前面儿看了一会儿,目光顺着墙面数到第九层,那里曾是我去过几次的地方。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小小的套间,那张工作台,有一把脏兮兮的灰色的扶手椅,那是他最后一个秘书坐过的,有一个空着一半的书架。 这就是名声显赫的萨特生活过的地方吗?萨特的话曾经响彻全世界,今天下午又像顽强的蜜蜂一样,嗡嗡地飞回墓地,那些话语难道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吗?还会有别的萨特吗?——或者说,像他这样的人是独一无二的,他不属于哪一种哪一类,他一死,他所代表的种类也就消失了。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我觉得我并不喜欢这个人,也不敢肯定地说我不喜欢他。那为什么也和别人一样,觉得有必要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呢?而且,那葬礼的仪式……那数以千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也许数以万计,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站满了墓地的条条小径。活着的人与墓地的幽灵,反叛者和小资产者,不分彼此,发出一片压抑的嘈杂。有左派的人士,有孩子,还有上流社会人士组成的代表团,每个人都用邮差的黑红色旗子包着头。《法兰西新杂志》(NRF)和“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友好协会”献了花。猎奇的摄影记者在窥伺。有的女人泪流满面。有一群年轻人,大概根本就没有读过萨特的书,却也在那里,攀缘在树上。有非洲人,有亚洲人,有“光明岛”派的越南人,也有“胡志明”派的人,两派人本来是根本不想见面的,但是,与他们的争执毫无关系的人群将他们拥在了一起。有声名显赫的人,有默默无闻的人。有的夫妻被人群挤散了,开始还远远地互相招呼,后来就再也找不到对方了。有的人原来是死对头,有谢了顶的,有目光哀切的——看那动情的样子,哪像昨天还在互相嘲讽、互相挖苦的人呢?当然也有与萨特亲近的人们,有他的弟子们,淹没在人群的嘈杂之中,为人群所左右,所裹挟,有时甚至被挤到了送葬队列的外面;有人在悄悄地议论他们,说他们见证了真正的信仰,言语之间流露出恭敬之情。更远处,一个美丽而哀切的女人浑身穿着丧服坐在墓穴前的一把折椅上,她头上的围巾散乱了,尽管有几个忠实的弟子想推开人们,在她四周围出一块空地,却怎么也挡不住涌过来的人群,人们挤得她无处立足。究竟是谁制造了如此奇迹呢?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神秘的魅力,在一生中激起过多少人的激情?他的声音孤独、干脆而铿锵有力,用那么多的语言,让那么多不同命运的人听到了他的话?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架能融化人的感情和才智的机器?因为他是当代人的庇护所。因为他是指南针。当他离去时,人们借着向他告别,也是在向一个时代告别吧。 我那时三十岁。 我后来又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热情、幻想和失望。 我知道,或者至少我希望,我还有足够的时间与同时代人将这段因他的死而暂时中止了的奇特的历史进行到底。 我还知道——我是在那一刻才知道了这一点的——为了将这段历史进行到底,早晚有一天,我会再次面对许许多多问题之后的人和作品。我知道我早晚会努力去衡量这场用萨特的名字命名的复杂、怪诞、暧昧的冒险。 这本书在我心中孕育了很久,我却下不了动笔的决心。我思之再三,魂牵梦绕,放弃了又拿起来。我写了,但又等于没有写,忘记了,但又没有放弃。它始终就在我眼前飘着,这是个不成形的、不确定的计划,我早晚会把它从虚无飘渺中拉出来,可眼下,它仍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而且,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我们这个漫长的世纪末所发生的件件波折,没有让我加快将这本书写出来,而是让我觉得有理由拖延下去,没有催促我开始动笔,而是让我觉得有理由放弃写作的计划。 革命的思想对萨特的生活和作品产生过多么大的激励啊,可是这种思想像一盏小油灯一样地熄灭了。 萨特曾经迷恋共产主义,至少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有过这样的愿望;但是共产主义却不战而败,不辩而输。 萨特说过,一篇文章,只有与产生这文章的形势联系在一起看,才会有价值。产生萨特的形势已不复存在。好像整个背景原地转了个圈,复又落入了虚无。随着他的逝世,他的作品大段大段地消失,或归于沉寂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对萨特感兴趣,甚至于想写一本书,通过研究他来分析这个世纪的意义,似乎是最不识时务的拙劣之举。想研究马尔罗?当然可以。研究加缪?如果非要坚持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萨特……不行,萨特不行……说什么也不能以萨特为题搞研究……我想像着,如果对七十年代的导师们说,我打算有一天写一本关于萨特的书,他们会感到多么愕然。我的导师们也不在了,也去世了。但萨特仍然是禁区。在当时的文学中,在作家的作品里;最没人理睬的,最没有人要的,毫无疑问,首先就是萨特…… 于是我便读书。把已经读过的书拿出来重新读。我还记得在巴黎重新读到《厌恶》的那一天。我还记得有个朋友在伦敦对我说,《自由之路》其实是很不错的。我认为他说得对。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存在与虚无》时,我是多么赞叹;之后又紧接着读了《辨证理性批判》,我还记得我所感到的震惊。我发现,这是对哲学原有学说的彻底背弃,比费尔南多·佩索阿以多个化名所发表的作品对时代的背弃更甚,与罗曼·加里的双重作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非常喜欢这种局面。 我想悄悄地酝酿我的萨特,而且非常喜欢这种想法,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 人们说,他有些像加缪……因为他捍卫人权,所以他和加缪一样……而且当然也像马尔罗,因为他怀念英雄主义、冒险和“伟大的生活”,所谓“伟大的生活”是指让人与作品合二而一,让人成为作品的延续……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虽然我知道,新的时代将会非常缺乏真正“伟大的生活”,缺乏纯粹的作家,缺乏知识分子的象征,而萨特首先就是这一切的具体体现。 直到有一天,在繁纷的世事中,有两件事加快了事情的进程。 一件是1989年,我在柏林见到一个共产党的老作家。我是在柏林墙拆除后的第二天在他家里见到他的。他是乌布利希和昂纳克的朋友,斯大林主义的吹鼓手。由于制度所造成的所有罪恶他都赞成,而且仍在以他摇摇欲坠的权威来掩盖这些罪恶。他说,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公正地对待我们。我们虽然变成了红色教会之长,但我们是历史上的反法西斯主者。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们才是最好的民主主义者。说着,仿佛是为了给他的话找依据,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懂事的年龄》,上面有作者本人的签字——“知道如何让自由符合自己的愿望的人,斯特凡·赫尔梅林惠存,让-保罗·萨特”(我记得当时看到的,是这样的题词)。 三年之后,在萨拉热窝,当时是波黑战争的第一年,一些波斯尼亚的大学教师们决定留在被围困的首都,而且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冒着被塞族狙击手打死的危险,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离战线不远处的一个地窖里,在十分虔敬的气氛中一页一页地阅读和讨论《方法问题》:这些萨特的信徒们,躲在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为了逃避死亡而读萨特的作品;他们不仅从萨特的作品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也汲取抵抗和斗争的力量…… 为什么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和真正的抵抗战士,都能够从一个人的作品中得到依靠呢? 作者死了十年,十五年了,为什么他的作品不仅还能让各种各样的人怀念他,也能让各种各样世界观根本不同的人都聚集在他的旗下呢? 难道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最好的和最糟的事情,都是由于他吗?难道人们在同一部作品中,既可以得到崇高的箴言,又可以汲取奴役他人的原则吗?所谓“崇高的箴言”,是指让那些被剥夺了一切而走投无路的男男女女奋起反抗的话语。 突然之间,我是否爱过萨特,或者是否恨他,或者既爱又恨,或者既恨又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惟一重要的,是他为时代唤起的,是他为时代注入的那些交织在一起的感情。 惟一重要的,是与后萨特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萨特的作品在人们心中激起的那种不稳定的情绪。 通常人死了,人们因他而产生的情绪就会平静下来,人们的感情就会变得稳定。当然,作者死了,人们对文本的理解不会变得僵滞,文本不会局限于作者的死所赋予的某种意义;但至少作者的死有助于解决某些文字游戏所导致的争执,有助于裁决主要的争吵。对萨特,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他死后尸骨未寒,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 事情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转变的。 在那些年月里,我觉得这部浩如烟海、像恶性肿瘤一样畸形的、有生命的作品中,有其内部自身的冲突,也有作品与时代的冲突;很难分清其中哪些东西仍将伴随未来的暴行,哪些东西则相反,能让人们抵制暴行。这本书的轮廓正是在这些年月里变得清晰起来的。 这就是不稳定的情感所具有的功效。 由爱和恨、佩服和怀疑混合在一起的,让人很难说清楚的情感,也有其好处,那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萨特就好比是一个展开的时代。透过萨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万花筒:人们如何走过二十世纪,如何在这个世纪迷失方向,如何消除这个世纪可悲的趋势——现在又如何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人走进暧昧,总会使暧昧更加深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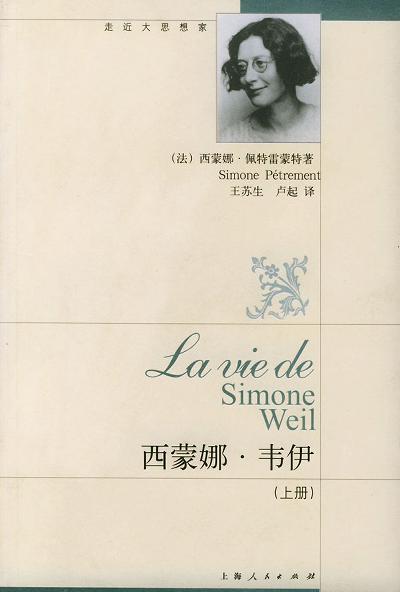
西蒙娜·韦伊(上下册)
本书详细论述了法国现代著名女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西蒙娜·韦伊的不平凡的一生,深入分析了西蒙娜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向宗教救世思想的转变,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痛苦、迷茫、奋斗和思考。书中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西蒙娜特立独行,自甘苦行、永远站在穷苦人民一边的“圣女”人格和感人生平,她独特的人生之路和充满智慧的思想可令每一位读者深受感动和启发。 -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影响极大、流传极广、风行一时的哲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国哲学家萨特,他的思想渗透于各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中。 本书由两篇文章构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前者发表于1946年,萨特此文的“目的是针对几种对存在主义的责难而为它进行辩护”。同时指出它与其他哲学流派的异同,澄清了各种无意的误解和恶意的歪曲。后篇发表于1980年萨特去世前不认,在其中,萨特一再强调,他的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哲学。 注:【ISBN】7-5327-0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