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索真文明
学术与政治似乎是一对孪生子,政治的没落必然带来学术的没落,这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独具只眼的黑格尔却说:常识虽然令人尊敬,对于历史研究却未必适用。著名学者朱维铮教授通过他对近代中国的深入研究,同样为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腐朽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使学术走向没落。晚清的学术,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取自异域。 -

维新旧梦录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可是中国历史是怎样走到维新之路的,本书中探讨的是清帝国的“自改革”从梦想到幻灭的百年历程。所谓“自改革”是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四分之一世纪提出的概念,意即清帝国只有实行由上而下的自我改革才能继续生存。“自改革”幻灭了,百日维新失败了,从戊戌至今,历史又走过了一百年,当年的种种难题,吏治腐败、机构臃肿、特权猖獗、法治不立、教育陈旧、八股误国,尤其是君权不受制约、决策黑箱运作,言论毫无自由等等仍然困扰着今天的改革者。读戊戌和戊戌前的历史,想想今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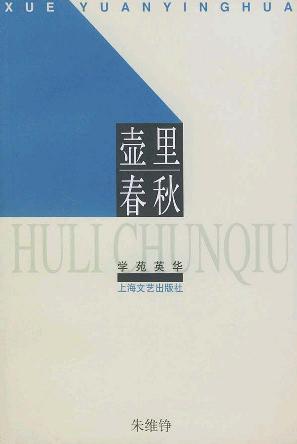
壶里春秋
朱维铮,著名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家。朱先生一贯反对空谈的学问,主张用实证的研究抵制意识形态领域空疏独断的学风。本书即是采选先生学术论著的精义合集而成,集中反映了作者治学的方向和治学的成就,是了解中国文化史的不可多得的好书。(“学苑英华”系列最新推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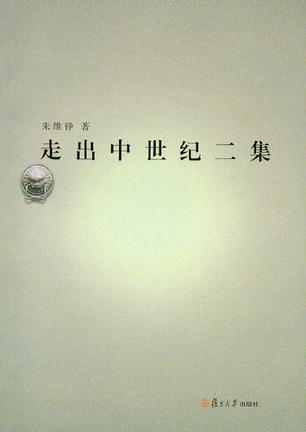
走出中世纪二集
作为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朱维铮教授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多元的探索视野和妙语连珠的流畅文字,在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连贯的发掘探讨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对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作出了独到地阐述,从而充分显示其不仅把握中国历史昨天、前天的学术修养,更体现其关怀人类社会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 目录 序 走出中世纪 ——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续) “君子梦”:晚清的“白改革”思潮 清末的现代化思潮 ——夜读小札 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 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 一、寂寞“待访”二百年 二、清末鼓动反君主专制的经典 三、推崇《明夷待访录》的角度 四、章太炎由“非孙”而“非黄” 梁启超和清学史 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 梁启超与“五四事件” “迷梦的政治活动” 映现危机意识的“心影” 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 并非治清学史的第一人 章太炎和梁启超,兼及刘师培 非天才的天才论述 自己给自己作盖棺之论 胡适《自传》的一则附注 难讲的“原儒”公案 关于钱穆研究 钱穆的文化关怀 民国学术史的过渡人物 新儒家呢,还是史学家? 略说钱著《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与章太炎、梁启超 附记:也说“国学大师”之类 令人将信将疑的回忆录 ——评《银元时代生活史》记章太炎 似已忘却的回忆录 《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上告杨荣国 杨树达私记陈寅恪 叙史的小小尾声 索解晚清的民间报人 ——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小引 杨度的《杨氏史例》 百年来的韩愈 《伯夷颂》颂错了? 曾国藩与韩愈行情 严复《辟韩》及其反弹 韩愈在“五四”前后 韩愈和民国“训政” 陈寅恪《论韩愈》前后 俞平伯与陈寅恪 陈寅恪在劫难逃 韩愈成了“尊儒反法”的反面教员 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 顺便说到《拘幽操》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引言 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 耶稣会士向往中国 基督教在华梅开三度 十八世纪的相反记录 马礼逊与太平天国运动 从“教难”到“教案” “传教宽容条款”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 在华的自由派传教士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 剪影与参照 晚清上海租界的宗教文化 历史展现的特定文化形态 光怪陆离的宗教现象 新旧基督教 两个租界的“自治” 新教各差会的“学术传教” 仍待深究的课题 过去的“风流世纪” ——关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 龚橙与火烧圆明园 ——以讹传讹的一则史例 附录: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现场报道 现代大学的中国先驱 ——《马相伯传略》弁言 《壶里春秋》小引 “五四”: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我看经学与经学史 ——《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 关于清代汉学 一、三类“汉学” 二、名目的确立 三、名实问题 四、形态问题 五、文化比较 晚清学术的非传统化进程 读《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家谱和年谱 “国学”岂是“君学”? 从儒学史说到新儒学 关于马一浮的“国学” ——答《大师》编导王韧先生 一、介绍马一浮的“价值” 二、关于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 三、马一浮与中西文化 四、马一浮为何强调“直接孔孟” 五、马一浮与复性学院 我的书架没有秘密 ——答《南方周末》编者刘小磊先生 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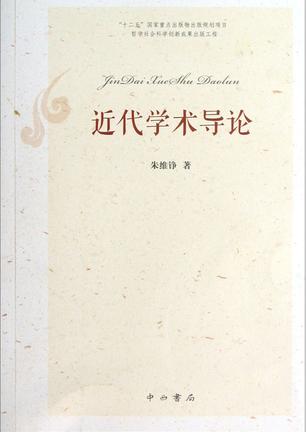
近代学术导论
《近代学术导论》是朱维铮先生生前最后一本授权出版的个人著作,也是作者治中国学术文化史多年来的总结。《近代学术导论》既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多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涉及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某些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勾勒出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发展脉络,深刻剖析近代学术嬗变背后的种种动力。作者视野宏阔,分析细腻,不仅能于他人习见之处发前人所未发,且在突破旧说的同时,以其犀利的分析引导读者对近代学术思想的变化进行反思,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关怀和责任感。 -

怀真集
序 言 每当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离开,作为校长的心情是最纠结的。 朱维铮先生逝世转眼已经一年了。朱先生的离世,对复旦、乃至对整个学界都是巨大的损失。先生于复旦大学大力振兴人文学科的关键时期离世,我切实感受到了没有朱先生的复旦多了一丝寂寞和忧愁,复旦的发展太需要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的建言、献策、指导和批判。 我对朱先生的学问,既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来作任何评述,历史系的同志们要我为朱先生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集写几句话,我只能谈一点我的感受。尽管我和朱先生的学科相距太远,但我和《人民日报》记者姜泓冰女士有着同样的感受:对于一位大师,我们外行“不必读懂他的专业贡献,更不必纠结于他的一言一行;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遗产’。”这种“气场”和“遗产”就是一种久违了的“士人风骨”。我认为,“风骨”至少是知识分子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概括,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首先体现在讲真话的巨大勇气。我和朱先生原先并不熟悉,论年龄他是我的老师辈,加之我是自然科学家,朱先生的学问对我来说太过深奥。因此,我只能以景仰的心情来阅读他的《走出中世纪》,从而来间接地了解朱先生。9年初,我从国务院学位办回来任复旦大学校长,为向朱先生请教复旦人文学科的发展理念而冒昧登门造访,领略大师风采。后来又在医院聊过数次,内容不外乎关于人文学科的治学之道和复旦的人文学科传统,以及关于中国近代科学史等等。每次谈话都获益匪浅,但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率真、求真、认真,乃至有些顶真的态度。他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对如我这样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静心想来,我们所有学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于讨论对象的“真”吗?然而,对于经历过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许提及,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都会深深体会到作为人文学者要做到这一点的特殊困难。还在“文革”的遗风仍相当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声疾呼:“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能够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责学界的“红卫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难找到同类。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学者也不再多数。 朱先生说的都是真话,“真话”无非就是把握和传达了实际情况的本质,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对象(或事件)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恰恰因为这个简简单单的“真”字的潜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说出真话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实,真话的逻辑非常简单,许多都是常识性的;在连常识都被广泛忽视的情况下,说些常识性的真话都会被看作是“另类”。难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的断言会成为名言。因此,编者将纪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为《怀真集》是十分贴切的。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还体现在“为学术而学术”、毫无功利性的治学态度。我感到他唯恐我本能地以工程技术学科的观点来功利地看待人文学科,对我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它也不为任何功利的目的服务”,“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我首次与朱先生面谈时他也表达了要“重拾纯学术大旗”的宏愿。他对我说:“纯学术很重要,它可以弘扬传统,启迪思想。当你讲历史用于功利目的时,那么它和技术一样是把双刃剑。”所以,在0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我发出了“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的感慨。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更表现在他对学术的诚笃,从不为服务于某种目的而“扯淡”。说真话固然很难,不说假话也还过得去,最为可恶的是“扯淡”。按照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哈里·G·法兰克福的阐述,“扯淡”的危害性远大于“撒谎”,因为“撒谎者”的内心还承认一个“真”的存在,而“扯淡者”从根本上漠视“真”的存在;“扯淡”是一种欺骗性的表述,但未到“撒谎”的程度,因而能规避因“撒谎”可能招致的道德上的谴责。在我看来,“扯淡”完全属于毫无道德的“工具理性”范畴;“扯淡”需要高超的技巧,因而“扯淡”在学界常常出现。以我的体会,学界的“扯淡”,表现不外乎“造神”和“造魔”。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造神”或“造魔”,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体现,都是“学界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造神”和“造魔”的目的几乎是完全是一致的,无非就是将“神性”赋予给被捧的一方,将“魔性”赋予被贬的一方,以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来似乎“合情合理”地达到某种目的。朱先生深知其危害性,不仅自己从不“造神”和“造魔”,还不时地呼吁“不要用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神”,“造神运动可以休矣”,……。 在我看来,现如今“神话”不断破灭,信者大不如前。因此,当今更要警惕的是“造魔”。因为“造魔”的手法就是在被评论对象的头上先摁上一顶可怕的“帽子”,随后就可以在“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下对被评论对象肆无忌惮地进行批判、贬斥、威胁,从名誉上搞臭,乃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依我在和朱先生的闲聊中积累的认识,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如若今天他还在世,他一定也会呼吁“也不要用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魔”,“造魔运动也可以休矣”! 虽然大师已然远去,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士人风骨”,就是复旦学术求“真”精神和复旦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我期待朱维铮先生所代表的“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永远在复旦高高飘扬! 杨玉良 3年2月21日 作者简介 杨玉良,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