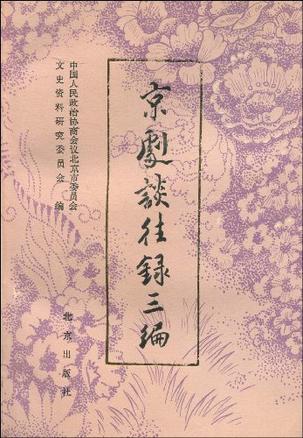我的三位老师:侯喜瑞 裘盛戎 侯宝林
赵致远
读了赵致远先生写的《我的三位老师侯喜瑞、裘盛戎、侯宝林》竟浮想联翩难以成寐。他以极普通的语言说了很深刻的事。我今年已70出头了,人上了岁数,往往会有很多的回忆,这本书更助长了我的回忆,为此要谢谢赵致远先生、蒋元荣先生和吴迎先生。
写序,不敢当,我是演员,写东西不是我的专业。回忆什么就写点什么,读者多包涵。1946年,抗战已胜利了,我父亲梅兰芳苦熬了8年,人心情好多了。当时,我在上海思南路87号我们家就近的法国人天主教百德路教堂 (今重庆南路南北高架)办的盘石小学一边读书,一边学戏。我是童子军的小队长,负责学校每天的升旗仪式。那时学校经济很困难,父亲知道了,就断然提议让我和葆王月姐义演为学校募捐,以解燃眉之急。当时,我才12岁,七姐16岁,父亲已将他人生之实践传递给我们了。剧码定为《二进宫》,这是王幼卿老师所授的。徐延昭请谁呢?父母亲几乎同时说:“请盛戎好!”就这样定了,裘盛戎先生当年相对固定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那天,裘先生来我家,大概30岁左右,很精神。父亲很客气地对裘先生说:“小七、小九还小,您在台上兜着点儿。”裘先生很风趣地说:“二老放心,我一定把二位小老板‘傍’严了。”可惜当年没有资料留下来。到我青年时期,与王泉奎先生、王琴生先生多次合作演出过《二进宫》。当前,李胜素、张晶的《二进宫》就是按我小时候学的路子演的。到1947年上海中国大戏院杜宅堂会,孟小冬的封山之作《搜孤救孤》,也是请了裘先生来傍她。建国以后,裘先生的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十净九裘”,人人皆知,这是他的造化。我们不在一个团,见面机会也不多。可每见到一次,他总是对我倍加关心,这是他敬重我父亲的缘故,我很看重这份情。
侯宝林先生是国宝,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了。接触最多的时期是“文革”后期,到打倒“四人帮”,几乎天天来陪我母亲说话,常客还有马连良夫人、名坤伶杜丽云等人。我们家的人都非常喜欢听他说话,在“语言文学”领域里,如果蔡元培先生在,一定会请他担任北大教授的。他对戏的各种行当、角色、流派信息的储存量,可以和当今Windows媲美。更值得回忆的是在1961年困难时期,他也常来我家聊天。当时,没什么吃的,听他说话,是一种精神食粮,使人学到东西,又使人轻松。最值得纪念的,也是在食物供应紧张的年代里,苦中取乐。在家中,我们合唱了一段《坐宫》,至今录音还在,侯先生的幽默是超然的,使人乐中进取。
侯喜瑞先生是令人敬重的老前辈了。前清光绪末年,我父亲在喜连成搭班,他是喜连成科班第一科的徒弟,宗黄(润甫)派。父亲说:“我和黄润甫先生合作过,他学黄派,已经从形似而达到神似的地步。”1922年梅兰芳剧团的前身承华社成立,他是重要成员,和我父亲合作多年。他离开承华社后,每当我父亲演《穆柯寨》,必定特请侯喜瑞先生演焦赞、裘桂仙先生(裘盛戎之父)演孟良。父亲说:“我也觉得与他们合演使这出戏出色不少。”1 927年父亲第一次在中和园演《凤还巢》就特请侯喜瑞先生演周公公;演《西施》时,特请侯先生演吴王夫差,例子举不胜举。建国以后,父亲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曾组织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专家出版述说他一生表演艺术经验的专辑,使仰慕侯派艺术的演员和业余爱好者,对侯先生能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从中得到启发,提高自身的表演能力。用现代艺术的语言来说,侯喜瑞先生的表演中“肢体语言”的功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很值得我们思考。
我希望我们票界的戏迷们,热爱京剧的“粉丝”(fans)们,看一看这本很值得一读的书,体味一下其中的甜、酸、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