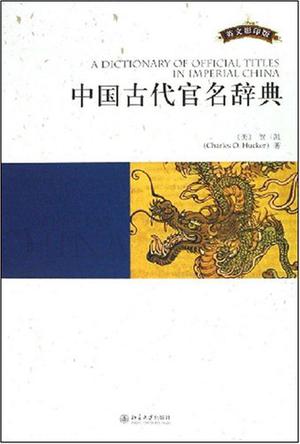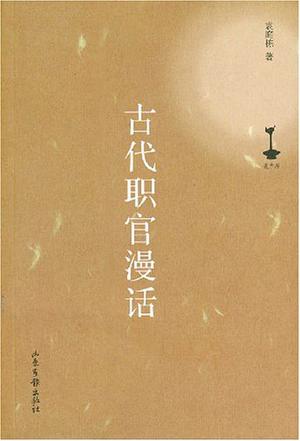中国古代官名辞典
贺凯(Charles O. Hucker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