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散文
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李国文的散文有学问,具真性情,也有一种洞明世事的敏锐的观察力,尤难能可贵的是拥有一颗超然的自由的心,唯其如此,方能获得从容和自信。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不知为什么,有的人,很在乎别人的感觉,尤其我们中国人,具体地说,譬如作家,更在乎外国人的感觉,好像必须外国人告诉他感觉以后,他才有感觉。这真是很可怜,怎么能如此不相信自己笔下写出的东西?‘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干吗这样缺乏自信心呢?”说得多好!对于迷信外国月亮的人不啻当头一棒。 喜欢李国文的散文,是因为他的文字不仅自在,而且老辣,见修养,也见性情,貌似随意,其实是一种气定神闲后而有的潇洒。他自己也说,安闲、怡乐、平易、冲淡是写作散文的一种适宜心态,“太强烈,太沉重,太严肃,太紧张,散文的‘散’的韵味,随笔的‘随’的特性,也就失去了。……‘散’是一种神态,笔下出来的却是冲淡、飘洒、不羁、隽永的文字,它和松松垮垮、不着边际、信马由缰、跑肚拉稀的笔墨,不是一回事。”可见,李国文对散文是有自觉的认识的,尤其是他的“‘散’是一种神态”的表述,令人回味不已。 李国文那些恣肆放言、散淡自在的文字,都是他的“尽意”之作,许多的篇章,气势一直环绕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意之所到,笔力曲折”,也许,正式因为“笔力曲折”的缘故,他那些颇见风骨的“意”和“气”,照样显得冲淡而舒适,读者接受起来,完全没有金刚怒目、剑拔弩张式的强迫感。即便在文章最气盛的时候,李国文也没有失去“‘散’是一种神态”的写作定力,他是确实知道,自己是在写“散文”的了。 他进入的不仅是散文的写作,更是散文的状态。这样的作家委实不多。这一话语实践的成功,再次告诉我们:散,永远是散文的基本神态(尽管它也依托于散文的内在气象);惟有将“散”内在为作家的写作神态,好散文才可能诞生。其实,如果以“散”为神态,以“气”为统摄,你的文字放得再开,再散,它依然是集中而和谐的;相反,失去了“散”的神态,没有了“气”的贯彻,你的文字哪怕再集中,也只能是僵化而做作的。 这或许就是散文的秘密之一吧。 -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馀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日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

中国文人的另类面孔
《中国文人的另类面孔》主要内容:只要有人群,就有两面派;有两面派,就有人腰里挨刀;有人腰里挨刀,就有两面派封官加爵;有两面派封官加爵,就会鼓励更多的两面派产生。这种恶性循环,于乱世尤盛。这和鬼子来了,汉奸则多,运动来了,嗜血者便亢奋,是差不多的道理。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说到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两类中国人的斗争史。一是讲节操的正人君子,二是不讲节操的小人败类。这部斗争史,也是讲节操的人基本上吃亏,而不讲节操的人总能得逞于一时的伤心史。 -

冬天里的春天(全二册)
小说以革命干部于而尤重返故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表现了“春天在人民心里”的主题。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的队长,解放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揭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于而龙和芦花当年都是石湖贫苦的渔民,为了还高门楼王家的债,于而龙喝了药酒到冰湖中捉鲤鱼险些丧命。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毅然举起了革命的火把,与高门楼王家斗,与日寇、湖匪斗,像胶龙和旋风出生入死战斗不息。于而龙后来又作为骑兵团长,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又作为第一批创业者,在沼泽地里建起了大工厂。可是他的结发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牺牲。芦花有着异常坚定和敏感的阶级感情,她与高门楼王家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她像一尊威严的战神,把王家老大的头颅掷在老二王纬宇的面前。王纬宇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份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又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在工厂又搞什么“红角”,凡事左三分,最后他刽子手的面目终于被揭露了。小说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更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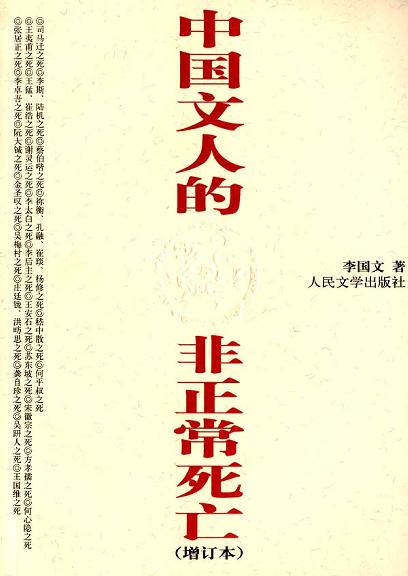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冤无头,债无主 ■书评 □丁国强 在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下,中国文人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无论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还是天子呼来不上船、仰天大笑出门去,都难以逃脱受迫害、遭打击的厄运。祸从文起,中国封建统治者有一整套对付知识分子的办法。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深入剖析了这种病态的历史现象。 所谓的“非正常”死亡指的是打破生老病死的规律,人为地中止性命。人生识字忧患始,每一朝代的统治者后面都堆积着书生文人血迹斑斑的头颅。这一切,在统治者看来,又是极其正常的,折磨和蹂躏知识分子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心理平衡或某种安全感。两千多年,大多数中国文人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而放弃了尊严,选择了苟活,发明了万千溜须拍马的技巧,将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批判性的缺失决定了文人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在得志与失意之间徘徊,忽而愤愤不平,忽而高呼万岁,忽而隐姓埋名,忽而上蹿下跳。他们把精神尺度与“能保其身”的生理目标放在一起,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混上个一官半职,从而获得了体制内生存的合理性。 乡村野夫如贾府里的焦大即使破口大骂、老拳相向也无妨,顶多挨一顿揍,啃一嘴屎,而文人却不能发一句牢骚、瞪一个白眼,否则就有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是表露自己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也容易被看成是变相的造反。多一句不是,少一句也不是。聪明的文人于是学会了委蛇之术,时时处处看掌权者的眼色行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时代,苟活是文人不得已的选择,与装疯发狂、拂袖而去相比,摧眉折腰侍权贵,是一种极为压抑的生存方式,不是中国文人没有火气,而是因为心中的火焰除了把自己烧焦以外,并不能改变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苟活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的生存方式,司马迁“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终于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活着,一切都有可能,断绝了生命,也就断绝了希望,断绝了文化的命脉。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苟活的文人都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志,他们中的更多人耽迷于权力,拼命上爬,不择手段,最终在权力场上粉身碎骨。 “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不过,这世上的文人总是难以消除干净,他们无法控制表达的欲望,所以,露头的文人总是此起彼伏。沉默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文人的内心里面却充满峥嵘。唯唯诺诺的是文人,破口大骂的也是文人,大放厥词、粪土一切的祢衡虽不失书生本色,却无意中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玩政治的文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给自己打造一副精美的棺材而已。 李国文曾谈到自己当了22年“右派”,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趴在头上拉屎撒尿都强忍下来,诸如此类软弱的事实。不管怎么说,终归是活了下来,没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搭上,才有今天的思如泉涌,墨气冲天。李国文嫌谢灵运过于张狂玩掉了脑袋,否则,还会留下更多更美的山水诗,殊不知,要求中国文人专心致志地搞“纯文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除了与统治者的残暴密不可分之外,后面都有一个让人肠断的性格悲剧。如果文人们都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忍辱负重,学会了避重就轻,侥幸熬过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文祸,恐怕也未必还能写出那等荡气回肠的文字来。贪生者当然可以笑到最后,但是,文学史上笑得最好的多是短命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