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 1945-196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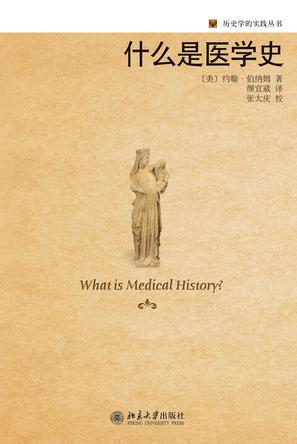
什么是医学史
《什么是医学史》内容简介:医学与健康史领域的研究近年来进展迅速。约翰·伯纳姆在《什么是医学史》中把医学史介绍给了对该领域比较生疏的读者。他让我们一窥堂奥的这个领域,一度只有医生们纵笔驰骋,而在今天,它不仅吸引着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吸引着决策者和各种类型的医务工作者。 医学史的魅力在于历史本身固有的戏剧性,医学化势力与去医学化势力之间持续的较量,尤其涉及到如下五个方面: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治疗者,从作法的巫师到技术专家;各个时代、各种文化中的病人;种种疾病,从魔鬼附身到每半小时扩大一英寸的可怕感染,还有不易察觉的环境毒害;新思想的发现与传播,所谓的新思想巨细并出,瑕瑜参见;围绕着医疗保障的无尽争论,它如何影响社会,同时又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制约。 -

疾病的歷史
什麼是流行病?什麼是造成疾病流行的原因? 流行病對於人類社會和文明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人類如何因應流行病所帶來的衝擊? 「疾病」是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文化或社會建構? 人類如何看待、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 疾病是人類共同的生物性經驗之一,其存滅與盛衰,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文明的變遷,有著緊密而複雜的關係。我們不僅隨時隨地在「感知」,也在「製造」疾病;不僅在「界定」(frame),也在「建構」(construct)疾病。本書所收錄的十三篇論文,企圖以若干個案說明人類看待、認識、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的古今之變,並探索疾病史研究的可能途徑、課題、材料、方法,以及寫作方式。 導言(節錄) 疾病也有歷史/林富士 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於一九九二年的「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會。設立研究室的目的,是為了讓既有的研究團隊能更加茁壯,並且與國內外的學者有更頻密的交流和對話。因此,在我受命擔任召集人一職之後,便邀請所內十一位同仁,在杜正勝先生的領軍之下,開始執行一項名為「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的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計畫(1998-2000)。那時,對於疾病、醫療史的各種課題,我們其實都還在摸索與嘗試之中,因此,每年都會召開專題研討會,邀請各界學者到史語所相互切磋。三年之間,陸續召開了:一、「中國十九世紀醫療」研討會(1998年5月22日);二、「潔淨的歷史」研討會(1998年6月11-12日);三、「養生、醫療與宗教」研討會(1998年1月9日);四、「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1999年6月11-12日);五、「疾病的歷史」研討會(2000年6月16-18日)。 其中,以「疾病的歷史」研討會規模最大,成果也最為豐碩。當時,總共有三十一位學者提交了三十篇論文。學者之中,以國籍或地區來說,美國五人、中國五人、日本兩人、韓國一人、香港一人,其餘十七人為本地學者。以專業背景來說,醫學九人、藥學兩人、文學三人、生物學一人、人類學一人,其餘十五人為歷史學。三十篇論文共分十個場次進行,前三場均以「流行病」為主題,共九篇論文。接續的七場,主題依序為:四、疾病觀念與醫療技術;五、疾病與文化;六、身心與疾病;七、性與疾病;八、生活方式與疾病;九、疾病與政治論述;十、文獻材料與疾病史研究。除此之外,在「綜合討論」時,我則提交〈「疾病的歷史」研究芻議〉一文,供作討論的基礎。 研討會召開之後,轉眼之間,竟已超過十年。在這之間,有些發表人已退休或離開原本任職的機構,有些則由研究生躋升為大學教師。而他們也大多將會議論文改寫,或發表在國內外的學術期刊,或是收入其論文集、專書之中,也時為學界所引述或討論。因此,似乎已無結集出版之必要。 然而,時至今日,疾病依然困擾著無數的個人和群體。人類不僅隨時隨地在「感知」疾病,也在「製造」疾病;不僅在「界定」(frame)疾病,也在「建構」(construct)疾病。因此,我覺得仍有必要透過論文集的編輯與出版,傳達當年探索「疾病史」的若干歷史經驗。當時我們頻頻扣問的幾個互相糾結的課題包括: (一)什麼是流行病?什麼是造成疾病流行的原因? (二)流行病對於人類社會和文明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三)人類如何因應流行病所帶來的衝擊? (四)「疾病」是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文化或社會建構(cultural/social construction)? (五)人類如何看待、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 這些問題並非由我們首先提出,也不會因我們的解答而消失。但我相信,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十三篇文章,仍然可以作為思考的起點或參考,仍有攻錯之效。 首先,林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一文,以中國史為例,概略介紹了疾病史研究的途徑、課題、材料、方法,以及寫作方式。其次,李建民〈祟病與「場所」:傳統醫學對祟病的一種解釋〉、陳秀芬〈在夢寐之間:中國古典醫學對於「夢與鬼交」與女性情欲的構想〉、李貞德〈「笑疾」考:兼論中國中古醫者對喜樂的態度〉、張嘉鳳〈「疾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病〉,范家偉〈漢唐時期瘧病與瘧鬼〉、廖育群〈關於中國古代的腳氣病及其歷史的研究〉、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等七文,分別探討中國傳統醫學(或宗教)對於祟病、鬼交(夢交、夢鬼交)、笑疾、疾疫、瘧病、腳氣病、痲瘋病的多樣看法、語言歧義、以及概念的古今之變。再者,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一文,揭示了中國的痲瘋「經驗」與「在地知識」如何與英國的醫者及醫學觀念互相激盪;劉士永〈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演變〉一文,則是解析近代西洋的公共衛生及醫學觀念如何影響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疾病結構」的演變。此外,劉錚雲〈疾病、醫療與社會: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相關史料介紹〉一文,以官方文書「內閣大庫檔案」,闡明清代社會常見的民眾疾病和傳染病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蔣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一文,則是利用私人日記解析晚明士紳家族的疾病與醫療經驗。最後,邱仲麟〈人藥與血氣:「割股」療親現象中的醫療觀念〉一文,則是透過「割股」療親現象,探討中國醫學中相當具有特色的「人部藥」和「血氣」觀念。 這樣的內容安排,自然揭露出歷史學界對於疾病史研究的興趣,主要還是在於醫學體系中的「疾病」觀念(包括疾病分類與病因論)的演變及其文化特性。同時,這也顯示,無論是「古今之變」的比較、醫學社群或社會群體內部的比較,還是中西醫學的比較,都是疾病史研究常用的手法。此外,從上述論文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運用不同類型的材料,才可以呈顯更多疾病史的不同面向。總之,透過本書的十三篇論文,以及我們過去摸索的經驗,我認為,對於疾病史的探索,只有透過跨學科的對話與整合,跨地域團隊的分工與合作,並且針對各種新、舊課題,廣泛使用各種方法、工具與材料,才能有重大的突破,並有助於我們對於人類整體歷史的理解。 選文(節錄) 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李尚仁 一、前言 歷史上痲瘋(leprosy),長久以來,一直和各種宗教迫害、文化成見糾結難解,若要探討疾病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痲瘋的歷史無疑蘊含豐富的材料。痲瘋病患在西方受到強烈歧視的原因,可回溯至《舊約聖經》〈利未記〉第十三、十四章,記載「痲瘋」是種令上帝不悅的不潔之病。後世一些學者認為〈利未記〉翻譯發生錯誤,原文的zara’ath(或tsara’ath)係泛指不潔的皮膚病,卻被誤譯為leprae(痲瘋),為西方痲瘋病患的污名種下宗教根源。痲瘋的症狀容易與梅毒、苺疹病(yaws)乃至數種皮膚病混淆,正確診斷並不容易,史料記載的「痲瘋」是否就是現代醫學定義下的痲瘋,其實大有疑問。中世紀痲瘋的真實身分在醫學界與史學界爭議不斷。早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國醫師暨歷史學者布黑(F. Buret)就發表異議,認為中世紀的痲瘋其實是梅毒。部分學者還認為,由於當時常由神職人員鑑定痲瘋病患,誤診的可能性非常高。考古學者於丹麥涅斯特華德(Naestved)的St. Jorgens痲瘋病患墳場,挖掘出西元一二五○年至一五五○年間下葬的屍體,遺骨經古病理學(paleopathology)檢驗,斷定死者生前患有痲瘋。然而,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考古發掘只能證明此一疾病當時已存在歐洲,卻無法保證史料記載的「痲瘋」病例罹患的都是現代醫學定義下的痲瘋。痲瘋的回溯診斷(retrospective diagnosis)仍舊問題重重。 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的痲瘋研究有許多重要的發展,支持不同學說的醫師,對於痲瘋病因有數種不同的看法與解釋,痲瘋的疾病分類學(nosology)研究也發生爭論,痲瘋如何傳播的問題更是爭議的焦點。挪威醫師韓生(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於一八七三年發現痲瘋菌,為現代醫學的痲瘋知識奠立重要基礎。為紀念他的成就,醫界甚至將痲瘋改稱為Hansen’s disease。然而,Hansen’s disease的致病細菌Mycobacterium leprae感染力甚弱,許多人對此細菌天生免疫,即使與痲瘋病患密切接觸也不會染病。因此,韓生的發現公諸於世之後,西方醫界對痲瘋是否會傳染仍爭議甚久。十九世紀西方醫學對痲瘋的傳播途徑與疾病身分(disease identity)的研究與爭議,是個有待探討的醫學史議題。目前有關十九世紀痲瘋病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痲瘋遭到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過程,以及教會收容與治療痲瘋病患的慈善醫療措施。澳洲、印度與美國等個別國家控制痲瘋傳播的醫療衛生政策,尤其是痲瘋療養病院的設立以及病院管理措施,也有不少的歷史研究。殖民醫療體制對痲瘋病患的管制或隔離措施,如何建構出被殖民者的身分(identity),以及被殖民者如何反抗這些措施等課題,近年也出現幾篇精采的殖民醫學史研究。然而整體而言,關於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的痲瘋研究,目前的史學探討仍相當不足,即使受現代醫學推崇為痲瘋病因發現者的韓生,他的痲瘋研究經歷,以及他的學說被醫界接受的曲折過程,相關的歷史研究亦十分薄弱。 十九世紀中國被視為痲瘋主要盛行區域之一,然而西方醫學界在中國進行的痲瘋研究,目前仍是醫學史甚少觸及的領域。本文以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為主題,探討十九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來華英國醫師何以對同樣的疾病現象做出相當不同的觀察與解釋,並分析他們關於痲瘋病因和傳播方式的討論。本文以英國倫敦的皇家醫師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與英國來華醫師康德黎(Jame Cantlie,1851-1926)分別於一八六○年代與一八九○年代進行的痲瘋研究為例,指出這兩篇報告對於痲瘋是否會傳染的問題,雖然看法南轅北轍,但使用的研究方法其實大同小異,兩者皆倚重英國殖民醫學、殖民科學乃至殖民行政管理所常使用的調查(surveys)研究方法。這兩篇報告呈現的醫學觀點轉變,則和歐美的帝國主義擴張活動、種族主義高張、排華風潮興起,以及熱帶醫學的專業化,有著密切關係。本文並且討論來華英國醫師對於當地資訊(native information)與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使用,分析他們如何透過對中國資料的不同詮釋,來支持其截然不同的痲瘋病因論與傳播學說。 二、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界對痲瘋傳播方式的探討 有關痲瘋的現代醫學知識濫觴於十九世紀,然而確立痲瘋是細菌疾病的過程卻充滿曲折。歐洲在十四世紀發生了史稱「黑死病」(the Black Death)的嚴重瘟疫(plague)之後,曾於中世紀造成大恐慌的痲瘋逐漸消退,到了十六世紀幾乎完全銷聲匿跡,除了北歐之外罕見其蹤。十九世紀前半,挪威是少數仍有本土痲瘋病例的歐洲國家,其痲瘋研究亦領先群倫。挪威醫師丹尼爾森(Daniel Cornelius Danielssen)和博克(William Boeck),對柏根(Bergen)地區痲瘋病患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他們分析了兩百一十三名病人,發現其中88%有血緣關係。因此,他們認為痲瘋是遺傳病,而且有隔代遺傳(atavism)現象,有時疾病遺傳隔了一代、兩代甚至三代才出現。例如某人得病,子女安然無恙,但孫子或曾孫卻又罹患痲瘋。丹尼爾森和博克在一八四七年出版研究成果,隔年該書法譯本出版。由於其一手研究內容詳盡、資料豐富且觀察仔細,使得該書論點對當時歐洲醫學界產生很大影響。細胞病理學(celluar pathology)創建者之一的偉大病理學家維考(Rudolf Virchow),宣稱此書是關於「痲瘋的現代生物學知識的濫觴」。丹尼爾森和博克的學說,由於否認痲瘋傳染的可能,也減少了歐洲人對於痲瘋可能透過傳染散佈而再度出現於歐洲的恐懼。 十九世紀後期,痲瘋再度引起歐洲大眾的憂慮。這並不是因為痲瘋又在歐洲流行,而是歐洲的帝國主義擴張活動,使得海外歐洲人接觸痲瘋病患的機會大增。痲瘋成為殖民政府必須面對的醫療問題,而且殖民經濟活動往往導致勞動人口流動,為數眾多的奴隸、苦力與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ur)離鄉背井,移居千里之外。這些廉價勞力主要來自亞洲與非洲,而痲瘋在其中一些區域原本就是風土病(endemic disease)。移民現象導致部分歐洲人擔心痲瘋是否會隨著這些流動人口四處散佈,甚至傳到歐洲。加上當時種族主義高張,歐洲人普遍認為有色人種衛生習慣不良、身體污穢不潔,使得他們更加懷疑移民會散播痲瘋。原本沒有痲瘋病例的夏威夷,在一八六○年代出現多起痲瘋病例,在西方引起嚴重關注。這個事件也對痲瘋遺傳說構成很大挑戰,因為遺傳說很難解釋為何原本沒有痲瘋的區域,會突然出現許多新病例。這個事件不只再度導致西方醫界爭論痲瘋是否會傳染,也使得一般民眾害怕痲瘋可能傳入歐洲。 在討論痲瘋傳播方式時,十九世紀西方醫師提到「傳染」,所用的字是「contagious」,這個概念指的是「接觸傳染」,亦即透過人與人或人與物的直接接觸來傳染。當時並非所有學者都認為接觸傳染原(contagion)是微生物,認為傳染病病因是細菌等微生物反而是醫界少數派的主張。要到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德國細菌學家科霍(Robert Koch)崛起之後,細菌學說(germ theories)才日益受到重視。十九世紀許多西方醫師認為「感染原」是一種化學毒素或酵素,一旦接觸或吸入會導致血液敗壞,產生出更多的毒素而引起疾病。感染原也是一種「刺激因」(exciting cause),會削弱病人的體質(constitution),使得體質原本不佳的人生病。接觸傳染的疾病(contagious disease)既有別於遺傳疾病(hereditary disease),也不同於瘴氣疾病(miasmatic disease)與瘧疾(malarial disease)。此外,當時對於「contagion」與「infection」也有清楚區別。後者類似今天的空氣傳染的概念,例如天花與麻疹等傳染力強、不需要緊密接觸就會染上的疾病,就被歸類為「infectious disease」。「瘴氣疾病」通常指腐敗的動、植物與穢物散發出惡臭毒素所導致的疾病。「瘧疾」主要指熱帶地區潮濕的腐植土或沖積土,在強烈太陽曝曬下散發出有害氣體,導致間歇發作的熱病(intermittent fever)。在十九世紀的醫學理論中,這些名詞的意義與現代醫學的定義不盡相同,必須先釐清這些基本概念,才能瞭解當時西方醫界有關疾病傳播方式的爭論。 在海外擁有大批殖民地的英國,對於痲瘋是否會透過接觸而傳染自是極為關切。這不只牽涉到殖民地居民的健康,也攸關痲瘋是否可能傳入英國本土。加勒比海溫渥島(Winward Island)的總督,建議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痲瘋病情進行有系統的調查,英國政府因而在一八六二年委託皇家醫師院進行相關研究。 皇家醫師院向海外歐洲醫師與外交官發放問卷,詢問當地痲瘋病情與相關資訊。調查完成後,皇家醫師院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痲瘋會傳染。《痲瘋報告》指出:「全世界不同地方的觀察者見解一致,都相當反對痲瘋會傳染的看法。」《痲瘋報告》特別提出「就這點而言,痲瘋療養院工作人員經驗得來的證據,特別具有決定性」。許多痲瘋療養院工作人員長年與痲瘋病患接觸,卻沒染病。皇家醫師院的調查委員會認為,這點足以證明痲瘋不會傳染。此外,該委員會發現「相關意見幾乎毫無異議地認為,痲瘋通常會遺傳」。然而,《痲瘋報告》還是審慎指出,有些病患身上「無法追查出遺傳的傾向」,因為這些病例的家族病史無法找出痲瘋的先例。因此,「到底有多大比例的病例是遺傳而來,即使不是完全無法斷定,通常也極難斷定」。《痲瘋報告》結論還特別強調痲瘋會隔代遺傳。就預防措施而言,皇家醫師院主張廢除任何會影響痲瘋病患權益的法律,反對隔離與拘禁病人,也不支持限制病人旅行遷徙。換言之,皇家醫師院勞師動眾大舉進行痲瘋調查,最後得到的結論,卻無異於以丹尼爾森和博克為代表的傳統主流學說。該份《痲瘋報告》的〈結論〉還在注釋中,大量摘譯與轉述丹尼爾森和博克的主要論點,並且大表贊同,視之為權威意見。 皇家醫師院的調查所觸及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痲瘋病是否是個獨立的疾病實體?或者它只是其他疾病所引起的症狀或併發症?當時有些醫師認為某些疾病和痲瘋密切相關,甚至認為它們其實是同一種疾病的不同症狀表現。象皮病與梅毒這兩種疾病就常和痲瘋混為一談。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指出:「許多觀察者,尤其是在印度的觀察者,認為痲瘋是梅毒的毒素所激發的,兩者是相關的疾病。」《痲瘋報告》還指出,由於「阿拉伯象皮病(Elephantiasis Arabum)(又稱『巴貝多腿』〔Barbadoes Leg〕或『交趾腿』〔Cochin Leg〕),和痲瘋常是同一個地方的風土病,有時兩種疾病還出現在同一個病人身上,因此有些人認為它們是相關的疾病」。然而,皇家醫師院調查之後認為痲瘋是獨立的疾病,與其他的疾病無關。《痲瘋報告》還特別引述丹尼爾森和博克的說法:「我們對痲瘋的描述顯示,它是個特殊的疾病,一旦完全發病,就不會和其他疾病混淆。」這一點是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最沒有爭議的部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痲瘋是個獨立的疾病實體,已經成為西方醫界主流共識了。 皇家醫師院認為痲瘋是遺傳病而非傳染病,代表了當時英國醫界的主流意見,而得到不少支持。就連在印度對象皮病(elephantiasis)做出原創研究的路易斯(Timothy Richard Lewis,1841-1886)與其同僚D•D•康寧漢(D. D. Cunningham,1843-1914),也支持痲瘋遺傳說而反對傳染說。然而這份《痲瘋報告》並沒有平息眾議,痲瘋的病因與傳染方式在英國醫界仍是爭議不休的議題。著名的皮膚科醫師福克斯(Tilbury Fox)在談到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時指出: ……許多寄回英國的報告,都是領事或其他非醫界人士寫的。這些報告必然包含主流觀點與人們的偏見,有些〔偏見〕還相當地驚人。由於沒有透過嚴格的醫學分析與批評來篩選事實,如此的來源必然含有相當程度的錯誤。這些錯誤又會滲透委員會的工作,使其失效。其實,他們所處理的〔材料〕在相當程度上等於是道聽塗說。 一八七三年在柏根痲瘋病院工作的挪威醫師韓生,宣稱找到了引起痲瘋的細菌,使得痲瘋傳染說聲勢大振。然而,韓生的發現也未能使爭議底定,因為英國醫界在一八七○年代尚未普遍接受細菌學說,許多醫師認為細菌學說太過簡化,忽略了環境其實在疾病發生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所以如此,並非全然因為英國醫界過於保守而無法接受新學說。在當時英國醫界對細菌學說激烈辯論中,「沒有任何研究者能明確區分不同的微生物,以確認某個特定疾病是由某種特定生物所引發的」。在這種情況下,光是宣佈在顯微鏡下看到微生物出現在痲瘋病患的組織,並不足以讓醫學社群放棄接受已久的學說而改奉新說。 -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
房內是一位富貴之家的孕婦,獨自半蹲地架在衡木上生產。房外則是她的公公,陪同來助產的高僧,隔著窗戶教她調息。西元六世紀一個不可思議的分娩故事,先後經兩位士大夫抄錄和轉載。這些男性醫學專家對產婦和助產婦的評價,透露了什麼樣的身體觀與性別觀?遭到品頭論足的女性,又表現了哪些醫療照顧上的能力與特色?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書從生育文化入手,介紹求子、懷胎、分娩的方法,乃至避孕、墮胎的手段,藉由重建各種醫方及其論述,說明中國婦科醫學逐漸成熟的過程。接著,以乳母與產婆為範例,進一步探討女性作為照顧者,乃至醫療者時,所面臨的待遇、評價與挑戰。最終,期望在一千五百年後的今天,從性別的角度,重新回顧女性參與生老病死的歷史。 自序 第一章 導論——從一則高僧助產的故事談起 第二章 求子醫方與婦科濫觴 一、前言 1.生育的壓力 2.所謂「醫方」 二、房中術求子及其養生脈絡 1.房中術求子 2.求子與養生異同 三、草藥求子與安胎 1.醫方中的無子論述 2.草藥求子 3.安胎藥方 四、外象內成的轉胎、養胎與胎教 五、結論:中國婦科醫學之濫觴 第三章 生產之道與女性經驗 一、前言 二、入月 1.服藥滑胎 2.設帳安廬 三、分娩 1.下地坐草 2.助產失理 3.難產救治 四、產後 1.新產安危 2.在蓐保健 五、生產之道的社會意義 1.分娩中的產婦、胎兒與丈夫 2.醫護行為與貴賤之別 3.婦產科發展與助產問題 4.隔離、禁忌與產乳不吉 六、結論 第四章 墮胎、絕育和生子不舉 一、前言 二、「生子不舉」情境多端 三、因產育禁忌而「生子不舉」 1.產孕異常 2.時日禁忌 四、以「生子不舉」節制家庭人口 1.貧困不舉 2.棄此保彼 3.棄殺女嬰 4.生男勿舉 五、「生子不舉」的地域性、方式轉變與時代分布 六、「生子不舉」的懲處與譴責 1.殺子刑律 2.士人輿論與宗教勸戒 3.家庭倫理 七、「生子不舉」的救濟與防範 1.寬政與胎養令 2.接濟與收養 3.墮胎、絕育與人工流產 八、結論 第五章 重要邊緣人物——乳母 一、前言 二、乳母現象 三、乳母的來源、選擇與職務 1.乳母的來源與出身 2.乳母的選擇與規範 3.乳哺、教養與救難盡忠 四、乳母的待遇與評價 1.乳母的待遇和影響力 2.乳母的評價與定位 五、結論 第六章 女性醫療者 一、前言 二、生育文化中的女性醫療者 三、女性治療各種疾病 四、女性醫療者的身分、技術及其特色 五、結論 第七章 危險卻有效——製藥過程中的女性身體 一、前言 二、合藥忌見婦人 三、從月水入藥到女體為藥 四、結論:人藥的性別分析 第八章 男女有別——家庭中的醫護活動 一、前言 二、健康照顧符合女性倫理角色 1.接觸、觀察與衛生保健 2.延醫、調藥與奉湯 3.祈禱、割股與棄保 三、疾病護理乃男子孝悌異行 1.父母唯其疾之憂 2.嘗惡、吮膿、祈禱與割股 3.尋藥之旅 4.以護進醫 5.「衣不解帶、親嘗湯藥」的孝悌典範 四、結論:醫護活動的性別分析 第九章 從域外看中國——《醫心方》及其婦科醫學論述 一、《醫心方》之撰著與傳寫 二、《醫心方》以胎產為婦人諸病所由 三、《醫心方》引《產經》及其「任婦月禁脈圖」 四、「中國醫學日本化」:偏重胎產的婦人方傳統 第十章 餘論——加入性別的中國醫療史 徵引書目 索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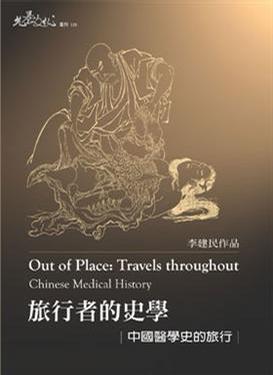
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
《旅行者的史學》探討醫學在中國歷史裏的建構和演變,以及衍生的文化、政治、社會、甚至性別意義。醫學不僅操練「望聞問切」的技術,也是一個文明認識生命,想像身體,辯證知識體系的入口。本書旁徵博引,呈現中國醫學傳統極其複雜多元的面貌,案例分析的部分尤其引人入勝。任何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興趣的讀者,都不會願意錯過! -

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生命医疗史系列: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所收录的17篇论文中可以得到解答了:中国的政治由大一统的格局走向分裂与多元。而在宗教方面,新兴的本土道教和外来的佛教逐渐茁壮长大,传统的巫觋信仰则大力推动厉鬼崇拜,并广设祠庙与神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