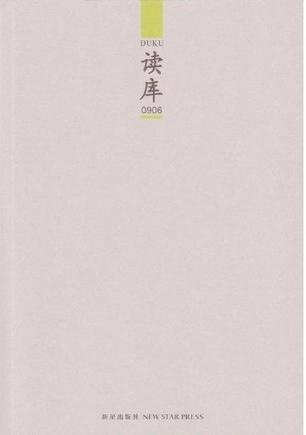還是拍電影吧,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賈樟柯
導演是什麼?導演該做什麼?
當每個人都能拍一部片的時候,導演的價值又在哪裡?
在世界各影展獲獎無數的賈樟柯,
從一位想說話的新生代導演,
到以自己的鏡頭、為這個時代發聲。
他記下了1996-2008的拍片心路歷程,
為所有想拍電影的年輕人提供了另一扇風景。
「1990年,我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不想再讀書,想去上班自己掙錢。我想自己要是在經濟上獨立了,不依靠家庭便會有些自由。我父親非常反對,他因為 家庭出身不好沒上成大學便讓我去圓他的夢。這大概是家庭給我的不自由,我並不想出人頭地——打打麻將、會會朋友、看看電視有什麼不好?我不覺得一個人的生 命比另一個的就高貴。我父親說我意識不好,有消極情緒。問題是為什麼我不能有消極情緒呢?我覺得杜尚和竹林七賢都很消極,杜尚能長年下棋,我為何不能打麻 將?我又不妨礙別人。多年後我拍出第一部電影《小武》,也被有關人員認為作品消極,這讓我一下想起我的父親,兩者之間一樣是家長思維。
小的時候看完《西遊記》,我一個人站在院子裡,面對著藍天口裡念念有詞,希望那一句能恰巧是飛天的咒語,讓我騰空而起,也來一個跟頭飛十萬八千里。這些年 跟頭倒是摔了不少,人卻沒飛起來。我常常想,我比孫悟空還要頭疼。他能飛,能去天上,能回人間,我卻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帶給我的一切。太陽之下無新事,對 太陽來講事有些舊了,但對我來講卻是新的。所以還是拍電影吧,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賈樟柯
賈樟柯談「大片」:
電影作為一個生意,只要能融到資本,投入多少都沒關係,收入多高都沒問題。問題在於它的操作模式裡面,具有一種法西斯性,它破壞了我們內心最神聖的價值。這個才是我要批評的東西。
我記得當時大家在批評《十面埋伏》的劇本漏洞時,張藝謀導演就說,這就是娛樂嘛!大家進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評《英雄》時,他也說:「啊,為什麼 要那麼多哲學?」問題在於《英雄》並不是沒有哲學,而是處處有哲學,但它是我們非常厭惡、很想抵制的那種哲學。可當面對批評時,他說,我沒有要哲學啊!處 處都在談「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學嗎?你怎麼能用娛樂來回應呢?這樣的偷換概念,說明你已經沒有心情來面對一個嚴肅的文化話題。這是很糟糕的。
作為一個導演,他們沒有自己的心靈,沒有獨立的自我,所以他們在多元時代裡無法表達自我。原來那些讓我們感到欣喜的電影,並不是獨立思考的產物,並不能 完全表達導演本人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國那時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託了當時的哲學思考、文學思考和美學思考。所以到《英雄》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個我 們曾經欽佩的導演,一旦不依託文學進入商業電影時,他身體裡的文化基因就會死灰復燃。他們感受過權威,在影片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權力是有嚮往的,對權 力是屈從的。所以你會發現一個拍過《秋菊打官司》的導演,在《英雄》裡反過來卻會為權力辯護。
賈樟柯談「自製電影」:
在法國的一家影院,我觀看了文德斯的最新紀錄片《樂土浮生錄》(Buena Vista Social Club)。這部主要拍攝於古巴,講述幾個老爵士樂手生活的影片,也是用數碼技術拍攝,而後轉為膠片的。銀幕上粗顆粒的影像閃爍著紀錄的美感,而數碼攝像 機靈巧的拍攝特點,也為這部影片帶來了豐富的視點。觀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觀眾熱情的掌聲,不禁讓我感慨,一種新的電影美學正隨著數碼技術的發展而成型。數 碼攝像機對照度的低要求,極小的機身,極易掌握的操作,極低的成本,都使我們看到一種前景。
有了VCD,我們有機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好電影;有了數碼攝像機,我們能夠輕易地拍下活動影像。
賈樟柯談「誰在開創華語電影的新世紀」:
楊德昌、王家衛、李安的電影正好代表了三種創作方向:楊德昌描繪生命經驗,王家衛製造時尚流行,李安生產大眾消費。而這三種不同的創作方向,顯現了華語 電影在不同模式的生產中都蘊藏著巨大的創作能量,呈現了良好的電影生態和結構。今天我們已經無需再描述這三部電影所獲得的成功,在法國,《一一》的觀眾超 過了30萬人次,《花樣年華》超過了60萬人次,而《臥虎藏龍》更高達180萬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