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报案研究
《苏报案研究》是发生在一百年多前的一件惊天大案,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著名事件。《苏报案研究》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包括英美外交文书、《纽约时报》等英文报纸和苏报案审讯英文详细记录,披露这一事件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如苏报案到底因何引发,列强为何介入,列强态度有何异同,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内幕究竟如何,苏报案是如何审理的,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真实表现到底怎样?从而为再现苏报案历史做出了新的贡献。《苏报案研究》还研究了苏报案发生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外报刊、政治宣传读物以及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对章太炎和邹容英雄形象的建构过程,说明一个因缘际会的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赋予各种政治意义的,事件的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又是怎样被神圣化的。 -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主要内容: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入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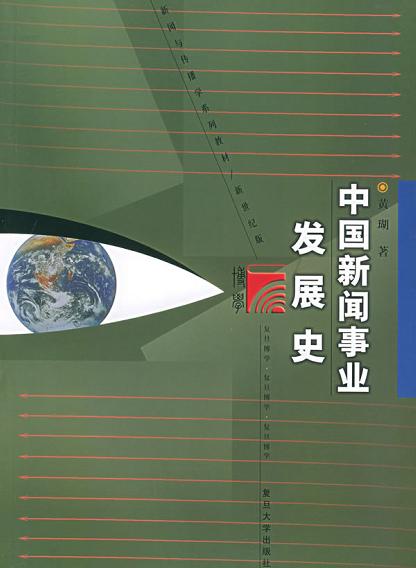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新世纪版)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博学”精品教材《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新世纪版)中的一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新世纪版)以崭新的视角,即以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为脉络,阐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作者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继承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以其开放性的视野和国内外新闻传播文化的底蕴,形成了这部教材兼专著。 -

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大公报》之崛起,一本文人论政,承袭旧风,屡有发扬。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曰不党,不为一党之见;曰不卖;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向外界一分经济援助;曰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曰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从于众。此四者。实得文化论政宗旨之精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由些得保障。 如果有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文化证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斯 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大公报人诚然政治见解各异,而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惟人民利益是从。时代的进代,历史斩进步,《大公报》之可贵者,乃在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其独立精神。 -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全书追溯中文近代报刊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挖掘出大量散佚于英、美、日和香港等地珍贵的报刊原件、翻版和抄本,去伪为真,纠正了自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报史专著不少错误的记载和“定论”。内容论及1815-1874年60年间中文报刊的变化,清晰地勾勒了中国代代报业萌芽与成长期的特征,为这一领域的补白之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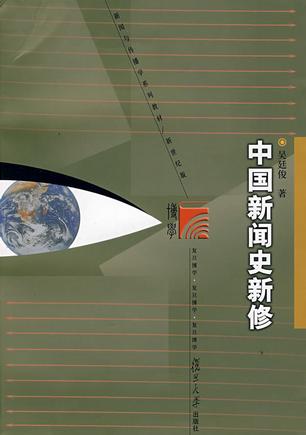
中国新闻史新修
本书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在已出版多本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本集大成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著作。全书以时间为序,“上编”、“中编”和 “下编”分别叙述了“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并用“补编”的方式叙述了我国台、港、澳地区1949年以来新闻事业的变迁史。作者认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新闻事业的形态特征分别是“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和“定于一尊”。这是“史实”的一条线。“绪论”和各章“简论”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线——“史论”。基于各章史实,本书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在横向上论述了在中国环境中主要生长出了“利器媒介”、“喉舌媒介”和“官营媒介”;在纵向上论述了中国媒介发展的沿革呈现“承袭型”,发展的动力是“政治推进”,生存方式为“依附生存”。此外,无论是“史”还是“论”,本书对1949年以前的民营媒介和自由主义报刊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本书被方汉奇教授誉为“体例新,内容新,观点新”,“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开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理论勇气”,以及“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全局的和准确的把握”,并认为此书于“史胆、史识、史才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十分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