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秉烛谈
-

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张一渠君是我在本省第五中学教书时候的同学。那时是民国二年至六年,六年春季我来北京,以后没有回去过,其时张君早已毕业出去了。十九年冬忽然接到张君来信,说现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出儿童一切用书,叫我给他帮忙。这事是我很愿意做的,因为供给儿童读物是现今很切要的工作,我也曾想染指过的,但是教书的职业实在是忙似闲,口头答应了好久,手里老是没有成绩,老实说,实在还未起手。看看二十年便将完了,觉得这样迁延终不是事,便决心来先编一小册子聊以塞责,待过了年再计划别的工作。写信告诉张君,他也答应了,结果是这一册《儿童文学小论》。 这里边所收的共计十一篇。前四篇都是民国二三年所作,是用文言写的。《童话略论》与《研究》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后来县教育会要出刊物,由我编辑,写了两篇讲童话儿歌的论文,预备补白,不到一年又复改组,我的沉闷的文章不大适合,于是趁此收摊,沉默了有六七年。民国九年北京孔德学校找我讲演,才又来饶舌了一番,就是这第五篇《儿童的文学》。以下六篇都是十一二三年中所写,从这时候注意起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比我这宗“三脚猫”的把戏要强得多,所以以后就不写下去了。今年《东方杂志》的友人来索稿,我写了几篇《苦茶随笔》,其中第六则是介绍安特路阑(Andrew Lang)的小文,题名《习俗与神话》,预计登在三月号的《东方》之后再收到这小册里去,不意上海变作,闸北毁于兵火,好几篇随笔都不存稿,也无从追录,只好就是这样算了。 我所写的这些文章里缺点很多,这理由是很简单明显的,要研究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修养,而我于此差不多是一个白丁,乡土语称作白术的就是,怎么能行呢?两年前我曾介绍自己说,“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时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那么一回事,本没有什么结集的价值,夫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这个道理我未尝不知道。然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是出于意外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浅薄,但是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主张不定,反覆循环,在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之后会有读经——把某派经典装进儿歌童谣里去的运动发生,这与私塾读《大学》《中庸》有什么区别。所以我相信这册小书即在现今也还有他的用处,我敢真诚地供献给真实地顾虑儿童的福利之父师们。这是我汇刊此书的主要目的,至于敝帚自珍,以及应酬张君索稿的雅意,那实在还是其次了。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周作人序于北平。 -

瓜豆集
《瓜豆集》是周作人自编文集之一。这半年里所写的文章大小总有三十篇左右,趁有一半天的闲暇,把他整理一下,编成小册,定名曰《瓜豆集》。为什么叫作瓜豆的呢?善于做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种种的推测。或曰,因为喜讲运命,所以这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或曰,因为爱谈鬼,所以用王渔洋的诗,豆棚瓜架雨如丝。或曰,鲍照《芜城赋》云,“竟瓜剖而豆分”,此盖伤时也。典故虽然都不差,实在却是一样不对。我这瓜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 -

鲁迅的青年时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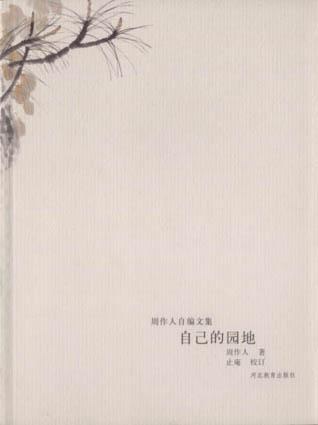
自己的园地
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作者不仅看到社会心理或群众心理庸俗的一面,更发觉了其危险的一面。他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 -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去年春天,还在给上海《亦报》写小文章,动手来编《呐喊衍义》,虽然只发表了极小一部分,但仍是继续着写,大概费了两个月的工夫,一总写了一百三十多节。这里分作两部,前部是关于《呐喊》的,后部是关于《彷徨》以及《朝华夕拾》,所以虽是两个头,实在却可以叫作“三衍义”的。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纪事实,本来与写《百草园》是一样的,不过所凭借的东西不同,一个是写国及其周围,一个是写两部小说里的人物时地。小说是作者的文艺创作,但这里边有些人有模型可以找得出来,他的真相如何,有些物事特别是属于乡土的,上物方言,外方人不容易了解,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了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这几项都是事实,因此我的工作只是记述而不是造作,就只怕见闻不周,记忆不足,说的或有错误,希望知道得更确实的朋友能够给与补正,但是要想找熟悉四五十年前绍兴事情的朋辈已经很不容易,我也曾这样找过,可是结果是很失望的。 《朝华夕拾》本来并不是小说,虽然也不是正式的自传,为便宜计也就收在里边,因为分量不多,不能独立,所以就并在《彷徨》部分里去了。原来《朝华夕拾》里可说的事实很不少,论理可以自成一卷,但是有许多都已在《百草园》里说过了,这里所说只是余下的那一部分而已。不但是《夕拾》,便是那两部小说里的人物,有好些也都在《百草园》里说过,因此如说《鲁迅的故家》可以作本书的补遗,这话可以说得,若是说本书可以作《故家》的补遗,也是一样的可以这么说的。 关于《夕拾》中在南京学堂的一段注解得很简略,因为以前曾写了一篇《学堂生活》,虽是说我自己的,但情形大抵相似,所以作为一个附录,加在后边。近时翻阅旧日记,看见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记事,也抄录了出来,当作另一个附录,虽然,这如附在《故家》后面,自然更为适当。日前偶看俞阶青先生的《诗境浅说》,联想到《曲园课孙草》,忽然记起鲁迅在三味书屋读《课孙草》的事情来。寿镜吾先生教他读这书,大概已经教他“开笔”作文了,后来“满篇”之后才叫洙邻先生批改,这事本来应当写在第三节《戊戌二》里边的,可是当时遗忘了。上文所说记忆不足的事可见是实在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忘却以前,能够记下这一点来,也正是很幸运的吧。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著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