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女与野兽》电影日记
对于所有的电影爱好者而言,阅读《美女与野兽》的拍摄日记纯粹是一种心醉神迷的享受。虽然时光流逝,这文章的魅力丝毫未减——无论从其诗意的力度,还是从对我们坦然展示电影角度而言。更确切的说,这是敞开心扉的电影。《美女与野兽》显然是一部独特的影片,摄制于法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法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法国刚刚获得解放。在那个艰难岁月,电力之类的基本资源常常非常缺乏。《美女与野兽》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技术与诗意。 这部日记具有绝对的现代性、不可思议的时代感。我们这个年代充斥的电影,多的是靠时髦的数字机器实现特效,靠后期制作众多的特技达到完美;《美女与野兽》的拍摄却把我们带回到了电影的手工艺术制作期,其技术性亦很强,但诗意却总是占据统领地位。科克托表现出一种极度的苛求——首先是针对他自己。这种工作态度与方式是21世纪的电影人必须探究与学习的。所有的电影都是一场考验,正是经过这样的考验才会产生美。我们需要阅读、再阅读这部日记,不仅仅是为了学习一种经验,更是为了从中汲取灵感,将科克托崇高伟大的事业永久传承。 -

关于电影
科克托与查理·卓别林同时出生于1889年,所不同的是,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平民的家庭,而科克托则降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家庭,自幼便浸润于上流社会的氛围中。六岁的时候,科克托便观看了卢米埃尔兄弟早期的影片《水浇园斗等,并接触到了戏剧和马戏。他九岁的时候,父亲开枪自杀。父亲的死成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魔咒,悲剧主题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循环出现,死亡与血追随着他的作品,如《诗人之血》、《双头鹰》、《永恒的回归》、《俄耳甫斯的遗嘱》等。极具艺术修养的外祖父每个周末都带他去听音乐会,他因此发现了贝多芬、李斯特、瓦格纳等,音乐的熏陶对他一生的创造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他涉足的艺术领域甚广,真正留下来的,或许正如弗朗索瓦·佩里耶所说,“还是他的电影”。他的艺术声誉主要来自于电影,他甚至被认为是法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不仅与雷诺阿、布莱松等人齐名,更作为不受教条约束、进行自由创作的艺术家典型,得到戈达尔、特吕弗、雷乃、德米等后来的新浪潮年轻导演们的仰慕。 其实,科克托直到1927年才尝试电影拍摄,而这部与一些朋友一起拍摄的、题为《让·科克托拍电影》的16毫米影片已无处找寻。当诺阿耶家族在1929年底建议他拍摄一部动画片的时候,可以说,他对电影拍摄知之甚少。然而,他很快在电影里找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新空间、新语言,最初的动画片最终在1930年变成了传世先锋派影片《诗人之血》。 如果说令超现实主义者们反感的《诗人之血》成了心理学家和电影爱好者感兴趣的典型,那么1943年拍摄的《永恒的回归》终于为他赢得了观众,这部以中世纪特里斯唐和伊泽的传说为原型的现代故事,重新燃起了他对电影的激情。而大获成功的《美女与野兽》则可以说是幻梦剧作中最杰出的一部影片。 科克托将电影作为表现自我的方式。他借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俄耳甫斯之名,唱出了诗人之歌《俄耳甫斯》和《俄耳甫斯的遗嘱》。他说:“《俄耳甫斯》曾经是我的‘总和’,我将我全部的生活都放了进去。”而“《俄耳甫斯的遗嘱》将是我对电影的告别”,“将是人们在船或火车消失之前挥动的手帕”。 于科克托而言,电影应该是以诗的形式来探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他对于电影的独到见解,在《关于电影》一书里,有着详尽的论述。他向来强调电影的艺术性,将电影称为第十位缪斯,虽然年轻,但也应像其他缪斯一样拥有高贵的身份。他多次引用穆索斯基临死时惊人的预言:“未来的艺术将是那些会动的雕像。”会动的雕像即电影,电影即艺术。他厌恶以商业为目的的电影,急功近利使电影误解它作为缪斯的神圣使命。他崇尚黑白电影,彩色就像“吸引昆虫的假花”,将淡化电影的神话色彩,使电影里会动的雕像接近现实,变得庸俗。 科克托的影片通常曲高和寡,这也许与他对电影的艺术要求吻合。他希望电影能跟其他缪斯一样,做一只母螳螂,吞噬它爱的人,让爱人的作品代替爱人活着。伟大的艺术品通常在艺术家死后获得价值。科克托影片的价值,在电影史里才充分显现出来。应该不要忘记的是,科克托还为众多法国著名导演编写了剧本,其中就有布莱松的杰作《布洛涅树林里的女人们》。因此,这位诗人电影艺术家在法国电影里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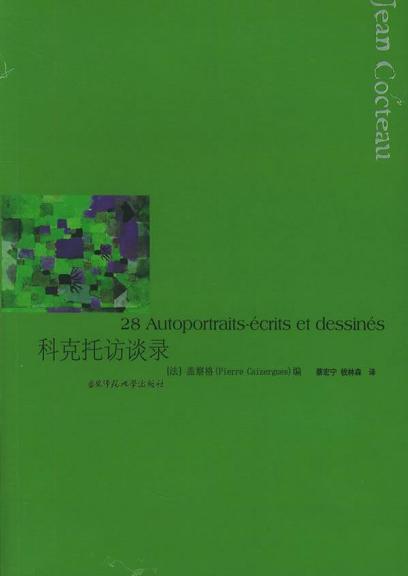
科克托访谈录
读《科克托访谈录》也许比读他的小说《可怕的孩子》或剧本《屋顶上的牛》更有益处,他在闲聊方面的天才也许远胜于他在文学上的造诣。科克托在访谈中讲过这么一段话:“才华或许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女子下车时的姿势。斯汤达写道:‘她才华横溢地下了马车。’才华是一个人的高级表达方式。而说到诗,或许是一个人最高级的表达方式。”对科克托而言,他最高级的表达方式也许不是诗,而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