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的反革命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哈耶克最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集中论述出现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 法区别开来。——约翰•格雷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 ——杨小凯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杨小凯 哈耶克思想中的许多东西——不论是批判性还是建设性的,都对我们目前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徐友渔 《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一书中描写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世界和社会意识,在法国,以圣西门和孔德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法则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 研究。他们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希望经由社会科学精英对这些规律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这种对理性的滥用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 程,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之做出了强有力的批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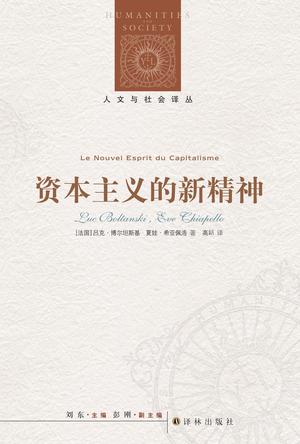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本书通过前所未有的对管理学文献的考察,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重构方式,揭示了雇主采用1968年的反文化语言发展了新的工作实践,以及更为成功和隐蔽的剥削形式。本书认为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成功仰赖于卓越批判的再起,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衰落的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重新赋予了重要性。 本书对现代社会作了有力而全面的阐述,并发展了针对现代排除模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 ——《社会学评论》 本书毫无疑问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当代经典。 ——《政治研究评论》 这部宏大的著作是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学,这一代人被资本主义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它就像一部伟大的小说,会让读者深深地沉醉其中,并会给左派的复兴提供新的武器。 ——法国《自由》杂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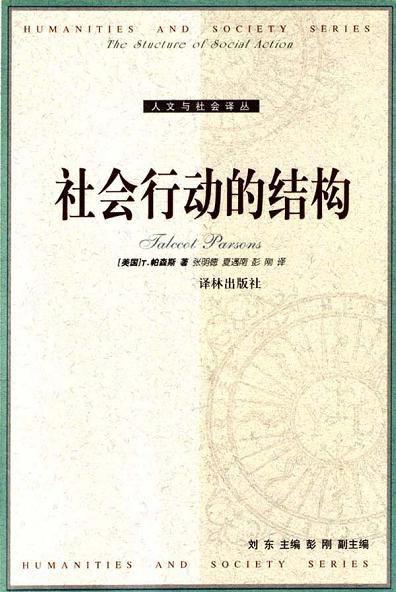
社会行动的结构
简介: 当代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巅峰之作。在这本书中,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析和吸收,重建了“一般社会行动理论”体系。本书把以目的—手段为成分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不仅确立了一门规范的社会学学科,而且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作了经典的规定。 导读: 序 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对社会理论方面一些作者的著述的第二手研究。但是,“第二手研究”有好几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也许是不为人所熟知的一种。 本书的基本目的,不是要确定和概述这些论者就他们研究的论题说了什么和有什么看法,也不是要根据当代社会学知识和相关的知识,直接探讨他们的“理论”中所提出的每一命题是否站得住脚。我们会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但重要的不是提出甚或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背景。 本书的副标题似乎已经说明了它的要旨:它是研究社会理论,而不是对各种社会理论的研究。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论者的著作中那些孤立且无联系的命题,而在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某些前辈的著作加以批判性分析就能看出其发展脉络的一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加以推理论证。把这些论者集中到一本书里论述,其一致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学派”,也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或时代,而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方面对这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分析,是阐述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结构及其在经验方面的实用意义的便利途径。 这个理论,即“社会行动理论”,不单单是一些在逻辑上互相关联的概念。它是一种经验科学理论,其中包括的那些概念关联到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东西。如果在探讨某个理论体系的发展的时候,不去涉及这个理论赖以建立及其所应用于的经验问题,就会成为一种最无谓的论证。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呆滞的“冥思苦索”的结果,也不是把一些假设中所包含的逻辑含义加以敷衍的结果,而是从事实(fact)出发又不断回到事实中的观察、推理和验证的产物。因此,本书在每个关键之处都包含有对于有关作者所研究的那些经验问题的明白论述。只有把理论与经验问题和事实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论述,才能充分理解这个理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它对科学有什么意义。 本书是作为一部前述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著作发表的。然而,通过探讨这四个人(指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译按)的著作来找出一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始末,却不是作者细致研究他们的著作的本意。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其他研究他们著作的人,都没有认为能够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一个单一的和融贯的理论体系。把他们放到一起研究是出于经验方面的原因,即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解释现代经济秩序——被不同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经济个人主义”——的某些主要特征所涉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关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即使从如此相互迥异的观点出发,也会涉及到一个共同的概念体系——这一点只是逐渐地明确起来的。这样,兴趣的焦点也正是因此而逐步地转移到阐明这个体系上来的。 从问题的脉络上说,这项研究工作早在作者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在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得到别人的教益极多,而且常常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很多是无法致谢的,谨对其中与写成本书直接有关的最重要者鸣谢如下: 在这些有直接关系的教益中,有四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最难以估量、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埃德温·F.盖伊(Edwin F.Gay)教授的教益。多年来,他一直积极关注这项研究。在这漫长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沮丧的进程中的许多关键时刻,盖伊教授的指点使作者受到鼓舞,不断激励作者使这项研究达到力所能及的最高质量标准。其次,作者的同事奥弗顿·H.泰勒(Overton H.Taylor)教授同作者接连多次讨论问题(特别是与经济理论有较直接关系的问题),对本书贡献良多,难以一一列举。以上二位教授也都阅读了本书部分原稿,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第三,劳伦斯·J.亨德森(Lawrence J.Henderson)教授对原稿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批判性审查,从而使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关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对帕雷托的著作的解释两个方面作了重要修正。最后,还要对一批批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们表示感谢。在本书酝酿阶段的大部分时间,作者一直与他们一起就社会理论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些生动的、互相交换意见的讨论中形成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思想,并使许多模糊的问题明确了。 还有两位批评家对本书特别有所助益,他们是诺克(A.D.Nock)教授和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博士。他们在阅读原稿后提出了建议和批判。诺克教授尤其对有关宗教的章节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阅读了原稿,或校订了全书或部分章节,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其中包括: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教授,约瑟夫·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教授,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亚历山大·冯·塞廷(Alexander von Schelting)博士,克拉克洪(C.K.M.Kluckhohn)教授,丹农(N.B.DeNood)教授,伊丽莎白·诺丁汉(Elizabeth Nottingham)女士,埃米尔·B.斯马里安(Emile B.Smullyan)先生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先生。斯马里安先生和本杰明·哈尔彭(Benjamin Halpern)博士对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以上人士在有关本书的专门内容方面提供了帮助。但是,对于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来说,得到的帮助绝非仅限于此。在其他方面,我特别要对两件事情表示感谢。一要感谢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由于它的惠准,本书在研究问题当中得以在书目和参考文献方面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帮助,并且在撰稿过程中在速记方面得到帮助。二要感谢我的父亲、玛丽埃塔学院(Marietta College)荣休院长爱德华·S.帕森斯(Edward S.Parsons),他承担了通读原稿的重担,在文字上加以润饰。在这样一本不可避免地比较难读的书中,任何通达流畅之处大多要归功于他。 承担原稿打印工作的是伊丽莎白·沃尔夫(Elizabeth Wolfe)小姐、艾格尼丝·汉内(Agnes Hannay)小姐和马里恩·B.比林斯(Marion B. Billings)小姐。伊莱恩·奥格登(Elaine Ogden)小姐帮助草拟了文献目录,我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37年10月 第二版序言 自《社会行动的结构》初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二年。战后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内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广泛兴趣,但不幸地发现此书已脱销,因此自由出版社将此书再出新版的决定就广受欢迎。 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决定按原书重印而不作任何改动。这样的决定并不是说,此书不可能通过修订而取得实质性的改善增色。此书的精神实质和其中许许多多的明确表述都离此甚远。作者本人的理论思考并未止步,而且倘若他此时又再来写这本书,那将会有实质性的不同,我们还可以期望,他会写得更好。 要弄出一个像是1949年新写出来的修订版,任务实在过于繁重。不仅要有许多实际改写的地方,而且在此之前,先得对本书所依据的主要素材进行仔细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这样做当然会大有收获,然而问题却在于,要对这样一本著作的收获的判断与这样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所可以有的其他用处之间,怎样作出平衡。 此种平衡中所包含的最为重要的考虑,就是将对于此前一两代人所作的理论工作的批判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提炼,与推进和当前经验研究的兴趣相关的理论问题的直接分析(而不再加工提炼批判取向)所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看看怎么做更为有利。不对此书进行全盘修订的决定,就表明了这样一个判断:就社会科学的现状而论,后一种做法对于一桩重大的时间和精力的投资而言,是一个成果更为丰硕的渠道。 《社会行动的结构》旨在主要成为对于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的、而非对于社会思想史的贡献。它对于其他著作家的研究工作的批判性取向之所以有其合理性,就是因为这是澄清问题和概念、涵义和关联的方便之门。这是一种充分利用我们的理论库存的方法。在当下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它使我们暂时停步,重新考虑那些对于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中有助于我们的原则所做出的根本决策,也就是说,“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件好事”;再就是,在我们沉浸于日常工作的情形中,可能有些资源和潜能是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了的。从汲取库存中得到的清晰明澈,为更大范围内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开启了可能性,它给人的激励是不会穷尽的。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合情合理地认定,对于其他人而言,也必定是如此。 《社会行动的结构》分析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理论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中的一场重大革命。这一研究中所讨论的三个主要人物绝不是孤立的,他们都为这个发展的“社会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我们的视野中又多了十年,但这并没有降低他们在这个运动的高峰上所处的相对位置。在达到一定高度的范围内,不止有三个高峰,然而这三个高峰比之别人要高上许多。 在社会学方面就是如此。本书的一个主要偏向,就是它相对而言忽视了整体概念体系的心理学方面——全面的修订当然会致力于在此取得平衡。在这里,至少同一代人中有一位,也即弗洛伊德,在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他的研究起点和经验关注对象有所不同,必须认为他的工作构成了同一个一般思想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在第二流的重要人物中,或许心理学比之社会学方面要丰富得多,但没有任何别人能够赶得上弗洛伊德那么要紧。情况既然如此,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置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背景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把本书的其余部分按照这样一种研究的结果进行调整——对于应该进行的那样一种修订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显然必定会令一部篇幅已经足够庞大的书更加冗长。 对于是否还有什么大致被划分为社会人类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的人物具有类似的理论重要性,也许人们意见不一。我的看法是没有。尽管比如说博伊斯(Boas)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或许有着类似的一般的重要性,而且同样是一位伟大人物,但他在同一个发展潮流中对于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所做出的贡献,与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等人不是同一性质的。在某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学思想的贡献有着头等的重要性,应该得到比之《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显然更多的强调。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尤其如此。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乃是当前基本的社会科学最迫切的要求之一。 这一根本性的理论发展就其紧要之处而论,我们可以说,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些著作家所围绕的参照系、他们充满争议的趋向、经验兴趣和思想传统,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使得他们研究工作的统一性,只有在经过艰苦的批判性诠释之后才能看到。实际上,比这还糟的是,他们之间所确实存在的差异,由于人们第二手的阐释与误解所造成的纷乱扰攘,而变得重重叠叠,难以厘清。《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主要作用之一,在我看来,就是清除了很多这种“杂乱之物”,使得某种理论体系的大致框架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对弗洛伊德的工作和人类学思想的分析所可能带来的、对于心理学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更好的理解,是我们所需要的。即使表述起来有些为难,想必也是人们所能够容忍的。但是纵然有了这类限定,本书仍然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利用它所提供的某些解释方式,就可以更加不受拘束、也更加富有成效地来利用原著。一句话,一个理论体系的纲要和它某些主要创造者的贡献,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专业群体的公共财产,而不是一小群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学者——他们极可能是相互竞争的不同团体——所能独占的。 假如说,《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发展起来的基本理论纲要大体上是健全的,它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提炼过程,它的意义要从一个更好的视角来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就得谈谈立足于它的发展所应具有的性质和方向。 我们强调过,这一体系是在与经验兴趣和那些著作家所提出的问题的直接关联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实情,而且这一实情有着头等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我们才可以说,这一经验取向在此阶段接近了“操作上具体化(operationally specific)”的层面。这其中最著名的例证之一(尽管还很粗糙),就是涂尔干对自杀率的分析。在全然不同的层面上的另一个例证,就是韦伯通过对于一系列不同社会中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而对宗教观念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的尝试。但就总体而言,在经验问题上总的做法还是一种宽泛的“澄清问题”,驱除混乱和站不住脚的解释,开启各种新的可能性。 因此,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尤其在使用了技术上更加精致的观察工具以及对于观察数据的整理和经验分析之时,如何使得这种理论更加接近于有可能为专门研究提供指导,对专门研究进行检验,并使之得到提升。 至少在很多地方,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一系列重要步骤,似乎也因为在理论层面上的一个转移——由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本身的分析,转向对于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而成为可能。这些“说到底”,当然就是社会行动的诸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s)”来进行研究。这反过来,又使得将具体的和可以处理的行动过程孤立出来进行深度的动态研究成为可能。这样一些过程,要作为与制度化角色相关联的行动来进行研究。对它们的研究,要依据他们在符合与偏离社会所裁可的角色界定的预期(expectations of the socially sanctioned role definitions)之间所取得的平衡,要依据施之于个人身上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角色预期,以及在这样的平衡和冲突中的各种动力和机制的汇集。 在结构—功能理论体系的框架内,要将这些问题孤立出来,达到可以在经验上加以处理的地步,这可以在一个能够获得一般化动态分析所具备的种种好处的相对较高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将动态问题置于它们与体系结构的关系中、以及过程与要将其维持下去所必需的功能性前提之间的关系中来加以研究,这就为判断一桩发现的一般意义、以及系统地弄清它与其他问题和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在社会学以及与其最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尤其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领域中,最有希望的理论发展的路线看来是双重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是对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包括相关的动力问题及其与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加工和提炼。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动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它的各个方面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有着直接的实质性重要意义。这样,主要的理论任务,就不止是对于目前重印的这本书的概念体系进行提炼,而是蕴涵着要转变和过渡到一个不同的层面和理论系统化的焦点。对于这个焦点及其相关问题的更加充分的论述,见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学疗法论集》(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rapy, The Free Press, 1949),第一、二章。 第二个主要的方向,是就理论上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发展做专门的操作性的表述,并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经验研究方面技巧的发展,在较近一段时期以来发展异常迅猛,在将来更会是这样。这些技巧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纵然对它们的使用进行指导的理论不过就是常识。但是这对于它们所允诺的、如果它们能够被整合到一个专门的一般化的理论体系中就能具有的理解力来说,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正是沿着这些方向的发展能够取得累累硕果的期望,促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全盘的修订。实际上,这样的修订看来并非真的必要。自从本书初版以来,作者本人所能够取得的理论进展,都已经坚实地奠定在它的基础之上,当然,这是以研究本书分析了他们的著作的那些伟大理论家而获得的见解为起点的。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不会仅仅是我自己的癖好。这些贡献的进一步传布,即使是以它们目前的形式,也会帮助人们提高理论理解力的一般水准,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更加称职,并激发其他参与者发展起社会科学理论进步的最富成果的路线,使之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实现世纪之交他们的伟大先驱者们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宏愿。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49年3月 平装本序言 对于一个运气颇佳、在他的著作初版后还活了这么长时间的作者来说,平装本能够在初版之后三十年印行,可以说令他心满意足了。自由出版社的决定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并非全然无关,这可以由1966年只卖出了1200本精装本的事实得到说明。那只是原先麦克格罗—希尔出版社的版本所售数量的大约八成,而那一版本只在大约十年后就已售罄。 当然,销量的上升,部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巨大增长,这其中,包含了对于社会科学书籍的需求的巨大增长。这本书的“余留价值”在众多的评论看来,难以归结为它具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文采,或者说它是把一些名声卓著的欧洲著作家的论著通俗化了——而有很多人是希望不必投入太多的智力上的努力,就能对他们有多一点了解。 因而,或许可以有一个较为公平的推论,那就是此书之所以能够留存至今,是有其实质性的依据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用人们所熟稔的“知识社会学”来部分地加以解释。随着社会科学的普遍上升,社会学在现代知识共同体中,变成了相对“时尚”的学科。然而,它理所当然地是追随着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才达到它目前的显赫地位的。正如尼斯比特最近所表明的,它的上升与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的新的关注有着莫大的关联——而那种关注在十九世纪和本世纪早期的经济和政治思想中,却是引人注目地付诸阙如的。由于致力于研究世纪之交那一代人中关注这些问题的一些鼎鼎有名的著作家——尤其是涂尔干和韦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或许有助于向范围狭小的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和为数不多的其他知识分子,引介对于该领域内某些问题的分析。本书当然有益于此种关注的持续增长。换言之,社会学的发展,不仅仅与其躬行者的贡献的纯粹科学价值相关,而且也与所处时代更加浩大的思想潮流相关,而那一潮流部分地“在存在上(existentially)”是被决定的。情况既是如此,作者显然就是在一桩“好事”的相对较早的阶段“赶上了趟”,因而有了成功的好运。 对于本书的命运而言,重要的是它从经验上研究了现代工业社会性质的某些最为广泛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而且,此项研究的开展,适逢俄国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等等事件和现象,提出了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就理论方面来说,此书集中讨论了经济学理论的边界和限度的问题。它讨论这一问题,既不是以“经济个人主义”的既定路线的方式,也不是以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方式——甚至于不是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了。此书比较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取向也许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许多知识分子觉得自己陷入了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的两难困境,而经济学在当时似乎是最为重要的理论性社会科学。 近些年来情况好像不再是这样,至少程度不同了。经济学理论在这个时期更加专门化了,在经济学家对他们的专门理论和对经济政策事务的特殊关注的兴趣,与他们对于别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兴趣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裂隙。只是在近来,通过各个学科在涉及到所谓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上的携手合作——在这些问题上,甚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方面,也要勉为其难地才能在分析性理论的意义上被作为纯粹的经济问题来加以研究——这两种兴趣之间具有的某种新的密切关联才得到恢复。 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些实质性的考虑——这些考虑既有经验层面的,又有理论层面的,它们都多少超出了那种被以比较愚笨的方式来理解的意识形态之外——对于本书之具有余留价值而言起了一些作用,那么,就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本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美国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都有一种想要与严格科学看齐的强烈愿望。这种趋向往往走得很远,以至于产生出科学哲学上相当极端的经验主义观点,实际上把所有理论都贬低为是“软心肠”的结果。这种倾向是美国各门行为科学的文化所独有的;确确实实,人们还能够听到,关于最纯粹不过的经验主义(特别是那种量化的经验主义)的优长之处和对于理论思辨(特别是如果会创造出什么“宏大理论”来的话)所带来的危险的喧哗之声。 我一直认为,《社会行动的结构》在双重意义上乃是经验性的研究。首先,它关注于西方社会人所共见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从此书所讨论的四位主要理论家的角度来看的那些问题。其次,它在对于社会思想的分析方面乃是一项经验性的研究。它所研究的著述就像中世纪采邑法庭上的名册一样,乃是提出了需要我们去理解和阐释的问题的文献档案。涂尔干《劳动分工论》中的某一个阐释是否可被证明为合理,就如同涂尔干关于新教与高自杀率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是否正确一样,都同样是经验性的问题。 无论如何,《社会行动的结构》本身乃是、而且也一直旨在成为一本理论性著作。此书的撰写得力于与对于严格科学所独具的长处的顽固坚持——尤其是或许在对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Bridgmans operationalism)更为通俗的解说中所表达的那种——正相反对的、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复杂的运动。在我看来,这一捍卫理论的运动的主要先知乃是怀特海(A. N. Whitehead),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一直是一个对此无比重要的阐述。这背后则是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的著作《理性与自然》。更加直接的影响,则来自L. J.亨德森(L. J. Henderson,他本人是一个作为严格科学家而言,具有良好背景的生理学家)关于一般而言理论的重要性和特殊而言体系概念的重要性的著作——这后一方面在他看来,乃是柏拉图最为重要的一项理论贡献。 正如此书中所说,我还受到了反对心理学中行为主义运动的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两种运动——格式塔心理学和托尔曼(E. C. Tolman)的“目的性(purposive)”行为主义——的影响。最后,柯南特(James B. Conant)在科学普及的一般领域中的著述,也鼓励了我。柯南特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观点认为,对于某一门科学的推进过程的最佳衡量标准,乃是“经验主义程度的减低(reduction in the degree of empiricism)”。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的研究(这些研究以种种复杂的方式与其他许多人的研究相联系)所表述的,并非径直就是有关人类社会的四种特别的观察和理论,而是在理论思维结构上的一个主要的运动。与功利主义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根本传统的背景相反对,这一运动代表了关于人与社会问题的欧洲——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回过头去看,这种对于思想史的阐释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它低估了特殊的法国传统的独立意义,以及法国传统中“自由派”(卢梭、圣西门和孔德)和保守派(博纳尔【Bonald】)、梅斯特【De Maistre】以及[并非最不要紧的]托克维尔)思想观念的复杂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将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以最为宽泛的方式推向一个新的轨道,由此出现的提纲要领显然就会是“宏大的理论”。从英语民族、尤其是功利主义的角度,我个人的经历就能表明它的新颖性。1924—1925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研习社会学,在我记忆中,我那时从未听说过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尽管他所有最重要的著作在那时均已发表。当然,涂尔干在英国和美国都已知名,但对他的讨论是一面倒的贬低;他被认为是“神智不清的群体精神” 理论的传道人。在一定范围内,我想我们可以说,这种“宏大的理论”的视野,最为重要的是它对年轻人(尤其是研究生)而言,有着某种感染力,尽管它逐渐广泛地传播开来了。 然而,有关“宏大理论”的得失之争并没有平息下来的迹象。1948年美国社会学会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开始提出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上的计划。《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ci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第146—148页;又见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第二、三章。回过头看,这似乎是一个要将专注于经验研究者与更加注重理论者整合起来所必需的一个极具建设性的动议。然而,这一评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抛弃在一般理论领域继续工作的研究计划。相反地,在相当漫长的生涯之中,我持之以恒地致力于这样一种研究计划。 我致力于此,是以我认定当时的通行见解——特别是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理论》(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注意,“理论”是复数)中所表达的那种——令人无法接受为起点的。索罗金认为,我所研究的三位社会学家——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分属于迥然相异的学派,而马歇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属于一个更加不同的思想领域。我不把他们的研究视为四种互不相关、相互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理论,而是认为它们属于一个理论思维的融贯整体,是以那一时期思想史中的主要运动来加以理解的。 这种双重的关切——一方面是作为一种分析图式的经济学理论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阐释——带来了成果丰硕的共同涵义,也即,每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图式,必定构成为一个更加庞大的、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工具(theoretical organon)的一个部分。因此,马歇尔——他那代人中最为杰出的经济学理论家——就必定具有一套如果不是明言的、也是暗含的社会学。帕雷托显然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他提供了一座最有用的桥梁。韦伯作为对于“资本主义”有着深厚兴趣的德国风格的“历史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纳入其中。最后,在完成了对涂尔干“群体精神”理论的讨论之后,我由于把握了这一事实——他的出发点(至少就某一主要方面而言)在于他对于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即劳动分工的批判(因而他也就使其相对化了)——而开始真正地理解了他。 我并不想在这里再重复一番本书的理论观点。我是想要使人们注意到我以下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我不是想要提纲挈领地表述社会学理论四个学派的领军人物的著述内容,而是想要证明,在他们的著述中出现了一个单一的、基本上自成一体的(如果说还有些零碎的话)理论运动。这就使得我有必要独立地构建出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结构,以证明该思想运动的统一性。构成本书框架的关于“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一般理论——以及为其正名所作出的努力——并不单单是那四位理论家著述的一个“提要”而已。它乃是一项独立的理论贡献,虽然尚不完备、缺陷不少,但绝非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是“第二手的”。我以为,本书之所以还具有余留价值,是与此分不开的。 然而,还有着更进一步的重要含义。这样一种情形——任何这种起初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表述出来的一般化理论体系,被证明是或者号称是最终定案——是最不可能出现的,而且一旦出现也是最自相矛盾的。如果它不想被别人只看做是表明所论述材料之内容的陈列表,它就得经历一个自身内在发展和变化的持续不断的过程。我想,我有足够的理由宣称,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持续不断地发生了,而且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将要完结的迹象;实际上,它肯定会在笔者自身不再涉足其中之后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将《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出版以来三十年里的这一发展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或许不无裨益。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结构—功能(structuralfunctional)”理论的阶段。这一阶段最充分地体现于两本著作——《一般行动理论试探》(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与希尔斯等人合著)和《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 两书均出版于1951年)——之中。这些著作完成了在体系概念中从来自经济学和物理学的(经由亨德森、帕雷托和熊彼特)一种模式的主导地位,向主要来自生物学、其次来自人类学(尤其是在坎农【W. B. Cannon】的著作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对涂尔干的解释中)的另一种模式的主导地位的重点转移。就狭义上的“行动”概念而言,这种理论更大程度上是涂尔干式的,而不是韦伯式的,因此这就使得马丁戴尔(Martindale)断定我放弃了全部的韦伯立场,这显然与实情不符。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它致力于与两门关键性的紧邻的学科——也即与人格理论特别相关的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和谐共处。首先,这导致了对于弗洛伊德著述涵义的严肃思考,这在1949年《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二版(自由出版社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到过。在理解作为人格之一部分的文化规范和社会客体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时,我赋予了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的殊途同归以极大的重要性。此种殊途同归的发展在较轻的意义上延伸到了韦伯,而对于美国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米德(G. H. Mead)而言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次,我开始强调后期涂尔干(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期的涂尔干)与整合的社会—文化体系理论(theory of an integrated sociocultural system)的关联,因为这一点是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或许尤其是伊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佛特斯(Fortes)和格鲁克曼(Gluckman)所强调的。我与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以及(多少离得更远些)弗思(Raymond Firth)——我在伦敦求学时的老伙伴,在这些问题上达到了某种既部分一致又部分分歧的“辩证”关系。 这一时期还有另一条主线,只是部分地与社会学同社会人类学以及人格心理学的整合有关。这就引向了一条走出旧有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的两难困境——它主宰了关于现代社会的思想——的道路。这条主线关注各种职业现象、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以及它们与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在其他别的兴趣之外,它还为模式—变量图式(patternvariable scheme)提供了温床,而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这一图式仅仅有了萌芽。它还是使得对于经济理论的地位问题提出新的攻击得以可能的那种观点的源泉;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社会行动的结构》之后一般理论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是由以上所提及的那本《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与斯麦尔塞合著,1956)发端的。这背后是《行动理论研究报告》(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与贝尔斯【R. F. Bales】等人合著),此书极大地修正了模式—变量图式。《经济与社会》(其原本是我1953年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主要内容)由帕雷托这一观点出发:经济学理论是抽象的,并且部分地与一种关于社会体系整体的理论相关。然而,此书进一步表明,经济乃是一个社会中可以清楚准确地加以界定的次级体系(subsystem),是与其他次级体系系统关联着的。这一分析的关键,是要将“四功能范式(fourfunction paradigm)”应用于关于生产要素和相应的收入份额(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息、组织利润)的旧有的经济学概念。 这种把经济视为一个社会次级体系的看法,已证明是可以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首先,此种一般化开启了一种对“政治(polity)”进行理论分析的新方法,将其视为与经济严格平行的、在分析上界定明确的一个社会的次级体系。这就消除了有关社会体系的一般理论中所存在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那种极为严重的不对称情形。这些发展与对于社会互动中的一般化中介的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以货币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而扩展到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的范围。而这种扩展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提升对于另外两种主要的社会的功能性次级体系——整合的(近来被称为“社会的共同体”)和模式—维系的(patternmaintenance)——的分析研究。恰恰就是在建立起这些发展框架的背景中,《经济与社会》不仅仅是《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关于经济理论与社会学理论关系的讨论的重述,而是代表着一个新层次的起点。 认为我的理论研究在其“结构—功能”的阶段未能恰当地说明政治结构和过程,这可能是一个颇有道理的批评,尽管我希望刚才所扼要说明的那些发展能够多少缓和这种批评。对于这一阶段关于社会及其相关的文化和心理体系中的变化的说明,也可以提出合情合理的反对意见。我的“后—结构(postStructure)”的理论发展的第三个主要阶段,集中考虑了这些问题领域。其特点是返回到了有别于涂尔干的韦伯式的兴趣上来,因为韦伯毫无疑问乃是后线型社会进化论者(postlinear social evolutionists)中最重要的一位。在最早在《经济与社会》中成型、尔后又由斯麦尔塞在他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大大发展了的那些方面,不仅出现了一个相当一般性的进化图式,而且还出现了一种范式,用来分析极为具体的模式化的变迁过程。这种范式主要与分化、包容、上升和价值一般化(valuegeneralization)的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相关。几篇论文和两本小书——一本已经出版,一本已接近完成——记录了这一发展阶段。 《社会行动的结构》首要地并不是想要成为一项思想史的研究。我给它选择的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时间段,并且,除了作为背景之外,没有提及此前的贡献。回过头去看,在相关的思想发展的广阔范围里,似乎有两位在我的书中不大受重视的人物,在当今的思想舞台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两位人物都属于比我的四位主人公那一代人更早的阶段;他们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尤其是着眼于作为社会体系关键类型的社会来看,对我而言,涂尔干和韦伯乃是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这两人都公然反叛了经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鉴于彻底科层制的“理性化”的前景,大概韦伯更首要地是对后者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的立场,构成了不同的两翼。马克思传播了这样的福音:可以通过理性化在社会主义中的完成,来超越片面的“资本主义”理性化形式的局限性。正如尼斯比特(前引书)所指出的,这是把启蒙运动的教义推向了一个彻底的结论。而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则代表了对于Ancien Regime[旧制度]的满怀忧虑的乡愁,以及对于它的消逝所带来的损失将无从弥补的恐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托克维尔乃是一个完全贵族化的社会的辩护士。 这两位著作家在当前的讨论中变得非常重要,他们乃是《社会行动的结构》所研究的那代人的前驱,并没有得到相当层次上的专业性的理论分析。对于托克维尔的贡献的恰当描述,似乎更应该是洞见卓识而非理论上的准确严密。马克思专门的经济理论现在必须看做是大体上要被取代的了,尤其是被像马歇尔和凯恩斯这样的人所取代。他的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往少里说,也需要根据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发展来加以修正。 因而,我仍旧坚持这样的立场:考虑到欧洲的和宏观社会学的背景,我所作出的包含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目录中的选择,事实上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发展线索而言还是恰当的。尽管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确很重要,但他们的影响看来仍然属于两翼而非核心。我希望可以说,前面所概述过的我自己在一般理论上的工作,从这一核心所包含的潜能中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些进展足够宽宏广大,不至于因为我积极的偏好和消极的偏见而过于剧烈地扭曲了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种种可能性。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68年1月 编 后 记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即有出版社致力于出版此书的中文本。但由于各种原因,中文本的翻译出版却颇费周折,由张明德、夏翼南两位先生翻译并经相关学者校订的译稿,竟经历了近十年的辗转。鉴于此书重大的学术价值,以及原有译稿的实际情况,特约请彭刚先生对原译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彭刚先生历时数年,做了大量订正、补漏、改译的工作,并新译出了该书三个序言,编制了全书索引,使译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提高。这里我们要向三位译者和所有参与此书译事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帕森斯此书篇幅庞大,学理繁复深邃,涉及到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帕森斯的文字又是以晦涩难懂著称(英语学界也经常有人抱怨说,帕森斯有的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虽然翻译工作的几位参与者都付出了辛勤劳动,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译本中一定还有错谬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指正,以使译本质量能够进一步提高。 编 者 2003年12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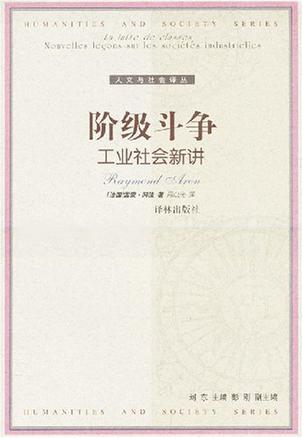
阶级斗争
简介: 雷蒙·阿隆根据当今工业社会的现状,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后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日益模糊,因此工业社会中的斗争主要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前 言 1962年,当我发表《工业社会十八讲》的时候,我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些课事实上是于1955至1956年间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曾由大学文献中心把授课内容用速印机油印出来。直到今天我仍拒绝把讲稿原封不动地出示给更广泛的读者。我把我迟疑的理由立即告诉读者。这些课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研究的机会,是学习的工具,它们启发一种研究方法,勾画出一些概念,提供一些现象和见解。讲义中保留着而且不可能不保留讲课和即席发挥的痕迹。这些课程事先没有撰写成文,因而是口语形式的,难免有缺陷,事后尽管做了修改,以减少其不足之处,但不可能彻底消除。” 《十八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国外多家出版社表示要将它翻译出版,这促使我决定发表这第二册书,然而我仍然要重申关于前面那本书所做的提醒。本书的十九讲是于1956至1957年间在巴黎大学教授的课程。分析阶级斗争是继分析工业社会之后进行的,虽然对阶级斗争的分析本身是自成体系的,但是读者只有把两册书看做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才能充分抓住分析的依据和意义。我对工业社会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曾使一些评论家感到意外的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进行对照的做法,在我看来都将因研究的展开而得到证实。对于工业社会的研究本身不是终结,它应该作为先导,引入另一项研究,即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的对于阶级关系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再导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这将是第三册《民主和极权》的内容。 同时,我很愿意用几句话来回答某些评论家对我的一个指责,应当说他们是出于好意,如米歇尔·科利内和罗贝尔·康泰。为什么我没有把本属于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东西,即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用语,归于他们的名下?如果我意欲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历史性的概述,显而易见,我必然会去参照圣西门主义者或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如同我在其他情况下已经做的那样。然而这不是我在《十八讲》中前四讲所要表述的意图,在那里我仅仅想粗线条地勾勒我打算遵循的方法,同时我也想提出把托克维尔预见的逐渐资产阶级化和马克思预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两者进行比照。关于托克维尔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工业社会(在他所访问的美国当时尚不存在工业社会)的目击者这一点我很难不知晓,尽管米歇尔·科利内煞费苦心让我明白。但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未来社会的见解比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看法要更加正确,本书要证实的正是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坐井观天地看待西方社会,所确认的也是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决定了我选择上一个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并展现他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为的是将它们与本世纪的现实进行比较。 把圣西门主义者阐述的题材与现实加以对照也并非没有好处和教益。我在论述有关战争的主题时正是这样做的,我引证了奥古斯特·孔德。然而当涉及圣西门主义者时,会出现两类困难:如同亨利·古耶在一些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亨利·德·圣西门本人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难以将奥古斯丹·蒂埃里、奥古斯特·孔德、昂方坦和巴扎尔的贡献与圣西门主义割裂,虽然某些人对此故作不知,但任何人都未予以否认。圣西门主义者表达和传播了时兴的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他们的思潮缺乏严谨和系统的形式。托克维尔或马克思分别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我们也许不能对圣西门主义者作出同样的评价。 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能够称得上是我们所生活的技术社会的预言者,如今,在电子机器尚未管理我们这个社会之时,经理阶层管理着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在预示所有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时,却无视我们时代经历大分裂的可能性,这两册书(继而第三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力图客观地来讨论这个主题。托克维尔设想民主社会可能具有两种体制,一种是自由社会,另一种是专制社会。卡尔·马克思则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而分别以这两个阶级所统治的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对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更缺乏判断力。或者至少是这样:假设某一天对事物的管理应该取代对人的统治,那么为使圣西门主义者和崇拜奥古斯特·孔德的人得到安慰,我们也只能说他们的预言还是大大地超前于今天的社会。 讲课距今已有六年多。最近十五年西欧历史发展之迅速令人震惊,使我今天不可能完全像昨天那样来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成果已为世事的演变所证实。但是在某些要点上还需加以补充,在这个前言中,我将只是扼要地予以指出来。 一,工人阶级是越来越走向趋同,还是正相反,即越来越走向分化?分化的原因是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有些是没有任何专业资格的非技术工人,有些是持有专业培训文凭的工人或管理着一架机器的低级技术人员。我认为我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充分的。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没有价值,因为多种多样和互相矛盾的演变是纵横交错的。上一个世纪所有工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失去了他们的重要地位,此外,众多工业部门中的熟练工人似乎销声匿迹而成为毫无特色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被迫从事一项“分割得极细的劳动”。但是这种景象仅代表所有工业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在某些尖端工业部门(石油、电子、电气)中,工业组织类型好像完全不同。从新型工人阶级的情况看,一方面是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更高的消费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这种作用将逐渐窒息上世纪可能存在的工人团体的原始文化和自主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两种简单说法——日益增长的趋同,日益增长的分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现实的复杂性。 二,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使阶级斗争具有政治色彩,换言之,无产阶级要把自身定位于一个旨在全面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些都不再时兴,甚至在共产党保有稳固的常设机构和几百万选民的法国或意大利都如此。在意大利,共产党寻求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并拒绝全盘谴责共同市场。经验甚至使最狂热的思想家都几乎不再坚持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任何改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合适地把工会和政党旨在进行即时的改革(列宁依据英国的范例称之为工联主义)称做实用主义的活动,而把共产党反对现存制度和以革命为目标称做意识形态活动的话,那么,十五年来欧洲经济的发展处处都加强了实用主义趋势,而削弱了意识形态趋势。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冲突从此没有其他目的,仅仅是“利益分享”,那就错了,因为增加工资或抵制技术改造会引起痛苦的转化过程。尽管眼下在大部分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似乎对共同管理的种种方式还有点漠不关心,但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某些国家,以组建企业为目标的请愿将发展起来。在实用主义争论和意识形态冲突之间,人们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论战或斗争,其最终目的可能是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生活,或者加强管理人员或劳动者代表参与某方面的领导。 三,最后,在美国,有四分之三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一部分居民——有人说占20%到25%,另一些人说占15%到20%——的贫困状况没有消失,相对地说,也许绝对地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这种现象在美国比在西欧国家更为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保障的缓慢进程(老年人的贫困)、多种族的并存(黑人、波多黎各人)、悬殊的地区差异(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青年的失业现象等。富足社会中“失败者”的分量不均衡地落到各类社会集团的身上。最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最可能找不到职业。 尽管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不那么突出,目前,欧洲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阶段,但时过境迁,同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在这里显露出来。现代企业技术复杂,要求为数更多的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准。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最缺乏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即使被雇用,他们从工业社会感受到的也只是受奴役而非得益。 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足的社会里,贫困问题甚至赤贫问题正显现出来。这里所指的贫困不是在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下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概念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是贫困问题并不因此就不存在,它恰好提醒那些素来易忘记它的人,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不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建立真正人道主义关系的灵丹妙药。劳动能够创造数量日益增加的财富,使得造成上世纪被人们称为社会问题的依据发生变化。现在更重要蹬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改变对现有财富的分配方法。然而,一味的经济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技术进步都不能担保会带来公正的秩序,更谈不上保证出现符合人类所向往的生活条件,人类为此而改造世界,甚于对自身的改造。 许多读者从《十八讲》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按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讲,这个结论或者由于它极平凡而被认为是明摆的事实,或者被看做是错误的。显而易见,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一本苏联杂志竭力对我进行的辱骂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力求明确指出苏联式经济和西方式经济间对立的真实本质。在双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都相同的情况下,在两种经济模式或增长模式之间,在两种类型的工业社会之间作比较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得出这个推断,无需成为像莫斯科的批评家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说这两种制度具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苏联《文学报》上反驳我的人可以放心——能够贬低两者的区别。即使比政治制度差异更小的经济制度,其区别也足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进行斗争”。斯大林的经济制度和赫鲁晓夫的经济制度都不允许我们要捍卫的政治自由存在。 但愿有一天,这些差异会缩小,两个世界将不仅像今天一样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不互相摧毁,而且意识到它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和平共处即理智地拒绝热核战争,尚未变成思想意识共处,也就是说,尚未承认对方的存在权利,尚未停止宣称自己掌握着惟一和绝对的真理,只要论战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使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法以清除所有不赞同越来越过时思想的人,那么,对于制度进行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将依然是学院式的习作,而不是历史性的对话。但是学院式习作有时已为历史性对话做了准备,也许正在热闹的宣传声中悄悄地成为历史性对话的真正组成部分。 1963年8月于布拉奈 附 录 一些批评家责备我没有整理出《十八讲》中的统计数字。由于课程的本身特点,我对这些责难并不在乎。从任何方面看,课程不是对俄国或美国社会、苏联式或西方式社会的描绘。课程的意向是得出一些基本概念、检验一种分析方法、消除幻想或成见。当前五年计划完成的确切程度、苏联和美国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我们研究最需要的内容,尽管这些事实或这样的比较值得关注。 然而为了满足某些读者的好奇心,另外也是因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在课程中几乎没有指出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附录中提供一些补充信息和最近统计材料是有益的。 1950年到1960年期间,西欧的增长率不仅远远高于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增长率,而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曾经计算出的增长率。法国在1950年到1960年间,生产力人均年增长率在农业中为4.7%,在工业中为4.5%,在服务业中为3.3%。德国和意大利在1949年到1959年间的增长率更高一些:德国的农业和工业都为5.6%,意大利的农业和工业各为5.4%和7.1%。美国相应部门的增长率为3.8%和3.7%,英国为3.9%和2.1%。 1960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3%,如果加权参照法国价格,该比例则为47%。假定国民总产量的增长率是4.7%,到1985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将相当于当前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2%,如果参照欧洲价格加权,该比例为115%。如果五十年代的法国增长率持续不变,而且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稍低于2%的增长率,人们显然可从中得出结论,二三十年以后的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于美国。所有这些计算都建立在一种传统的方法上。人们首先确定劳动力总数,人们接受某个生产增长率,接受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中的一定分配,同时接受按不同收入水平对劳动力最终需求的一定分配。最先进的国家把劳动力的分配及其最终需求量作为参照。这些数值尽管投射出巨大的不确定范围,但意味着从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消费增加2.5倍。因而1985年的年人均消费量以1959年的价格衡量将在9100法郎上下,相当于三口的中等家庭每月2300法郎。工业产量将始终在全部产量中占主要部分,即总产量的三分之二。45%的人口将在服务业工作。 即使西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于美国,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而言,美国继续比旧大陆发展得快,因为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8%,比法国或德国高得多(两者都低于1%)。此外,美国幅员辽阔——这是英国和德国都无可比拟的。 这些数字提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否由于不可能保持或不可能再现的增长原因,五十年代的增长率是例外情况?或者是否这个增长率预示了西方经济真正的质的变化?由于统计和方法的不确定性,不同作者计算出的比率有差距(尤其是人们应该取哪种价格作参照,是最初年份、最终年份还是中间年份的价格?),但无论差距大小,所有作者在大约的数字上意见都一致。从1839年开始算起,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实际价值)年增长率为1.58%,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5%。没有出现人均增长率增加或减少的明显倾向,因为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根据人口增长率必然有增长或减少的倾向。 另一篇由D.C.佩奇、F.T.布莱卡比、S.弗罗因德写的论文(也发表在《工业经济社会研究及资料学会学报》上,第804期,1961年12月1日)按每人每年创造的实际价值(换个说法是一年期间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计算出国民生产的增长率。对长期增长率的计算,日本自1880年起,意大利自1863年起,德国自1853年起,法国自1855年起,美国自1871年起,英国自1857年起,结果如下:日本最高,约为2.9%;英国和意大利最低,约为1.2%;美国以2%的比率位居西方国家之首;德国和法国为1.5%。如果我们想一想计划总署预计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4.7%,我们就会估计出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指望的真正革命。 为什么今天可以设想大大超出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呢?在我看来,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依据如下:意识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曾有利于改变企业主甚至人民群众对劳动和生产力的态度。昨天,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一系列个人行为直接瞄准的目标,有时候几乎对此察觉不到,今天,要达到什么结果,成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目的,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来说都如此。 西欧大陆国家传播现代生产模式,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如农业过去曾经抵制科技革命。在这些国家面前有较先进国家的例子,至少能够大概预测几年期限内主要产品的总量。为保证技术进步,人们耗费巨额资金进行研究,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切地说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总之,十五年以来,西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大大减少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只是表现为加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交替,而非扩展和收缩的交替。这些论点丝毫不打算证明大陆欧洲的经济,特别是法国的经济能够指望4.5%到5%的人均年生产增长率。这样的比率是例外情况,虽然过去已经出现过(1922年到1929年间的法国,1872年到1880年间甚至1871年到1889年间的美国)。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增长率在几十年期间保持不变,还是属于例外。再说它们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保持在4%或5%。5%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11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130倍以上。4%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7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50倍以上。 另外,不仅目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而且目前能源和原料消耗量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我们计算了世界能源需求目前相当于50亿吨煤,到1975年将是90亿吨。按年增长5%算,石油的消耗到2000年将达到75亿吨。 从长远前景看,不存在能源和原料匮乏的问题,或者相反情况,不存在由于科学进步出现能源和原料富足的问题。我们要指出的仅是,生产的发展如同国家财政部门所估计,从此西方经济持续增长,今天欧洲的增长率高于过去按长时期计算的增长率,美国因其长时期增长率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总之,2%的增长率在一个世纪之后可使产值增加7倍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苏联的数字和斯大林去世以来十年的情况。苏联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在1953年到1958年间继续加速,自1958年以来速度明显慢下来。 在1953年到1958年间,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进行了多种改革,规模最大的是取消“拖拉机站”,所有改革都旨在使集体农庄庄员有更多的可能发展生产和上交产品。自1950—1952年至1957—1959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为6%。从那时开始,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这迫使政府于1962年1月1日宣布提高食品价格)。最近这些年农业的失败看来首先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开垦亚洲的处女地和其他一些决定从技术上说都不令人满意)。 最近几年的失败没有抹去斯大林刚去世后那些年获得的发展。与1958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相比,1953年初至1962年初期间,牛的存栏数增加45%,羊的存栏数增加31%,增长速度是巨大的。人均肉类产品41.5公斤,相当于美国的40%左右。相反,两个国家的人均黄油数量应该说可以比拟,苏联1962年人均牛奶291公斤,比美国稍低(约低15%)。相反,如果我们把当前苏联农业的人均收入同1928年进行比较,我们会感到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只是刚刚在消除。还不应该忘记农业收益是在全部劳动力缩减比例近一半的条件下获得的。 至于生活水平,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五年期间发展得很迅速。在1952年到1960年间,生活水平大概提高了将近50%(但起点很低)。1962年由于农业价格的上升和农业生产的停滞状态,生活水平下降了。根据西方的所有统计,苏联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水平,更不必说美国的水平了。 工业发展的速度在最近几年明显减慢,但还是属于快速的。1956年的计划于1957年9月被放弃。代之以七年计划(1959—1965)的出台。但事实上,这最后一个计划也处于半放弃状态,或者至少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在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它将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重工业都比预计的稍稍落后。 不管怎样,国民产值的增长率仍然很高。虽然估算各不一样,但最近十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概在6%—7%。如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这个结果的取得是由于非农职位的大量增加(每年4%—5%),以及净投资的百分比非常高(根据A.伯格森教授的估计,在30%上下)。继承者们肯定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改革,力求使制度“合理化”。但是在最近三年内,回归到越来越集中的倾向取代了原来的分散倾向。虽然苏联的经济学家和领导人承认工业经济的复杂性和投资中的必要选择所提出的新问题,专断而精细的计划经济特点在农业和工业中都没有被消除,甚至没有明显减弱。在总产量,也许在技术质量方面(至少在某些领域),显露出与西方经济的靠拢。今天两种经济制度——诸如收入分配、价格作用、增长因素方面——几乎还是和十年前一样相去甚远。 越来越需要经理或技术专家的苏联仍然由党内人士在统治。官方思想体系继续证明党和国家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泛滥的反常现象已经消失。极端的恐怖形式已成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化是不容置疑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被人们视为独一无二的普遍真理,并且不承认其他学说的存在权利。赫鲁晓夫先生接受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是不接受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 当然,形势不再像过去那样凝固不变。苏联领导人谴责个人崇拜,并不断重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有权拥有某些创作自由,但条件是忠实地遵循党的方针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天平的指针时而倾斜到自由主义一边——关于集中营的报道被发表——,时而倾斜到另一边,赫鲁晓夫先生提醒人们抽象画和十二音体系音乐是西方腐朽艺术,意识形态排斥和平共处。 换个说法,苏联式制度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知识分子有完全的辩论自由,他们将会对根本信条、党和无产阶级的混同、国家正统性、党内人士的至高无上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拒绝给知识分子自由不再可能也不再应该被推进到斯大林式的荒唐地步。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思想统治的稳定性究竟可相容到什么程度?苏联领导人在摸索中寻找答案,与西方和解以及与中国争吵使他们越来越急迫地要解决这个问题。 -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本书对社会学理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象学、社会批判理论及哈贝马斯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流派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进行了详细而精当的分析。它所呈现的各理论流派并不是互不联系的,呈现的方式也不是平铺直叙的个别介绍,而是排列成一个辩证的顺序,有优劣、高下之分,其根据主要是“知识论—科学哲学—方法论”这一轴线。本书是实用主义、哈贝马斯思想、后实证主义、后经验主义和批判理论相结合的代表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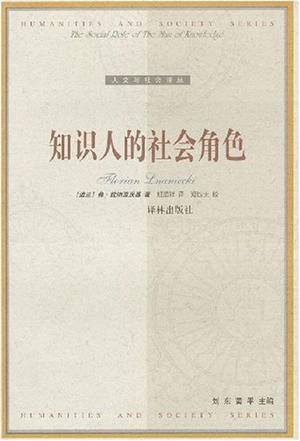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简介: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相媲美的价值。它所播下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本书可能是最具持久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刘易斯·科塞 导读: 一九六八年版导言 刘易斯·A.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之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评论》杂志。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I.托马斯(WilliamI. Thomas)亲密合作。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过余生((有关传说材料与参考书目主要取材于海伦娜·Z.洛帕塔(HelenaZ. Lopata)教授——她是兹纳涅茨基的女儿——为她父亲的遗著《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Roles,San Francisco:Chandler, 1965)所作的序言。))。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一九○九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W.I.托马斯。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出版了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W.I.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5 Vols, Boston: Badger, 1918—1920)。)),即使在美国,这也是第一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New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4.))、《社会行动》((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6.))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在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上尤其令人惊讶。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RalphLinton)最早于一九三六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R.林顿:《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1936)。))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 ((《社会行动》(SocialActions),第11页。))W)〗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humanistic coefficient)。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of the situation)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行动的结构》((New York: Free Press,1949; 第一版,1936年。))得出类似结论之前几乎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作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Dilthey)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传统。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William James)、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杜威(JohnDewey)和库利(Cooley)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二十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早期马克思和杜尔凯姆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对知识社会学史所作的更全面介绍,请参见L.A.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科塞与伯纳德·罗森伯格(BernardRosenberg)著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Macmillan, 1957);和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杜尔凯姆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K.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A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Kerr, 1904),第11—12页。)),马克思提出了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最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事实倒是,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相反,他认为,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不可能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的思想产物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舍勒认为以前的理论建立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也反对这么做,他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杜尔凯姆,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杜尔凯姆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尽管如此,必须认为,杜尔凯姆的著作是此领域中最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作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杜尔凯姆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成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collectiverepresentations),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杜尔凯姆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的不变的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杜尔凯姆断言,社会通过形成逻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分类。第一个逻辑类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让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杜尔凯姆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三十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K.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页。))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论,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属于社会学领域。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正如古代克利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利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之陈述的真理价值。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能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第4页。))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杜尔凯姆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杜尔凯姆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果的开创性研究。而特别想从社会组织的特征中导出象征思想的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象征思考的能力当作所有人类存在物的根本潜能,象征思想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兹纳涅茨基决心为自己强加一个严格的自我否定规范:他准备避开一切涉及认识论问题的引诱。他希望进行严格科学的、实实在在的探究。为了与他的早期方法论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张自己的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上有效的。他相信,研究或否定这些主张的真理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事。“社会学家必须遵守那些个体或群体为他们所共享的知识所制定的有效性标准”。((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5页。))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义”而是主体的“情境定义”赋予研究以活力。无论知识系统被判定为真或假、有效或无效,都与社会学家无关,社会学家只须满足于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兹纳涅茨基雄辩地总结为:“当社会学家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时,他必须同意,对于他们公认为有效的知识,他们才是他唯一必须考虑的权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反对他们的权威:他受绝对朴素这一方法论规则的约束。当他涉及他们接受并运用的知识系统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理论有效性标准”。((同上,第6页。)) 兹纳涅茨基不仅拒斥所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还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纳·斯塔克(Werner Stark)所谓的微观知识社会学(themicrosociology of knowledge)((W.斯塔克:《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也就是说,他不去亲自关心“社会总体知识气氛”或“社会系统的总体历史运动”。((同上,第30页。))他更为谦逊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的中心工具是“社会圈子”(socialcircle)概念,所谓“社会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对其发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兹纳涅茨基指出,至少在异质社会(heterogeneous societies)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特定的社会圈子给予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收益,并帮助已将听众的规范性期待内化在心中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社会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子将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权利和免疫性。知识人预见公众的要求,倾向于从这些现实的怀有期望的公众角度去划定材料与问题。于是,可以依据公众,以及依据社会关系网络所期待的绩效,对思想家进行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分类。在这些角色中,他区分为技术顾问(TechnologicalAdvisors);圣哲(Sages),即那些为群体之集体目标提供意识形态评判的人;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Sacred and Secular Scholars),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Discoverersof Truth)到“知识传播者”(Disseminators of Knowledge),从“组织者”(Systematizers)、贡献者(Contributors)到“真理战士”(Fightersfor Truth);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Creators of Knowledge),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FactFinders)或问题发现者(Discoverersof Problems)。 这决不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分类演练。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于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因此,社会圈子不会期望技术领导者去寻求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可能会使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动之正确性所持有的信念产生动摇。体制期待技术领导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相比之下,知识创造者会由于他发现了新事实而获奖赏。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社会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类型的知识绩效。 兹纳涅茨基这本书为研究对新奇观念的接受与拒斥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默顿就在一篇评论中肯定了这一点。它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于采取某种态度对待经验材料施加压力的方式”。((《美国社会学评论》,第6期(1941),第111—115页。转载于科塞和罗森伯格的《社会学理论》,第351—355页。这里引文取自第353页。))比如圣哲,现存秩序的变革者或辩护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寻求可能动摇现存秩序的新事实。另一方面,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这取决于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最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统完善起来,学派的知识承诺就阻止对新奇的发现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同上,第353—354页。))因此,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neophobia)的结构性来源,兹纳涅茨基允许我们较大地偏离那样一种全盘主张,即主张所有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认创新。附带提一下,如果兹纳涅茨基在今天写成此书(在过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会发现这对于研究嗜新病(neophilia,即片面强调新颖)的互补结构条件同样也是有益的。在某些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他们的公众要求他们不停寻求新的刺激物,以复兴已经疲惫不堪的智力或美学上的嗜好。 兹纳涅茨基不满足于仅仅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他还为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化和取代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学派,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将其成员与竞争对手学派隔离开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一个神学学派失去垄断地位而被迫与其他学派竞争时,它不再依靠未经检验的信仰而是必须发展出合理的劝说模式。相互冲突的信仰系统发出的挑战,对于神学知识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过程作出了贡献,原先由神学学者所占据的领域,逐渐地为世俗学者所接替。怀特海(AlfredNorth Whitehead)曾经指出,观念冲突不是灾难,而是一个机会。兹纳涅茨基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观念的冲突为以知识探索者的开放宇宙取代圣哲之封闭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这几个例子说明,兹纳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创造性地使用于知识生活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life)之中,这足以使本书的读者思考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值得按兹纳涅茨基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这的确是对他的最高奖励;他为未来之完满的知识人社会学(the sociologyof the man of knowledge)提供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利用兹纳涅茨基某些范畴的尝试,见L.A.科塞:《理念的人:社会学家的观点》(Menof Ideas: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兹纳涅茨基异常谦虚,他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