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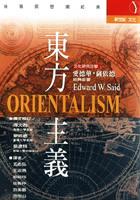
东方主义
後殖民論述 本世紀的最後這十年中,影響美國的社會與人文學科領域最普遍與最深遠的一股思潮,毫無疑問的是「後殖民主義」與其影響。 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立刻引起廣泛的迴響與不同立場的批評爭議,值至今日,已經有日文,德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土耳其文等二十多種譯本相繼出版。 薩依德的論述,其影響力甚至從中東,伊斯蘭世界到非洲,南亞,中南美洲等地。有如股排笑影,成為文化論述的重要著作。後殖民主義思潮的經典,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方向與思考態度。 《東方主義》是一本有關歐美如何看待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兩百年學術傳統的權力與想像的研究。薩依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以及富柯的知識權力論為其論述的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性的網絡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的支配,知識再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係以及煮奴式的霸權體系一一展演於前。 -

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一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这种表述,有长久的历史和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萨达尔此书,正是对这一历史和结构的一种梳理。在梳理东方主义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的同时,萨达尔也梳理了晚近有关东方主义的诸多理论和批评,并讨论了东方主义在当代西方的深化和实践。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西方思想史中俯拾即是的对于东方的诋毁和侮蔑之语,(其中包括了对于东方各种文化形态可笑而偏私的误解:对于中国、印度、伊斯兰等丑化描述)并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和严厉的批评,并认为这些对于东方妖魔化的想像暗示了西方文明缺乏包容性和平等对待其他文化形态的信心。虽然作者引用的许多文字反映了西方人在认识东方的过程中非常荒唐、可笑,甚至是黑暗的一个侧面,其中也确实包含了许多污蔑、偏激的段落,但是,由于本书作者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这些段落是本书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除了对于个别过于露骨、淫秽,或者反对的文字进行删改外,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其原貌的,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部分,应该对于它们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其中将东方妖魔化的内容更应该进行批驳,这也正是本书最重要的目的。 -

领事先生
他是中国百姓的洋大人,还能讲一口四川话。他是军阀们的朋友——或者敌人,他卷入了20世纪初中国大地的历史与阴谋。他是法国领事先生。 本书获1973年联合文学奖。 我丈夫(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他一直牵挂着她,对她有恨,也有爱。这三部小说是他的尝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玛丽-弗朗索瓦丝·勒克莱尔 吕西安·博达尔的自传体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读者,凭借的是对传统中国丰富细致的描写。他行文运墨很容易使人想到浩浩奔泻的黄河。——迪迪埃·塞内卡尔 这本书写的是作家父亲阿尔贝·博达尔在中国四川的往事,它跟《领事之子》、《安娜·玛丽》组成了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带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我的父亲阿尔贝·博达尔在我三岁那年调任法国驻成都领事。当时的成都既是川滇军阀势力斗争的矛盾焦点,又引起了英法两国的殖民利益冲突。围绕着鸦片和军火贸易,一条连接河内到成都的铁路计划在领事先生脑中慢慢成形,于是印度支那总督梅尔兰、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云南军阀唐继尧、法国政治流氓杜蒙纷纷卷入了臆想的阴谋之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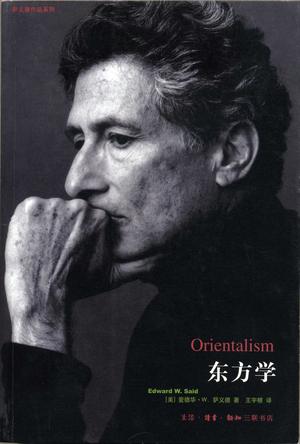
东方学
《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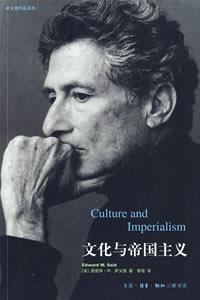
文化与帝国主义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