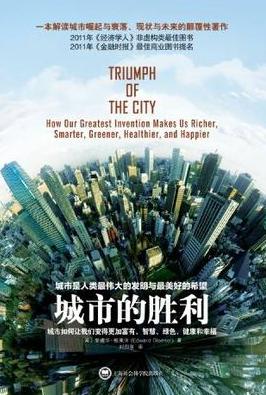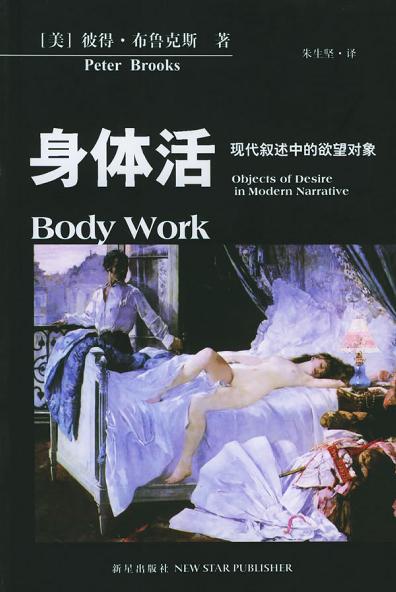读库0803
张立宪
目录:
为其他的百分之九十设计
“90展”部分展品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固执复制
海波与他们
幸运之轮
中国学车记
关庚的生活底稿
那个时代的书装艺术
花花世界且说黑
贱客凯文
佛朗切斯卡:心之形状
医海钩沉
祖逖与刘琨
同居-崔莺莺
“哥斯达黎加时代”
文摘: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申新搁浅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十八岁.二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当时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一个厂、一万二千九百多枚纱锭起步,发展到此时,已拥有九个厂,纱锭总数超过五十五万,还有六万多线锭、五千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六,前后不二十年时间。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九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一亿零二百三十六万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半。
申新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十六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二十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点三三元,市场价却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十四点三三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经济学家马寅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另一原因是税负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的在华厂家。申新被抽去特税达一千五百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则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的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制布匹,这种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所以袋皮向不征税,面粉征税,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在五百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的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赶紧提取存款。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当年,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火灾,荣家从中国银行借款二百多万元。荣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银行求助,还向南京政府建议“庚款借锭”,就是用庚子赔款基金购置外国纱锭借给各纱厂,各厂分期偿还。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六千三百七十五点九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六千八百九十八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一千二百多万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经常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十五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四个厂,福新面粉有八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尽管福新八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虽然从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下来了,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出面担保不可。荣、王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荣、王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因此,他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四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荣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六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八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当时,申新九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儿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万元,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除的。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1922年冬,债务达三百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折合二百二十多万两规银),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而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十一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四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点多。九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五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