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儿们
半夏,男,本姓李,1959年生人。文学硕士,编审。做工、读书、教书,当编辑,至今。在《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文汇读书周报》、《散文》、《书屋》、《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约20万文字。另有《西皮二黄》、《亲爱的小资——关于一个不确定群落的N种不确定描述》、《城市感官》等专题散文集出版。 本书是“天地人和生态文化散文书系”分册,该书就是生态建设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它不仅要以文学为载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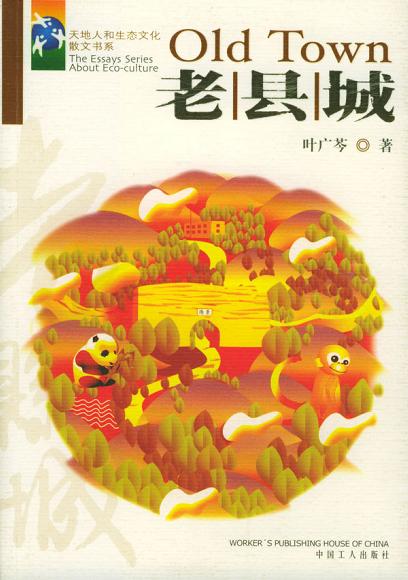
老县城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中学就读于北京女一中,1968年分配到陕西,当护士、记者,1990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95年调入西安市文联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1999年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2000年开始到周县持职任县委副书记,关注生态与动物保护,长期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老县城村。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作家协会副主度,陕西省人大代表,西安市第十、十一届政协委员,主要作品有 -

人参
本卷所收《人参》、《灰猫头鹰》、《太阳的宝库》和《赤裸的春天》四部作品,以普里什文特有的用微笑回应大自然的微笑的风格,反映一个共同的主题:心灵与自然的吻合。 《人参》是普里什文作品中最完美的、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中最富有中国韵味的一部小说,也是俄罗斯文学描写中国人形象最生动、最正确的一部作品。作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俄国士兵我,流落到中俄边境的乌苏里原始森林,在那里遇见一个中国采桑老人卢文,老人身上体现的东方文明让他惊叹不已。两人在森林里一起生活,驯养梅花鹿。最后年老的卢文去世了,另一个梅花鹿化身的女人来到我的身边。于是,他们一同出发寻找那只作为生命之根的人参的经历。人参,是著名的生命之根,是自然神力的代表,象征存在的精神源泉。 《灰猫头鹰》是普里什文的一部译作。讲述一个靠捕猎海狸为生的印第安人,在与他收养的一对海狸孤儿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转变,意识到没有了海狸,自然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此,这只海狸成了主人公的家庭成员,跟着他们夫妇远行,甚至能帮他们干活。 《太阳的宝库》不仅是普里什文战后创作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俄罗斯儿童文学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被收入各种版本的儿童文学选本,还被列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自问世以来,它的总印数已是一个天文数字。 《赤裸的春天》是一部旅行日记。记录了普里什文在自幼就熟悉的俄罗斯腹地对春天最早的萌动所做的细致观察。春天到了,但大地还没有换上绿装,春天因而是赤裸的。这是对春天的最初几行脚印的描绘,更是唱给俄罗斯春天的一曲欢乐颂。这部作品浓郁的抒情氛围和强烈的欢乐精神,是普里什文创作中乐观一面的一次集中体现。 -

大地的眼睛
《大地的眼睛》(1946-1950)由《通向友人的路》、《沉思录》、《人类的镜子》三部分构成,是普里什文最后一部完成的著作,是一部关于他自己的“总结之书”。 《通向友人的路》以传记性质的抒情笔记对影响作者个性形成的重大事件和感受进行了分析。在分析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成长历程时,普里什文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融入自然”,置身森林就像待在朋友中间一样。标题中的“友人”原文为单数名词,可能是普里什文心目中的某个读者,也可能是普里什文自己,思考中的他常常和自己交谈。也可能另有所指,即自然本身,或许还有诗。 《沉思录》主要是普里什文关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和自然现象等的“沉思”,这些沉思具有深刻的思辨色彩,同时又充满着鲜活的感受和生动的细节。 《人类的镜子》最饶有兴味,普里什文把自己写动物和植物的笔记都收录在这部作品中。他称狗、猫、鸟为“老乡”,他总能在动物身上看到人类的影子,能感觉到“动物的智慧”,甚至能观察到“一棵树的生活”。因此,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便成了“人类的镜子”。 普里什文用人生、艺术、道德、历史的观点来诠释真、善、美和爱。他的作品不仅让我们了解大自然,也让人类了解真实的自己。《大地的眼睛》得到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高度评价,帕乌斯托夫斯基称其为“一部充满诗意的思想和意外的瞬间观察的惊人巨著”。 -

鸟儿不惊的地方
普里什文以《鸟儿不惊的地方》和《跟随魔力面包》两部随笔集成为俄国北方自然的文学发现者而进入俄罗斯文坛。 《鸟儿不惊的地方》是普里什文的成名作,也是再现北方原生态生活和文化的第一部艺术品。它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以富有俄罗斯民间文学特色的语言,细致生动地描绘了实地考察中了解到的北方地区的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描述了尚未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妇女、儿童、农民和猎人的淳朴生活以及民俗风情,融合了历史深处凝重而从容的思考。作者因实录的科学性而入选俄国地理学会会员,并获该会授予的银质奖章,被认为是“科学中的艺术学和艺术中的科学家”。 《跟随魔力面包》描写作者跟随具有魔力的小圆面包走向俄国北方,走向一片片人迹罕至、魅力无穷的地方。作品把充满宗教氛围和神秘色彩的索洛维茨地区,北方渔民粗犷、自由的生活,挪威的异国风情,都披上了一层童话色彩。现实的写景、真实的见闻和飘涉的梦境、浪漫的故事相互穿插,共同构成了这部亦幻亦真、虚实结合的作品。高尔基赞扬它“非常出色”,勃洛克说它“当然是诗”,但还有某种超然诗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