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往事
近世以来,西风东渐,冲突碰撞,法治徘徊,中国是个茶几,上面摆满杯具,每个法律人的精神家园都在政治博弈的角斗中飘摇。本书试图拂去遮蔽历史真相的尘埃,以史学之眼光、文学之笔法、法学之思维,研究、访谈、阅读等多般器械轮番上阵,在政法舞台上钩沉往事,呈现一部可思可叹的政法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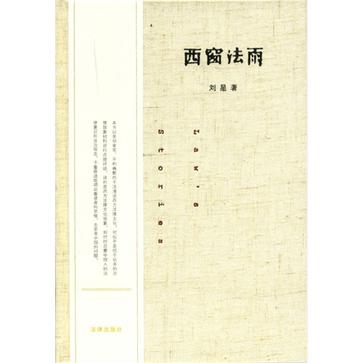
西窗法雨
本书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文章短小、精彩,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领略作者颇为尖端、颇为前沿的研究心得,在这样的论说里,进入法律的智慧天地,享受智慧的乐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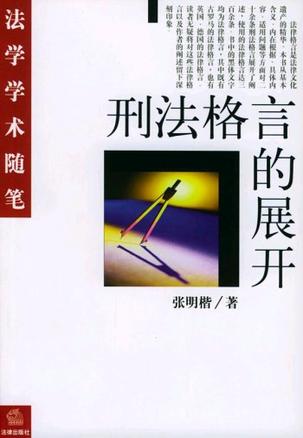
刑法格言的展开
法律格言是法律文化遗产的精华。本书从基本含义、内容在根据、具体内容、适用问题等方面对二十余条刑法格言展开了阐述,使用的法律格言达三百余条。书中的黑体文字均为法律格言,其中既有古罗马的法律格言,也有英国、德国的法律格言。读者无疑将对这些法律格言以及作者的阐述留下深刻印象。 -

西窗法雨
《西窗法雨》(第2版)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 -

新波斯人信札
《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出版于1721年,可算是孟德斯鸠的成名之作。作者在《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中,以书信的形式,借两个波斯人之口,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出色的批判。这两点,也正是我们──《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的几个作者,在讨论中国的法观念问题时竭力想要做到的。有趣的是,孟德斯鸠当年乃是冒了两个波斯贵族的名,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品评法国。二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是借助几位来自巴黎的青年的眼睛,从法观念角度对中国社会作了一番认真的观察。《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所收的十一封信,就是出于“他们”之手。实际上,写《波斯人信札》的是个纯正的法国贵族,而参与《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写作的,却都是地道的普通中国青年。这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孟德斯鸠安排两个波斯人出场,可能有增强戏剧性效果的考虑;但是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要把一些法国人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掩藏着的问题以一种截然对立的鲜明形式提示出来,这,也是《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采用类似写法的考虑之一。总之,把《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定名为《新波斯人信札》,主要是出于上面两种考虑。至于书中讨论的问题,自然颇不相同。因为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完全不同。甚至同为书信体,形式也不尽相同。孟德斯鸠以故事、寓言等方式来述说他的思想,《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则是直截了当地发议论。也许,这会使一些爱看故事的人大失所望,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是为那些愿意探究社会问题,勤于思考,勇于批判的人写的。 其次是关于《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的写作。 《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共收信札十一封,由五位作者分别写成。其中第八封信由石台风撰写,第十一封信由贺卫方撰写,第一至第七封信由我写成。最后,由我对全书润色、加工,并加写每封信前的“引言”。 《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作者多人,行文风格各异,但是,我很高兴地发现,大家的思路非常接近,所成各篇,正好相互补充。出于对各位作者的尊重,我尽可能地保持了原作的风格,但愿这不会造成阅读上的不便。 -

政法笔记
冯象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之一,就是不满所谓的普法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普法”?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言说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言说,其实和司法过程极其相似。法学家写的案子,和法官写的判决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法治”,是西法东渐和“法治本土资源”变迁的经验环节。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官多半写不好判决书,法学家撰文说案更显得尤其重要。 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因为汉语的构造承袭的是三纲五常的微言大义,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像两位领导出场,表面是平列关系,其实多半是一种偏正结构。甚至于有着语义上的越俎代庖。钱钟书《管锥篇》中谈过这个问题,如“兄弟”指的是弟,而“祸福”说的也多半是祸。钱先生说这种词义结构的特征来自道家相对主义对国人的思维影响。这道理固然精辟,但我对这解读还是不满。“偏义”与其说和道家思维有关,不如说恰恰是和儒家礼教一丝不苟的“差序格局”合拍的。因为没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没有语法面前每个字平等的逻辑。 “政法”一词其实也带有偏义,而且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来词。现代法治西学东来,在细微技术上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丝中华法学的遗迹。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谈到法律领域,笼罩全局的仍然是这个老妪般的“政法”二字。 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政治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