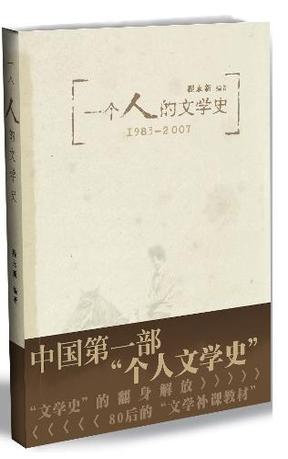到处都在下雪
程永新
程永新也有着和我一样的经历,不懈地探索着小说的写作,同时不断地品尝着小说叙述的美妙和快乐。我想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都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成的,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有着难以言传的亲切之感,我读到了八十年代的思维和情感,八十年代的城市和节奏,甚至是八十年代的气候和尘土,总之一切都是八十年代式的。
能给程永新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写文章是我的幸荣。我是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收获》编辑部最大的那间办公室里,隔壁是一楼层的厕所,当时我正在和肖元敏聊天,程永新从厕所里出来时,我们见面了。在他刚刚编辑的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我的《四月三日事件》,这一期的《收获》是文学探索的专刊,后来被称为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号角。那时的程永新只有二十九岁,其英俊、其潇洒、其谈吐之风趣无人能及,是《收获》编辑部的宋玉,巨鹿路的潘安,外滩的丘比特,黄浦江上空的阿波罗。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在一起下军棋下围棋还要打扑克,熬到天亮熬得头昏眼花,然后将巨鹿路675号四周的小餐馆通通吃遍。十多年自暴自弃的生活之后,如今我们都年过四十,程永新的机智风趣是更胜一筹,他的俊美却正在成为传说。
十多年前我就知道程永新也在写小说,不过他从未拿出来让我读过。我们通宵达旦地下棋打扑克,也曾经通宵达旦地讨论着文学,程永新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对小说的真正理解,他对小说形式的敏感是发自内心的,同时对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和它们之间的衔接也是心领神会,很少有像他这么优秀的文学编辑。
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读完这本小说集时,才知道为何他曾经那么深入透彻地理解和支持我的写作——这是因为他也有着和我一样的经历,不懈地探索着小说的写作,同时不断地品尝着小说叙述的美妙和快乐。
我想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都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成的,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有着难以言传的亲切之感,我读到了八十年代的思维和情感,八十年代的城市和节奏,甚至是八十年代的气候和尘土,总之一切都是八十年代式的。
我在这些作品中了解到程永新当时的写作方向,起码有两个方向是很明确的,一个是在《岸边》这样的作品中,程永新努力通过一个场景来表达人物内心的动荡,一场表姐的婚礼,让一个名叫米林的人百感交集。里面几乎没有故事,全靠叙述的推动来展示,通过婚礼的方方面面来烘托人物的复杂情感。这样的小说是最难写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是这方面的经典。
程永新的另一个写作方向是在《麻将世界》里指出来的,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写作才华,他的叙述轻巧而且妙趣横生,故事引人入胜,人物生动鲜明。他首先写到一个名叫毕森的人,这个人出场时是轰轰烈烈的,他会吹单簧管,他的单簧管“就是在那个夏天里成了召唤一个又一个女友的牧笛”,毕森十分走红,他还嫌不够,还自己张罗着在大学里开了一个音乐讲座,听他讲座的人多得能把礼堂挤破,于是他红得发紫,女友多得让他更加忙不过来。接下去是那个阿克隆正式出场了,这个人出场更是不同凡响,他是以一个毕森的崇拜者出场的。“讲座结束后,人群里有人奇迹般地给站在聚光灯下的毕森抛去一束鲜花。我注意到毕森的眼镜片在全场的掌声中闪着异样的光芒。我们朝讲台上走下来的毕森拥去。毕森高傲的头颅昂扬地晃动着,我相信,那一刻是毕森一生中最最辉煌的时候。一直走到校园里,毕森四周还簇拥着许多人,后来渐渐地只剩下我们这些朋友,像是毕森的贴身卫队一样不离地跟随着他。这时,大家才发现,还有一个人默默地走在毕森的身边。他的手上捧着鲜花,是那束别人抛给毕森的鲜花。”这就是阿克隆的出场,他后来的几次出现都是这样替毕森捡起别人抛过去的鲜花,默默地跟随在毕森的身后。直到毕森成立学校乐队,实在找不到一个会弹钢琴的人时,这个阿克隆才胆战心惊地提议自己来担当演奏钢琴的重任,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结果这个阿克隆竟然弹出了《土耳其进行曲》,而且弹得不错。
接下去是嘈杂的友谊和爱情,杯盘狼藉的生活仍然有理想,当然欲望更是泛滥成灾,里面还有同性恋,程永新始终用暗示的方式在叙述着同性恋。最后的结果也充满了暗示,当然不仅仅是同性恋的暗示了,是整个生活和命运在暗示着什么。
我对程永新后来放弃写作觉得十分可惜,不过生活中可惜的事太多了,也就不用叹息了。我想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我所以一直写作到今天,是因为我出身于拔牙,我要是不写作了,我还得回去拔牙,整天看别人张开的嘴,所以我的写作是义无反顾。程永新是名牌《收获》杂志的名牌编辑,他不写作了还是个名牌。
本书是一个精准而难得的社会记录。这不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褪色,相反,岁月的拂试使它愈加清澈。
这篇小说的叙事显示了作者多方面的才华,而结构的精妙显得尤为突出。驾驭如此复杂的故事线索、如此众多的人物而能圆润无碍,其叙事功力显而易见。这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