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做对了什么
文集是继作者07年《世事胜棋局》和08年《病有所医当问谁》的最新力作,延续了作者的一贯风格,言词犀利、笔法畅快,凝结了作者精深学识和卓然远见,是一部值得从头到尾细细读来再慢慢品味的案头佳作。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2009年的最新文集,其中收录了包括作者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内的25篇文章。全书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30年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针对当前的金融热点问题,第三部分分析了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第五部分针对城乡统筹土地改革的新问题展开了讨论。 简要目录 纪念中国改革30年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30年改革感言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通货与通胀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谨防一错再错 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币值稳定是第一民生 货币的教训——美国次贷危机的思想影响 货币不能松 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 转型的困难 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 向内转型的困难 体制政策要靠前 未来的瓶颈 新形势,新挑战 未来中国经济的挑战与走势 经济新形势下的新起点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为什么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打通城乡土地市场 走城乡兼顾之路 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对成都重庆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一个建议 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城乡协调 成都经验的启示——在成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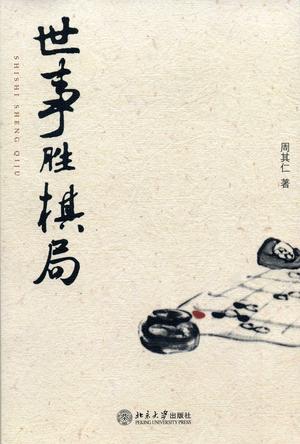
世事胜棋局
《世事胜棋局》是发表于《经济观察报》“挑灯看剑”专栏文章的第二本续集。内容包括经济看大势、国有经济名与实、收入分配是一个问题、话说教育、现象背后有道理、磨砺经济思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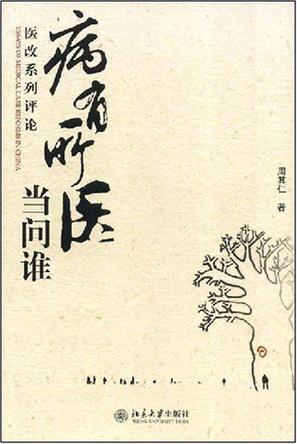
病有所医当问谁
本书收录了周其仁教授近一年多来关于医疗改革问题的全部评论文章,内容包括:宿迁医改、天价医药费的讨论、医疗体制的市场化、医生拿红包的是与非、医疗价格管制、农民缺医少药的根源、社会保障的初衷、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责、中医与西医的分叉等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热点话题。作者保持其一贯的研究风格,注重实地考察,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针对我国医疗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语言通俗、生动,观点犀利、明确,一切对经济问题、医改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均能从中受到启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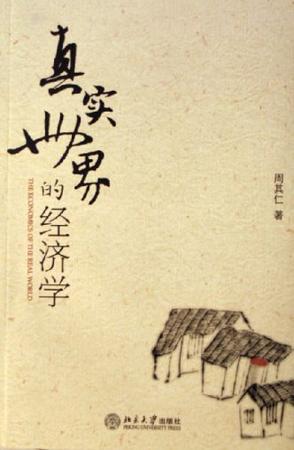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章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回头一看,时间过得很快。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收在“另眼看垄断”栏目下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我参加水工研究的“副产品”。作为一个“电信经济问题专家”我是1998年秋“卷入”电信开放市场的论战的,大部分有关文章已经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数网竞争》一书: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全部来自“I水工”。更一般而论,大凡在所谓“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之上加上了“国家行政垄断”的行为,经济逻辑如出一辙。《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一些文章,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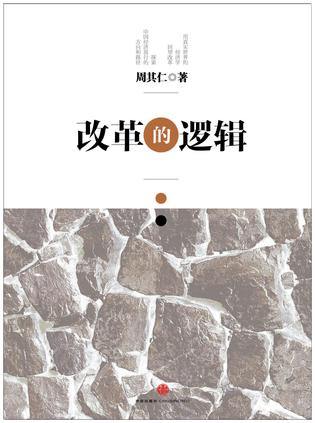
改革的逻辑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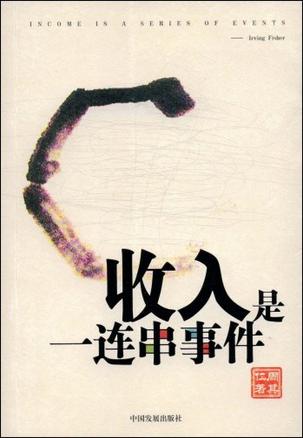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主要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是一连串事件,而以一连患事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增长,正确而又别开生面。二十多年来,数之不尽的漏着,不计其数的波折,使朋友们或什么观察专家认为中国玩完了,走回头路了。我力排众议,从来没有那样看。收入既然是一连串事件,不可能每事件都是好的。果树开花结果子,在过程中这天日晒,那天雨淋,一时蜜蜂传播花粉,一时虫蚁蚕食为祸。这一切都影响植树者的收人,每天的收入或上或落,变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