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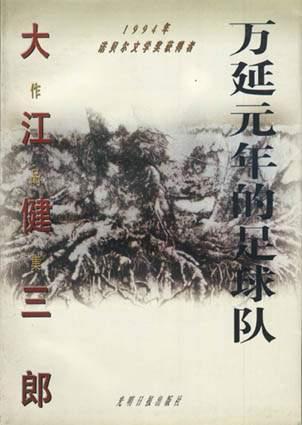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大江健三郎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小说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采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 -

性的人
大江认为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于是他实实在在地耕耘这块荒地。本集通过作为“性的人”青年J的同性恋、性滥交等反社会的行为,来体验人的存在的真实,人性存在的真实。还通过“我们的时代”的靖男在同情人的性快乐与无能的反复中,思考我们的时代日本青年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同时在快感刚萌芽就立即枯萎,但并非由于生理上的因素,而是因为陷入“精神阳痿”的痛苦…… -

政治少年之死
作为1994年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殿堂级作家大江健三郎,十几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首次变成中文的早期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和惊喜。而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两部小说——《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是如何优秀。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暗示的,这些作品散发出一股炙热迷幻的青春气息,那种感觉,就仿佛在夏日午后,做了一个时空回旋,缤纷而惊栗的短梦,骤然梦醒,汗水淋漓心跳如鼓,不知身在何处。 -

两百年的孩子
据介绍,《两百年的孩子》是大江为了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的作品,里面引用了一段二十世纪法国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的话,这段话曾让19岁时在大学教室里的大江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的一生——大江写这部书,就是为了“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 许金龙说,译介大江的作品,很痛苦。更重要的是,大江的作品,绝对不是那种给你带来阅读快感的书。“它的内容,让我面对时觉得痛苦——一个痛苦的世界。当然也有快感,快感就是当我把这个谜解开之后,我会觉得很痛快。诺贝尔演讲时说过,有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说‘我在美丽的日本’,但在大江看来,日本是暧昧的。他展示给读者的,不是川端康成似的美文,他说自己是把人类最肮脏的东西展现给世人。”但每每痛苦过后,许金龙会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他不给人快感,但让人思考。他在对人类负责,很厚重。他的东西,你可以读一个月,也可能读一年,读十年。” 在去演讲的途中,他不停搓手,显得非常焦虑、紧张。有人说:“先生您不必紧张,您面对的都是孩子,都是中学生。”他说:“我不只是面对他们,而是全中国的孩子;不仅面对中国的孩子,也是面对日本的孩子,面对全亚洲的孩子;这是在对未来发表演讲。我希望能够和解,能够和平,而这一切是要理解做基础的,而我是肩负着沟通使命的。”每逢重大活动,大江都很少喝水,免得需要上厕所而不方便。但那天,站在礼堂外的大江主动提出上卫生间,只为“镇定一下”,他在卫生间大约镇定了十来分钟。 《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是大江健三郎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惟一一部幻想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智力障碍的哥哥与健康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人组借助时间旅行器,目睹了日本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进程的各种场面,故事也随之而铺展开来。作者以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二百年来的历史,以及人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灵魂与肉体、物质和精神的状态,既而提出“新人”的思想,指出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以“和解”取得和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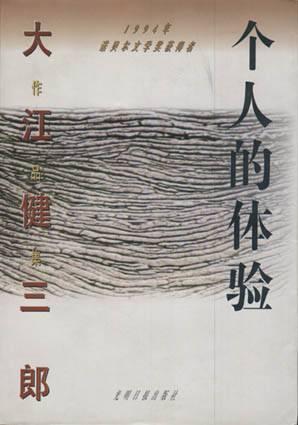
个人的体验
小说主人公鸟的妻子生了个残疾婴儿,使鸟突然间陷入艰难的处境,鸟首先选择了逃避,他把婴儿扔在医院,并设法让其衰弱而死,自己则躲到旧日情人火见子的卧室,陷入爱河欲海之中,火见子是天使又似魔女,她给鸟安慰,使鸟忘忧,也诱使鸟不断堕落,经过漫长的心灵炼狱,最后,鸟终于幡然醒悟,勇敢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决心和残废婴儿共同坚韧地生存下去。 -

定义集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大江健三郎 青春至年迈的思绪沉淀 娓娓道尽大江健三郎眼中的父与子、危机与未来、人与世界、爱与和平 《定义集》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于2012年7月出版的随笔集,原是《朝日新闻》于2004年6月至2012年3月间为大江先生开设的一个专栏,由每月发表的一篇随笔连缀而成的这七十二篇文章,记录了大江先生在这六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乃至越陷越深的绝望,当然,也记录了老作家在这绝望中不断寻找希望的挣扎。较之于鲁迅先生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位老作家似乎更在意“始自于绝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