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地的麦子不死
本书是知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研究张爱玲及“张派”传人文学创作论文的精编本。作者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及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的阐述,对海内外“张派”传人谱系的梳理,对“张派”传人各类创作得失的分析,在本书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全书高屋建瓴、论述精当,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张学”研究著作。 -

十作家批判书
《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事件。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这些充斥于教科书和报刊杂志的显赫名字或人物,毫不夸张的说,是他们亲手把一大堆读者拖进了伪文化的深渊,是他们,正在糟蹋一个民族的方块文字,以及这个民族的想象力。 -

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
相傳遠古時代有一種怪獸名叫「檮杌」。這種怪獸外表怪誕,好鬥不懈,且有預知吉凶的能力。隨著時間流變,檮杌的形象逐漸由怪獸轉為有魔性的惡人。更耐人尋思的是,檮杌也被視為歷史的代稱,擔負「紀惡以為戒」的功能。到了晚明,檮杌又被援引為小說,以其幻魅多變的特質,評述古今、敷衍正邪。檮杌由怪獸、到魔頭、惡人、史書、小說的轉變,是足以說明中國文明對歷史、暴力、敘事想像的一端。有鑑於歷史中的暴力層出不窮,我們必須尋思:歷史是對怪獸也似的暴力的記錄,或者竟是其體現?我們對歷史與怪獸的關聯,是戒慎恐懼,還是視而不見?這些問題到了二十世紀變得更為迫切。因為在一個嚮往啟蒙革命的世紀裡,暴力的怪獸早以更細膩的方式,深入我們生活的肌理間,而我們卻可能居之不疑。環顧此時此地,我們有可能已經成為一種龐大的,以民主進步為名的怪獸的一部分了麼?藉著這一論式,本書觸及歷史與文學間複雜的對話關係,如國家神話的生成,文類秩序與象徵體系的重組,「史學正義」與「詩學正義」的糾結,群體與個體的互動,還有更重要的,現代性(modernity)和怪獸性(monstrosity)的辯證,歷史和「再現歷史」的兩難。 -

被规训的激情
余岱宗大学毕业以后,本来可以选择出国,他的英语不错,而且有其他相应的条件;也可以选择当个小说家,做个浪漫文人,一面编制故事,一面自己也卷入一些曲折的故事。他在大学生时代就写过小说,被当时享有很高权威的全国性刊物《小说选刊》转载过,他后来写的小说,其中有一个中篇,还入选《福建省建国五十年优秀中篇集》(那个选本,一共才选了不到十个中篇)。《福建文学》副主编施晓宇先生在一次会上说,余岱宗是我们省小说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之一。然而命运既是自己设计的,又是由不得自己的。阴差阳错,他教了几年中学语文以后,就考上了我的硕士。 他似乎想在文学研究这个领域里试试身手。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的脸庞就是一个矛盾:白皙的皮肤,应该是江浙一带移民的后裔的表征,而略微深凹的眼睛里有点比鹰隼柔和一点的灵气,又像有几十分之一的阿拉伯人种的血统。脸蛋是英俊的,但常有书生气的呆笑。凭我的直觉,这种才子,在学院里也许是块好料,或者说得文雅一点是块璞玉,当然,玉不琢,不成器,好在他很用功,埋头自我打磨。 然而,他老是想改变活法。硕士毕业以后,他没有选择在学院啃书本。也许是为了再试试他有没有未被发现的、潜在的能量,他去了一家电视台,干了一年。结果是除了有点发胖外,没有多少成就感。他的气质和修养和那样成天撒开脚丫子四处奔波的生活方式,不大能够相容,终于决计回到大学校园里来,重新开始,从助教当起。 这时离他大学毕业已经七八年了。 他的小说还是照样写,而且有了一点影响,省里开什么笔会,请他去作个讲座之类的,还挺叫座,弄得一些小男生、小女生眼睛一愣愣的,不时余老师长、余老师短地引用来争辩。 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似乎并没有放在小说上,他在读硕士的时候,钻研了不少当代西方文论的经典,当助教的时候,开会发言,往往有些让人不得不多想想的高见,这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惊异,事情本来就该如此。但是,有一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童庆炳教授来我们这里,听了他非常简短的发言,居然特别青睐,点名要他去念他的博士。然而他没有去。为什么不去,他笑而不答。对这个奥秘,至今在师兄弟中还有一些哥德巴赫式的猜想,其中一个说法是,他当时正是新婚蜜月后不久。 后来,他顺利地通过考试到我名下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 当代文学。 这个方向,对于他来说,具有双重的优势。第一,他有文学创作的深切体验,对于又学形象的奥妙,他是内行,许多外行(包括拿了博士学位的、只懂得一大堆西方理论的一些人士),要花上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不一定能明白的道理,他早已体会良深了。第二,他对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有相当的涉猎。有一段时期,他几乎言必称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等。一些对于艺术本身相当隔膜的研究生,常常生吞活剥地运用西方大师的话语来掩饰他们在文学感受力方面的空虚。新名词大轰炸,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是文论界的一大顽症。如果不知道他具有长期的创作经验的话,我也许担心他会变成一个令人眼花绦乱的教条主义者。 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可以代表他在学识和智慧方面的水准。 他所研究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当他选择这个题目,意味着向两种倾向发起挑战。一方面是对持传统观念的学者,他们把红色小说神圣化、经典化,以一种宗教的虔诚对之加以膜拜;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激进的批评家,站在今天的立场对之加以挑剔和藐视(2世纪九十年代初甚为流行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某些文章,可能就有这样的倾向)。 比较深遂的理论修养使他站到历史的制高点上,他把当年的文学经典当作一种历史的文本,加以宁静致远的审视。他看到的不是传家的精神珍宝,也不是一堆心灵的垃圾,而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深刻的矛盾、转化和走向反面的过程。他把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灌输)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宏观的、理性的灌输是比较单纯的,而感性的规范要复杂得多。他提出:“革命快感”、“革命激情和革命痛感”,及其“卫生化”。“纯粹化”,必然和文学形象感性发生冲突,这就导致了红色恋情的弹性空间萎缩、革命超人的困境等等。 这一切必然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一方面是革命的感性世界的规范越来越严酷,空间越来越狭窄,(如他指出的“中间人物的‘敌对化”’)一方面为了追求文学感性最大有效性,又不得不反复强调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就决定了进程是曲折的,反复的,痛苦的,艰难的。有时还是充满了血与火的、壮烈的牺牲。但,总的说来,则是轰轰烈烈地朝向英雄的纯粹化,也就是人性。感性的抽象化、样板化的路上前进。 革命感性的规范与建构终于以感性为理性所淹没、消解而告终结。 西方文论的修养给予他在历史和逻辑上高瞻远瞩的宏观魄力,他对于小说艺术的长期创作体验,又使他能在微观上,不时作出原创性的概括。北京大学洪子试教授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称赞他文章中不时有“才气的闪光”,大致就是指的这些东西。 当他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都能够自由发挥的时候文章就显得有气势。 这种气势还得力于,他把红色文本放在比较开阔的历史语境之中。他不像一些研究生那样将红色文本加以孤立地考察,而是把它们放在同样文化体制下的苏联文学加以比较。这就更加有利于他揭示中国红色文本的特色,洞察其革命理性的泛滥和革命感性的虚弱,中国特殊国惰在他笔下就显得格外鲜明了。 对于他这样的年纪的学者来说,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他毕竟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一辈,对于当年的文化氛围、文学气候,直接的感知比较少,大都依靠文献的阅读,由于时间的限制,他的阅读量还不能达到充分还原当年历史氛围的程度,有些章节难免显得薄弱一点,在论及革命小资的恋情的时候,论述口气的明确掩盖不住感性文献基础的薄弱。 好在他对于这个课题相当执着,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又有了新的积累。在这本专著中,我们看到的,已经是经过补充的改写的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一课题不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留下的空间还是相当广阔的。 -

博尔赫斯谈诗论艺
《博尔赫谈诗论艺》是博尔赫斯应美国哈佛大学之邀在该校6次讲学的演讲集。编者米海列司库说:“博尔赫斯跟历代的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引述讨论的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包括荷马史诗、维吉尔、《贝奥武甫》、冰岛诗集《天方夜谭》、《可兰经》以及《圣经》、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洗涤剂 慈、海涅、爱伦·坡、史蒂文森、惠特曼、乔伊斯,当然还有他自己。”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广征博引,涉及从古至今许多文章现象、具有真知灼见的文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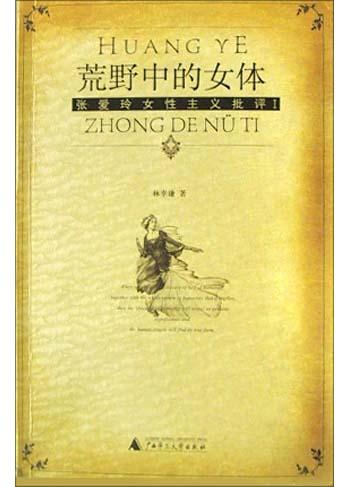
荒野中的女体
张爱玲作品的魅力在于:不时折射这位民国女子临水照花的又一面貌。林幸谦教授重读张爱玲,以女性论述为基础,旁及心理分析、身体诗学和政治、文化批判。全书自张爱玲少时的作品始,重要作品无不触及。尤其在解析张爱玲创作策略及叙述立场之余,还反思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本文性别论述间的互动与对话。立论尖新,实为难得的文学批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