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南水北
韩少功归隐乡野后创作的首部,跨文体长卷散文,记录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入体察,一部亲历者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韩少功的“寻根”与回乡,他二十几年来的写作和生活,演绎着中国人在城乡之间的焦虑和选择,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 -

一个人的村庄
《一个人的村庄》讲述了刘亮程是真正的作家,也是真正的农民,是真正的农民作家。作为农民,写作真正是他业余的事情;而作为作家,他却无时不在创作,即使在他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闲逛的时候。在文章里,刘亮程是一个农民,但是作为农民的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呢——或者说,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以作家自许呢?我不知道。我揣测,在他的村庄里,在与他一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村民们的眼里,这个无事扛着铁锨闲逛,到处乱挖,常常不走正道却偏要走无人走过的草丛中的人一定是个难以捉摸、有些古怪的人吧。在他们眼里,这个说不出却总觉着有点不一样的人是不是有点神秘呢?当然,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个人在跟他们一样的劳作之外,还喜欢偷偷观察着村里的人,以及驴,兔,飞鸟,蚂蚁,蚊子,以及风中的野草和落叶,甚至村东头以及村西头的阳光…… -

生命册
《生命册》作者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 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有“我”极力摆脱却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啐语中自宫……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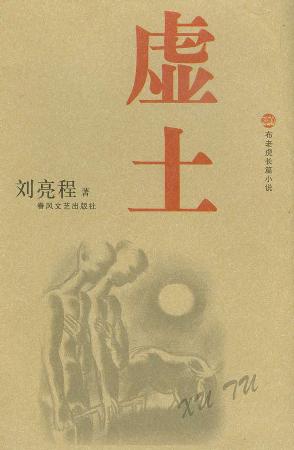
虚土
《虚土》中依旧是一座村庄,建在茫茫的虚土梁上。一个五岁孩子,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出生。或者已经出生却从没有长大。长大的全是别人。全是被别人过掉的生活。被别人做完,废墟一样弃在荒野上的梦。虚土庄的所有事物,都披着一层梦呓般的虚幻色彩,"梦把天空顶高,把大地变得更加辽阔"。生活的方向被一场一场风吹偏,人们在虚土梁上落脚的村庄常常空无一人,人都去了哪里,我自己又去了哪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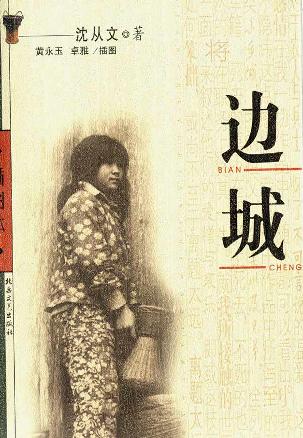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这篇作品如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着眼于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变迁,描摹了湘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生活悲剧,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