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失格
-

離人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太宰治恍惚與不安、希望與悔恨的人生自剖 青春是人生的花朵,同時,也是焦躁、孤獨的地獄。 該如何是好,我不知道。肯定很痛苦。 談何感想! 即便是渾圓的雞蛋,只要換一種切法不也能變成道地的四方形嗎。可以羞赧地垂眼嘟嘴裝可愛,亦可效法剛自原野出現的原始人那種樸素。於我而言,唯一確實的,是自己的肉體。這樣躺著,觀看十指。動一動。右手的食指。動一動。左邊的小指。這根也動一動。這樣凝視半晌後,會覺得:「啊啊,我是真的。」其他的種種一切,皆如絲絲縹緲流雲,甚至是生是死,亦無法分明。 《離人》收錄太宰治隨筆散文和太宰文學作品之精華語錄,全書共有四篇: 〈人生戀文〉為太宰治發表於各報章期刊,關於人生哲學、生活感想、文學見解之隨筆散文。從這些隨筆散文可進一步認識太宰治──相對於絕望、頹廢、墮落之外──理想、善良、試圖扭轉命運、積極向上的另一面。 〈津輕通信〉寫於1946年。太宰治東京家被炸毀,舉家遷移妻子位於甲府市的老家,而娘家隨即也因燒夷彈付之一炬。二度受災,迫不得已帶著妻兒回青森縣津輕老家,投靠大哥。〈津輕通信〉即描述那段期間,太宰治寄人籬下的心情,和與故鄉舊識種種格格不入的無奈。 〈如是我聞〉發表於1948年《新潮》,是太宰治對所謂「文壇大老」宣戰之昭告文。太宰治表明態度,「誰罵我我就罵誰,這場筆戰我奉陪到底。」「我寫出〈如是我聞〉這種拙文,不是因為瘋了,不是因為自大,不是受人吹捧,更不是為了博取人氣。我是認真的。不要輕易下定論說什麼以前人人都那樣做,換言之,不過爾爾。不要自以為是地斷言以前有,所以現在也要步上同樣的命運……」內容辛辣,一反太宰治「氣弱」文風,文章刊出即震驚文壇界。〈如是我聞〉共計四回,最終回在其死後刊出。 〈人生絮語〉為凝縮太宰文學作品精華之箴言集。 -

人間失格 朗読CD付
<内容> 『人間失格』太宰治(装画:梨とりこ/朗読:小野大輔) 繊細で艶やかな作品で読者を魅了する挿絵家・梨とりこのイラストと、涼宮ハルヒシリーズ(古泉一樹)・『黒執事』(セバスチャン)・『黒子のバスケ』(緑間真太郎)などに出演する女性に大人気の小野大輔の朗読で、太宰の自伝であり遺書であった不朽の名作が華麗によみがえる! -

太宰治的人生筆記
我出生時就是人生的高峰。先父是貴族院議員,他用牛奶洗臉。他的兒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需要靠寫文章掙錢。因此我可以理解所羅門王無盡的憂愁以及賤民的骯髒。──太宰治 太宰治的散文精華箴言集 收錄太宰治的重要語錄,集結成人生、文學與太宰治個人的三個面向,是一本適合從文字認識太宰治的精練札記。 太宰治最「不得已」的短篇 太宰治自述是為了創作《晚年》而生,若之後多活了些時間,不得已又再出了短篇集,他將為那本書取名為《歌留多》。 附錄有太宰治年表、關於太宰治及相關紀念場域介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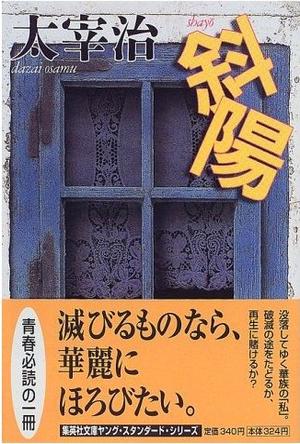
斜陽
内容(「BOOK」データベースより) 敗戦後、元華族の母と離婚した“私”は財産を失い、伊豆の別荘へ行った。最後の貴婦人である母と、復員してきた麻薬中毒の弟・直治、無頼の作家上原、そして新しい恋に生きようとする29歳の私は、没落の途を、滅びるものなら、華麗に滅びたいと進んでいく。戦後の太宰治の代表作品。語註や著名人の「鑑賞」もついて感想文に最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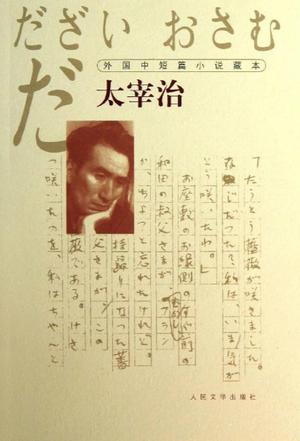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太宰治
编辑推荐 日本“无赖派”文学大师太宰治作品 人文社全新权威译本推出 名人推荐 我很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 ——王家卫 我对太宰治文学所抱有的厌恶情绪是异常强烈的。第一,我讨厌这个人的脸。第二,讨厌这个乡下人“洋气十足”的趣味。第三,讨厌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与自己不适合的角色。一个想和女人‘情死’的小说家,总得多少有点严肃的风貌才行啊! ——三岛由纪夫 虽然三岛由纪夫讨厌太宰治,可我觉得三岛由纪夫的文章本身就很像太宰治的文章。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作品里都有很多警句;有的地方是用警句替代描写。尽管我觉得很滑稽,但是不得不说,三岛由纪夫是用太宰治的文体来写东西的。 ——大江健三郎 媒体推荐 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 ——日本著名评论家 鸟居邦朗 前言 一直想选译代表性的日本“私小说”名家名作。原因很简单,“私小说”在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日本现代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也有一定的关联。这里选译的太宰治的几部重要作品,除《津轻》外,也是颇具代表性的“私小说”名作。 那么,“私小说”当如何定义?根据日本文坛普遍认同的说法,“私小说”最初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不妨说它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变种”。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一个说法,也是日本“私小说”的一个注解——“作为(今日的)作家,既有的观察和预备的笔记,一个牵引一个,再加上人物生活的连锁发展,故事便形成了。故事的结局不过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由此可见,想象在这里所占的地位是多么微小……小说的妙趣不在于新鲜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越是普通一般,便越是具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段,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 自然主义小说是“观察”与“分析”的小说,有趣的是,自然主义文学近乎绝对崇奉的“真实”,恰巧契合了日本“私小说”日后形成的美学标准。 二十世纪初至今百余年,“私小说”的确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曾在其《日本的现代小说》(岩波书店,1968)中断言,日本所有的现代作家或多或少都曾写过“私小说”——晚年的芥川龙之介写过哀切的私小说《点鬼簿》,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精神气质迥然相异于“私小说”样式的作家也曾写过类似的作品,如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椅子》。评论家伊藤信吉说过,明治以来,随着新作家的出现,相继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学性格,其中具有广义文学性格的,惟有生命力强韧且长久的“私小说”。有人将“私小说”定义为“第一人称小说或意识与感觉性经验碎片的重构”;也有人强调“私小说”与日本“日记”传统具有的紧密关联——典型的例证正是“私小说”代表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及阿部昭由“日记”类作品编集而成的代表作。评论家饗庭孝男说,“日记”记录的是现实中切身体味的深刻幻灭,梦幻中深化或提升了生命的生活记录,其根底里浮动着对于生命苦楚或瞬间幻灭的依依不舍。有趣的是,这种日记文学的特点也明显体现在太宰治的《斜阳》等代表作品中。 其实,在日本的“私小说”发展史上曾有一个理论值得一提。即将日本“私小说”样式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趋向或类型。一类是“破灭型(或‘毁灭型’)”,另一类则是“调和型”。前者的主要代表作家是葛西善藏、嘉村矶多和太宰治,后者的主要代表则是志贺直哉。前者的基本特征从词语本身亦可察知——此类作家总是面对种种无法克服的“危机”感,无论面对外在环境还是内在感觉,他们都无法看到任何新生和希望,他们面对的只有哀愁和绝望,“破灭”或“毁灭”是他们每日每时都要面对的必然——他们无以回避的生活方式或结局。相反后者的基本特征则在于,作家或作品中人物未必需要在充满现实或心理“危机”的苦斗中“自我”毁灭,他们有可能达成一种妥协或者和解的状态。 重要的是,属于“破灭型”的太宰治(1909—1948)有共通性也有独自的文学特征。《丑角之花》(1935)、《斜阳》(1947)、《维庸之妻》(1947)和《丧失为人资格》(1948)是太宰治最重要的几部代表作。如所周知,太宰治是“二战”之后日本“无赖派”文学最具特色的作家,除太宰之外尚有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石川淳和伊藤整等。毋宁说,该派作家仅仅在“自我”的否定与毁坏方面,或在自觉地趋向堕落与“破灭性”感觉等方面,具有着些许有限的共同性。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总体上讲,“无赖派”文学与“私小说”本无太多关联或共同性,但从历史的视角反思二十世纪日本“私小说”基本的发展历程,太宰治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特异性存在,他被称做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作家之一。有人将之列为典型的“私小说”代表作家,有人却从根本上否认他是一位“私小说”作家。其实不论怎样讲,太宰文学与“私小说”那种内在精神气质上无以分割的紧密关联是显而易见的。每当读者触及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心理感觉或略呈小家子气的小说作品,似乎便产生一种不大舒服、没完没了、近乎绝对的黏糊糊的晦暗感觉,一种莫名其妙、极端消极的精神气质或美学追求,显然并不仅仅关涉于他的小说形式或表现。太宰治代表性的主要作品刊出于战后,小说中充斥的竟是其战前小说已反复触及和表现的毁灭、负罪、死亡或“丧失为人的资格”。因此,与其说太宰治的战后小说反映了战败后的日本世态或战争之于民众的影响,莫如说太宰治天生的作家气质或精神秉性恰巧契合了战后的世态与文化氛围。 一言以蔽之,太宰治的“毁灭感觉”,早就根植于他特有的、“自我”内在的精神基因中。太宰治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告白形式。这个特征也符合“私小说”形式方面的基本要求。表面上看,《斜阳》等重要作品的基本叙事和心理趋向与葛西善藏等人的小说文体十分相像。但某种人为给定的“差异性”奠定了太宰治特殊的文学史地位。在一般读者的视野中,太宰治煞费苦心地反复营造一种特殊的精神氛围,或竭尽所能地烘托尽量真实的“毁灭”意愿,这种状况在《丧失为人资格》中变得更趋极端,竟连小说题名也有了极度鲜明的意念提示性。为此有人将之称为太宰文学的“集大成”。评论家奥野健男的观点却不同,他说“《丧失为人资格》是太宰治的内在精神性自传。但该作与传统的‘私小说’不同,它没有拘泥于所谓经验事实而是依据‘虚构’的方法表现更趋深层的原初体验。”这里也许存有着一个读者无法在文本中单独发现的核心问题。之前反复触及“私小说”与“私小说”作家经验世界间、某种近乎绝对的“对应关系”,“私小说”一个基本的样式前提在于作家“自我”与作品表现在真实经验层面上最大限度地统一。一般情况下,当然先有经验后有表现,太宰治恰恰在这个方面略有不同。太宰治似乎实现了某种“私小说”样式或文体的革新。但是仅从作品本身其实看不出它与传统“私小说”具有何等区别,只是前提发生了变化,作品一反常态地变成了“第一性”的存在,作家反倒变成了“第二性”的存在。有观点认为,太宰文学中的等式是反向的,不是作品必须等同于作家心理或作家的现实生活,而是作家必须向着作品的完美实现做出现实的“牺牲”。于是在太宰治的文学世界中,为了作品本身的完美实现,小说家需要人为地改变“自我”,而去符合或迎合文学形式或样式上的诸般要求。在此意义上,太宰文学时常具有一种所谓的“演技”性质,太宰治现实生活中的“毁灭意欲”以及一次又一次令人不解而厌倦的、现实与虚构中的情死,或许都是为着实现其独特美学时的一种“演技”或“表演”。这种表演对于太宰治可谓代价沉重。他不断重复一种死亡的游戏,付出的乃是生命的代价。 总之表面上看,太宰治的文学符合传统“私小说”的样式标准。实际上,那却是一种(仿佛是一种)“逆向性”的、人为设定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太宰文学在日本现代文学或日本“私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 魏大海 前言 一直想选译代表性的日本“私小说”名家名作。原因很简单,“私小说”在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日本现代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也有一定的关联。这里选译的太宰治的几部重要作品,除《津轻》外,也是颇具代表性的“私小说”名作。 那么,“私小说”当如何定义?根据日本文坛普遍认同的说法,“私小说”最初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不妨说它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变种”。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一个说法,也是日本“私小说”的一个注解——“作为(今日的)作家,既有的观察和预备的笔记,一个牵引一个,再加上人物生活的连锁发展,故事便形成了。故事的结局不过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由此可见,想象在这里所占的地位是多么微小……小说的妙趣不在于新鲜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越是普通一般,便越是具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段,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 自然主义小说是“观察”与“分析”的小说,有趣的是,自然主义文学近乎绝对崇奉的“真实”,恰巧契合了日本“私小说”日后形成的美学标准。 二十世纪初至今百余年,“私小说”的确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或现象。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曾在其《日本的现代小说》(岩波书店,1968)中断言,日本所有的现代作家或多或少都曾写过“私小说”——晚年的芥川龙之介写过哀切的私小说《点鬼簿》,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精神气质迥然相异于“私小说”样式的作家也曾写过类似的作品,如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椅子》。评论家伊藤信吉说过,明治以来,随着新作家的出现,相继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学性格,其中具有广义文学性格的,惟有生命力强韧且长久的“私小说”。有人将“私小说”定义为“第一人称小说或意识与感觉性经验碎片的重构”;也有人强调“私小说”与日本“日记”传统具有的紧密关联——典型的例证正是“私小说”代表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及阿部昭由“日记”类作品编集而成的代表作。评论家饗庭孝男说,“日记”记录的是现实中切身体味的深刻幻灭,梦幻中深化或提升了生命的生活记录,其根底里浮动着对于生命苦楚或瞬间幻灭的依依不舍。有趣的是,这种日记文学的特点也明显体现在太宰治的《斜阳》等代表作品中。 其实,在日本的“私小说”发展史上曾有一个理论值得一提。即将日本“私小说”样式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趋向或类型。一类是“破灭型(或‘毁灭型’)”,另一类则是“调和型”。前者的主要代表作家是葛西善藏、嘉村矶多和太宰治,后者的主要代表则是志贺直哉。前者的基本特征从词语本身亦可察知——此类作家总是面对种种无法克服的“危机”感,无论面对外在环境还是内在感觉,他们都无法看到任何新生和希望,他们面对的只有哀愁和绝望,“破灭”或“毁灭”是他们每日每时都要面对的必然——他们无以回避的生活方式或结局。相反后者的基本特征则在于,作家或作品中人物未必需要在充满现实或心理“危机”的苦斗中“自我”毁灭,他们有可能达成一种妥协或者和解的状态。 重要的是,属于“破灭型”的太宰治(1909—1948)有共通性也有独自的文学特征。《丑角之花》(1935)、《斜阳》(1947)、《维庸之妻》(1947)和《丧失为人资格》(1948)是太宰治最重要的几部代表作。如所周知,太宰治是“二战”之后日本“无赖派”文学最具特色的作家,除太宰之外尚有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石川淳和伊藤整等。毋宁说,该派作家仅仅在“自我”的否定与毁坏方面,或在自觉地趋向堕落与“破灭性”感觉等方面,具有着些许有限的共同性。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总体上讲,“无赖派”文学与“私小说”本无太多关联或共同性,但从历史的视角反思二十世纪日本“私小说”基本的发展历程,太宰治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特异性存在,他被称做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作家之一。有人将之列为典型的“私小说”代表作家,有人却从根本上否认他是一位“私小说”作家。其实不论怎样讲,太宰文学与“私小说”那种内在精神气质上无以分割的紧密关联是显而易见的。每当读者触及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心理感觉或略呈小家子气的小说作品,似乎便产生一种不大舒服、没完没了、近乎绝对的黏糊糊的晦暗感觉,一种莫名其妙、极端消极的精神气质或美学追求,显然并不仅仅关涉于他的小说形式或表现。太宰治代表性的主要作品刊出于战后,小说中充斥的竟是其战前小说已反复触及和表现的毁灭、负罪、死亡或“丧失为人的资格”。因此,与其说太宰治的战后小说反映了战败后的日本世态或战争之于民众的影响,莫如说太宰治天生的作家气质或精神秉性恰巧契合了战后的世态与文化氛围。 一言以蔽之,太宰治的“毁灭感觉”,早就根植于他特有的、“自我”内在的精神基因中。太宰治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告白形式。这个特征也符合“私小说”形式方面的基本要求。表面上看,《斜阳》等重要作品的基本叙事和心理趋向与葛西善藏等人的小说文体十分相像。但某种人为给定的“差异性”奠定了太宰治特殊的文学史地位。在一般读者的视野中,太宰治煞费苦心地反复营造一种特殊的精神氛围,或竭尽所能地烘托尽量真实的“毁灭”意愿,这种状况在《丧失为人资格》中变得更趋极端,竟连小说题名也有了极度鲜明的意念提示性。为此有人将之称为太宰文学的“集大成”。评论家奥野健男的观点却不同,他说“《丧失为人资格》是太宰治的内在精神性自传。但该作与传统的‘私小说’不同,它没有拘泥于所谓经验事实而是依据‘虚构’的方法表现更趋深层的原初体验。”这里也许存有着一个读者无法在文本中单独发现的核心问题。之前反复触及“私小说”与“私小说”作家经验世界间、某种近乎绝对的“对应关系”,“私小说”一个基本的样式前提在于作家“自我”与作品表现在真实经验层面上最大限度地统一。一般情况下,当然先有经验后有表现,太宰治恰恰在这个方面略有不同。太宰治似乎实现了某种“私小说”样式或文体的革新。但是仅从作品本身其实看不出它与传统“私小说”具有何等区别,只是前提发生了变化,作品一反常态地变成了“第一性”的存在,作家反倒变成了“第二性”的存在。有观点认为,太宰文学中的等式是反向的,不是作品必须等同于作家心理或作家的现实生活,而是作家必须向着作品的完美实现做出现实的“牺牲”。于是在太宰治的文学世界中,为了作品本身的完美实现,小说家需要人为地改变“自我”,而去符合或迎合文学形式或样式上的诸般要求。在此意义上,太宰文学时常具有一种所谓的“演技”性质,太宰治现实生活中的“毁灭意欲”以及一次又一次令人不解而厌倦的、现实与虚构中的情死,或许都是为着实现其独特美学时的一种“演技”或“表演”。这种表演对于太宰治可谓代价沉重。他不断重复一种死亡的游戏,付出的乃是生命的代价。 总之表面上看,太宰治的文学符合传统“私小说”的样式标准。实际上,那却是一种(仿佛是一种)“逆向性”的、人为设定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太宰文学在日本现代文学或日本“私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 魏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