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尔赫斯七席谈
《博尔赫斯七席谈》初版于1973年,全书共七章。是他于70年代初七次采访博尔赫斯的谈话 实录。博尔赫斯在他当时工作的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原在墨西哥大街564号,1992年岁末,迁 至阿古埃罗大街1502号)的一间斗室里,对访者侃侃而谈,阐明了自己的出身与家庭背景、 文学修养与实践、创作活动与文学主张以及对世界文学流派、名家与名著的见解。� 《博尔赫斯七席谈》中博尔赫斯果然不同凡响:学识渊博但虚怀若谷,对文学事业挚爱但近乎天 真,喜欢直抒胸臆、言辞尖锐,但一旦发现出错立即自我批评……� 这本博尔赫斯访谈录,完全是索伦蒂诺与作家七次谈话的实录,没 有丝毫的加工修饰。所以,大师在谈话的时候,有些前后不一,甚至矛盾的地方,也都保存 下来了。索伦蒂诺说,他所要记录的,正是这么一个本色的博尔赫斯。 -

俄罗斯套娃
《俄罗斯套娃》是卡萨雷斯晚年的短篇小说集,首版问世于1991年,包括七则故事,大都和旅行相关,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相信,旅行有助于解放灵魂。这些故事又大都和寻情逐爱相关,却是纯爱故事的反题:恋情罗曼司的女主角本来是不可替换的,但对于孱弱、敏感、不成熟的男性而言,她们 更像是层层嵌套、模样近似的套娃,“打破了一个,其余的还能留下来”。 —————— 博尔赫斯一生挚友 阿根廷幻想文学大师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短篇小说集 —————— 比奥伊•卡萨雷斯是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是句陈词滥调,但陈词滥调常常是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才会一再重复。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小说有魅力,但也有危险的智慧和突然而至的悲伤,只有一个老道的文学家才能传达出这样的效果。 ——约翰•厄普代克 -

名家名译随身典藏
《名家名译随身典藏》共10册,包括《追击》《罪恶下的恋情: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欧拉》《狄金森诗选》《谁是杀人犯?》《南方高速公路》《蓝眼睛》《三角帽》《雪莱诗选》《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均使用同一ISBN。 -

诗艺
身为一位作家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身分对我而言很简单,就是要忠于我的想象。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不愿只是忠于外表的真相,而是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我会写一些故事,而我会写下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不是相不相信历史事件真伪的层次而已,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 诗与语言都不只是沟通的媒介,也可以是一种激情,一种喜悦——当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认为我真的了解这几个字,不过却感受到内心起了一些变化。这不是知识上的变化,而是一个发生在我整个人身上的变化,发生在我这血肉之躯的变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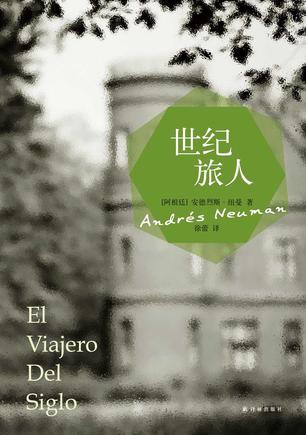
世纪旅人
一位谜一般的旅人。一座迷宫一般,走不出去的城市。 镇上的街道、房舍仿佛不断重组和变貌,他走失在这迷宫之中。 守夜人消失在街角,阴影中探出帽子黑色的檐。高跟鞋急促地穿过小巷,帽檐倾斜,面具套上了脸。 还有爱和文学: 一段值得铭记的爱,引人床笫缠绵,诱人尽情书写; 一道架通 古今的文化拼盘,在幻想世界中浓缩了现代欧洲的种种冲突。 波拉尼奥:“(安德烈斯·纽曼的作品)别具匠心。任何好的读者都能从他的书中有所感悟,那是只有在由真正的诗人书写而成的顶级文学中才能找到的东西。” 斩获2009年西班牙丰泉小说奖,2010年西班牙文学批评奖;入围2013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六人决选名单、2014年IMPAC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安德烈斯·纽曼:《格兰塔 》杂志:“西班牙语最杰出的青年作家” , 2009年柏林国际文学节唯一受邀拉丁美洲作家;小说已被译成14种语言。译成英语后,亦荣登《卫报》、《金融时报》等英国报章选出的年度最佳小说榜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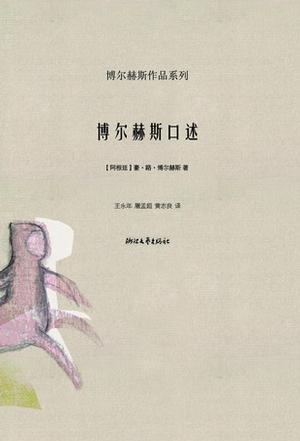
博尔赫斯口述
收入《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博尔赫斯口述》、《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三个博尔赫斯散文集子。 博尔赫斯曾经“冒着犯下时代错误的危险”,虚拟了一个百年之后关于自己的百科词条,极有博尔赫斯风,节选如下: 博尔赫斯,豪尔赫•弗朗西斯科•伊西多罗•路易斯 作家和自修学者,1899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去世日期不详,因为作为当时的文学品类的报纸在当地的历史学家们如今正在评述的那场大战乱期间全部遗失了。他的父亲是心理学教师。他是诺拉•博尔赫斯的哥哥。他爱好文学、哲学和伦理学。在文学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致命的局限。……他喜欢写短篇小说,这一点使我们想起了爱伦•坡在赞赏某些东方国家的诗风时说的那句名言:“没有别的什么更像一首长诗。”……他虽然只是在日内瓦受过正式的中学教育,却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过课。他是卡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有传闻说他在考试中从不提问,只是请学生随意就命题的某个方面发表见解。他不限定日期,总是说他自己就没有日期的概念。他讨厌开列参考书目,认为参考书籍会使学生舍本逐末。 他庆幸自己属于其姓氏所代表着的资产阶级。他觉得平民和贵族全都耽于金钱、赌博、体育运动、民主狂热、追逐功名和争出风头,几乎没有差别。他于1960年前后加入了保守党,因为(他说)“它无疑是唯一不会煽起狂热的政党”。 有一大堆专题和辩论文章断言博尔赫斯一生中享尽荣华,这种名声至今仍然让我们疑惑。我们发现对此最不理解的竟是他本人。他生平就怕人家说他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时至今日,这种说法已经秘不可测,我们将继续探究其中的奥妙。 尤其不应忘记博尔赫斯生活的年代适逢国家处于没落时期。他出自军人家庭,非常怀念先辈们那可歌可泣的人生。他深信勇敢是男人难得能有的品德之一,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信仰却使他崇敬起了下流社会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是通过一个杀人凶手之口讲出来的故事《玫瑰角的汉子》。他为谣曲填词,讴歌同一类的杀人犯。他为某个小诗人写了一篇感人的传记,那人唯一的功绩就是发掘出了妓院里的常用词语。独幕戏剧的作者们早已营造出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博尔赫斯的世界了,但是有教养的人们却不可能胸怀坦荡地欣赏那些节目。他们为那个给了他们这一乐趣的人欢呼叫好是可以理解的。他秘而不宣的而且说不定竟是下意识的苦心则是编造出一个压根儿就未曾存在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话。因此,年复一年,他于不知不觉中而且完全没有料到竟然助长了对残忍暴行的推崇,这种推崇最后演变成了对高乔人、对阿蒂加斯和对罗萨斯的崇拜。 …… 博尔赫斯是否曾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的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 …… (全文收录于“博尔赫斯作品系列”,为“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