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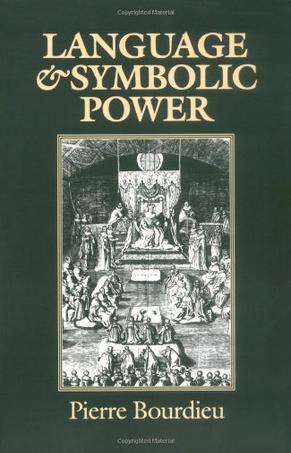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his volume brings together Bourdieu's highly original writings on language and on the relations among language, power, and politics. Bourdieu develops a forceful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including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of Saussure and Chomsky and the theory of speech-acts elaborated by Austin and others. He argues that language should he viewed not only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s a medium of power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display their practical competence. Drawing on the concepts that are part of his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Bourdieu maintains that linguistic utterances or expressions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produc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 linguistic market" and it "linguistic habitus." When individuals use language in particular ways, they deploy their accumulated linguistic resources and implicitly adapt their words to the demands of the social held or market that is their audience. Hence every linguistic interaction, however personal or insignificant it may seem, hears the trace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at it both expresses and helps to reproduce. Bourdieu's account sheds fresh light on the ways in which linguistic usage varies according to considerations such as class and gender. It also opens up a new approach to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in the domain of politics. For politics i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rena in which words are deeds and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power is at stake. This volume, by one of the leading social thinkers in the world today, represent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power. It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specially in sociology, politics,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

言语意味着什么
导 言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真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学术研究成为流行时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即以确立“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为目的,停留在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方法论的“解读”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没有发表)。因此,对于这一具有至高权力的学科所施加的最为可见的支配性影响,我可能比别人更为敏感,无论它是涉及理论著述的文字手稿,还是按照表面意义对概念所作的机械转换,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这种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与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导致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有时是荒谬的再解释——所作的机械转化。但是对时髦品味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注定要认可无知的拒绝:最初是索绪尔的著作,然后是——当我开始接近于察觉到作为执行的话语(和实践)模型的不足之处时——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认识到了生成性倾向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就是包含一些基本问题的社会学。 这一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除非我们超越作为纯理论的结构语言学意图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则这些问题就无法发挥它们全部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语言学场域之外的音韵学模型的改变,对各种象征性产品、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神话系统或者艺术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创过程普遍化的效应,正是这种初创过程通过把语言方式与其生产和运用的社会条件分离开来而使得语言学成为了最自然的社会科学。 不言而喻,不同的社会科学对这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也具有不同的先天容纳倾向。将人类学家与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以及由其外部观察者的地位所赋予的“公正的观众”的中立性,使人类学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当然,还有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一领域,引进一种预设了功能的中性化的分析方法只能是使感知艺术作品的模式变得神圣化,而这种模式总是要求鉴赏家的、即“纯”的和纯粹的“内部”性情倾向,而排除任何对“外部”因素的“还原性”指涉。因此,颇像是另外一个理论分支的祈祷轮 (prayer wheel),文艺符号学把对艺术著作的膜拜抬高到了理性的层次,而同时又没有改变它的功能。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 “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导言 第Ⅰ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1.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2.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1.权威化的语言: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2.制度的仪式 3.认同与表征: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要的元素 4.描述与规定: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1.审查与塑形 2.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3.科学性的修辞: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的论证 注释 译后记 -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本书主要写布尔迪厄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自己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却偏偏经历了学校的体制就在自己脚下崩溃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