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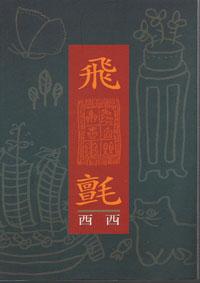
飛氈
書名《飛氈》,嚴格說來,應是《飛毯》。氈與毯,音和義皆有別。 先說氈。何謂氈?我古代製氈,是把羊毛或鳥獸毛洗淨,用開水澆燙,搓揉,使其黏合,然後鋪在硬葦帘、草帘,或木板上,趕壓而成。《說文》之解釋為『捻毛也,或曰捻熟也。蹂也,蹂毛成片,故謂之氈』。《釋名》說:『毛相著旃旃然也』,稱為氈。《考工記》說:『氈之為物,無經無緯,文非織非衽。』 氈並沒有經過紡捻和編織加工的過程,紡織學上稱為無紡織物。它的出現,遠比任何一種毛織毯為早,新疆地區氣候較冷,在原始社會時期,已經廣泛使用。公元前一千年的周王朝,宮廷中已設了『共有其毳皮為氈』,監製氈子的官吏,稱為『掌皮』。 氈是無經無緯壓成之物,如今居室所用的blanket,即毛氈。一般手工用的felt,也是氈之一種。氈音沾。 次說毯。毯也是用羊毛或鳥獸毛製成,卻經編織過程;織法大玫分兩類:一為經緯平紋組織法,一組經線與一組緯線平行交織;相當於如今几桌上月的襯墊物mat,或置於門口地上用之蹭鞋墊rug。二為裁絨法,主要是在一組經線二組緯線織成的平紋基礎組織上,再用絨緯在經緯上拴結小型羊毛扣;即如今一般所稱之地毯,carpet。毯音坦。 《飛氈》一書中所敘述的毛織品,是地毯,為什麼稱為氈呢?《說文》說得好:『氍毹、毾登,皆氈菼之屬,蓋方言也。』小說中的肥土鎮,有自己的方言,對於毛棉絨絲織成的鋪墊物,不管平紋或栽織法,不管是為人取暖、覆蓋、供人欣賞,包裹東西,作為書寫的墊子,以至純為踩踏之用,一律稱之為氈。這不完全是虛構,我生活的地方,一直氈毯不分,都讀成『煎』。所以,小說從俗,名為《飛氈》。至於內文氈、毯並用,則略有分別:分正常敘事,用毯;如由肥土鎮人口中陳說,則用氈。 打開世界地圖,真要找肥土鎮的話,注定徒勞,不過我提議先找出巨龍國。一片海棠葉般大塊陸地,是巨龍國,而在巨龍國南方的邊陲,幾乎看也看不見,一粒比芝麻還小的針點子地,方是肥土鎮。如果把範圍集中放大,只看巨龍國的地圖,肥土鎮就像堂堂大國大門口的一幅蹭鞋氈。那些商旅、行客、從外方來,要上巨龍國去,就在這氈墊上踩踏,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塵。 可是,別看輕這小小的氈墊,長期以來,它保護了許多人的腳,保護了這片土地,它也有自己的光輝歲月,機綠巧合,它竟也飛翔。蹭鞋氈會變成飛氈,豈知飛氈不會變回蹭鞋氈? 這書的寫作,曾由朋友替我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資助通過後半年,忽然產生一些古怪的議論,讓我看清楚了某些人情物事,而這,未嘗不是多年來努力編織這氈的額外收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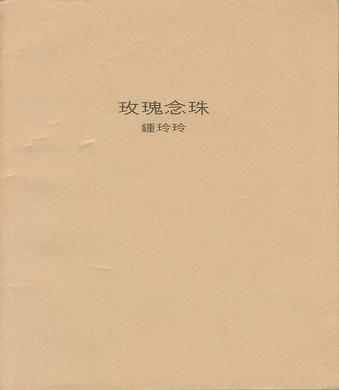
玫瑰念珠
《玫瑰念珠》寫到的,是青年文生的學習,陽桂枝、汪玫莉的遭遇,和徐良琴的寫作,雖然學習中的文生,為幫助還是拯救,感到困惑極了,但只要是真的,就是可予辨認,和充滿體味的人生,儘管陽桂枝在時中經歷的,是死與變容,但汪莉在長久的懸念中,但願慈愛與恩典,直至永遠,儘管徐良琴相信,文學作為情感教育的一種,始終是美好的,但必須多年以後,才能體悟,在我和我們之間,原是無分彼此的。 -

好黑
" 已經無法追究是甚麼原因,上大學以來,世界變得越來越輕飄飄的。一天在街上行走,忽然覺得大廈與身邊的行人都變得虛浮,甚麼也可能突然上升、消失,自己的身體彷彿也能隨時瓦解。這樣的時候,胡亂說一句甚麼都是絕對真實,同時又極盡虛假的。有些人說創作是為了表達自己,但我懷疑那個「自己」是否確切地存在,我倒希望那些有形的詞句、堅實的文字能填塞虛無的「我」。每篇小說倒是一個暫時的結構,能讓我撿拾亂七八糟的碎片,把一切重組成一種可見的形式。" -

白髮阿娥及其他
-

停車暫借問
這次的修訂範圍主要集中於三方面。 一是把方言的部分收拾一遍 二是將文義含糊混亂處略為理清理順 三是例行的撿錯字別字,其他盡量不多手亂改。不為了省事,實在是怕改壞了,用我現時的求好求正確的尺度,煞風景破壞天真未鑿。除非直接影響閱讀理解,否則即便有幼稚或不通,我寧忠於作品的原貌。 -

坐牢切勿拾肥皂
到底世界上真的存在所謂﹕“肥皂”定律﹖ 還是各地監獄都有向囚犯派發正確性侵犯指引﹖ 幹嘛每次在電影里犯人在洗澡﹐總是會俯身拾起掉在地上的肥皂時﹐被其他囚犯合力制服﹐然後雞姦? 這弄得我老在渴望身邊朋友之中能有人被捕﹐或幹脆認識個快要入冊之人。我就可以搭著他的肩膀叮囑﹕「進里面後﹐凡事要小心。洗澡時﹐肥皂一旦跌落﹐就記著千萬別彎身去拾。”」 原來我對世界﹐生命的許多認知與體會﹐并非源於現實﹐而是來自電影。電影啟發我之余同時限制扭曲了我﹐我在看完《芝加哥》電影版后才在倫惇看舞台劇﹐演律師的那位黑人演員相當精彩﹐可是我上半場卻看的輾轉反側﹐不是因為我有種族偏見﹐而是我得忙著把腦中的電影版扮演者﹐進行矯色和曬黑。 ——《坐牢切勿拾肥皂》主要是彭浩翔於二零零五至二零零九年間,在香港雜誌CUP、HIM、Pandaa等之專欄,及其個人網誌之文章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