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陆深处
这是一部相当诗意化的小说。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他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那一系列事情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惟有从她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

异乡人的国度
《异乡人的国度:文学评论集》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文学评论集,收入发在《纽约时报》或《纽约客》上的文论26篇,这些文论写于1986-1999年间。库切不光是被公认的经典作家,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兼通文理,学识驳杂,不亚于博尔赫斯。他的文学评论有相当的分量,那随笔式的文论很具亲和力和可读性。他不但论及了18至19世纪的作家如笛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还剖析了博尔赫斯、奥兹、莱辛等20世纪的文学巨匠。优美的文笔和较高学术价值使之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评论集。 -

福
《福》(Foe)是作家库切的第五部小说。这部小说是比较典型的后现代作品,与英国传统经典小说《鲁宾逊飘流记》有很强的互文性。可以说《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大胆反拨与颠覆。对《福》的解读有不同的版本,一些人认为《福》是“南非状况”的寓言,也有学者从女权主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福》以苏珊作为个体对事件的亲身经历,一种小历史去反拨那个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宏大历史。在对大历史的反拨方面,该书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展现一条解构历史的路径。 -

慢人
在这部提名2005年布克奖的新作《慢人》中,库切秉承了他一贯的语言风格,却在文体上收缩了故事情节的成分,加大了哲学思考的比重。这无疑使这部探索型远离了“讲故事”的休闲品位,走入了更加广阔而又弥深的思想领域。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老摄影师将如何面对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女护士及其家人和一个神秘来方的女作家?库切在这个简单的故事构架中并没有突出它的传奇色彩,更没有用桃色八卦的悬念挑逗读者的胃口。因为他关注的并非瓷娃娃般的爱情,而是相比这之下更有负重感的命题,诸如衰老、残缺、羞耻、死亡甚至超越死亡的轮回。在其代表作《耻》中,库切讨论了作为民族和种族意义上的非洲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与白种人共同背负的群体耻辱。 -

男孩
库切的自传体小说《男孩》和《青春》是两部各自独立而互有关联的作品,前者叙写主人公十岁至十三岁时在南非的孩童生活,后者是他大学毕业后到伦敦谋职的一段经历。《男孩》结束之前主人公跨入了中学校门,而《青春》开篇之际则是大学生活的尾声了,两者之间略去了一段很重的人生经历。保以闪开偌大一个空当,这事情颇费猜详。 关于这个男孩的故事还涉及其家庭的种种变故。老爸老妈秉性不同,角色各异,只是谁也没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还有可怜而执著的安妮阿姨,她让约翰见识了人生的无奈。这里所有的情节都带有天真而阴郁的色彩,且充满奇奇怪怪的幻想,然而这一切细琐之处背后却有着宏大的叙事意图。通过一个小男孩,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见证殖民者的文化帝国主义给南非社会播下冲突的祸根——库切借此铺衍本书的悲剧性语境,透过主人公内心的困惑,世事艰难的老生堂谈了人意料地演绎出一套全新话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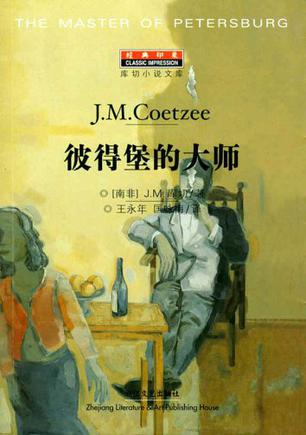
彼得堡的大师
《彼得堡的大师》在另一个向度上,库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人和其他作品的人物也邀请到1869年的彼得堡,让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地下室”、“火”等属于陀思安耶夫斯基话语的场景里,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中去。小说中,库切多采用现在进行时,并用他(he)来叙述,形成作品中的共时性。情节在共时性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自由行动处在一种关键时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库切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迫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正如巴赫金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些思想家式的人物:具有伟大而尚未解决的思想的小人物。那么,在《彼得堡的大师》中,库切创造了思想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这样,不仅是陀思安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具有开放的、鲜活的他人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拥有完全独立的声音,发出价值十足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说陀思安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的,那么《彼得堡的大师》是复调的复调。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以及那些有着特殊意味的场景 经过库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调,呈现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折射出丰富的寓意。 1971年,库切回到南非,后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其间,他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做过陀思安耶夫斯基专题。库切是喜欢实验的,也许在研究中,遗世独立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还引起了他的共鸣,一种慢慢相借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小说,当然用的是他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来表达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敬意。在对人的命题的探险历程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中,库切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是同行与对话者。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所经历的革命的俄国生活有着异形同构的特质。所以,库切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等待野蛮人》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彼得堡的大师》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彼得堡的大师》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彼得堡的大师》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