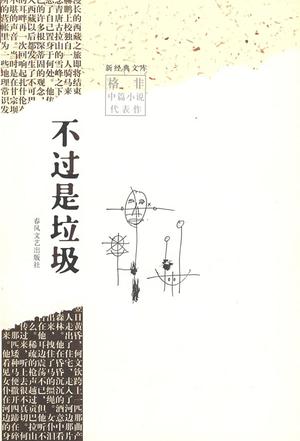边缘
格非
《边缘》作为格非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对他本人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为我们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保持如此绵长的沉默而惊讶不已。从90年度的《敌人》到92年度的《边缘》,格非几乎不着痕迹地完成了对既往艺术范式的全面突围,他不仅以清晰的时空结构和透明的情节线索消解了以往神秘晦涩的艺术倾向,而且还在对文本游戏色彩的抛弃过程中实现了风格由混沌向澄明的升华,并由此表现出了对“迷宫”式写作姿态的真正遗弃!格非无疑以其卓有成效的艺术努力和出人意料、判若霄壤的“艺术蜕变”,显示了作家超越自我的可能及其限度,并在此意义上对整个新潮小说界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提醒。“超越与澄明”既是小说艺术姿态的绝好总结,同时也更是小说主题和人生内涵的精妙概括,据此,格非为新潮小说指明了某种方向。 一 如果说格非的迷宫小说曾一度因其朦胧晦涩和危机四伏的神秘而令人望而生畏的话,那么一旦格非跨出迷宫的门槛其不期而至的清晰给予读者的欣喜也是不言自明的。尽管《边缘》以一个老者弥留之际的灵魂坦露为线索叙述故事,小说时空依然变幻、飘忽不定,但众多跳荡的故事片断和人生画面不仅具有可重组性,而且各自也具有逻辑联系,这就使《边缘》的故事形态具有了整体上的统一性和透明性。小说主人公是“我”,因此“我”的人生经历也正成了这部小说的故事主体,而从“我”的视角出发,小说又平行地展开了仲月楼、徐复观、宋癫子、杜鹃、小扣、胡蝶、花儿等人物的故事,彼此互为交织又互为对比共同构筑了整部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主题结构。具体地说,“我”的人生故事又呈现为三个阶段: 其一,少年麦村阶段。“我”的记忆开始于“那条通往麦村的道路”,而这条光秃秃的实际上“包含了我漫长而短促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的道路也正是“我”人生和故事的开端。通过那次母亲眼中的“错误”迁徙,“我”在麦村的童年生涯揭开了帷幕。而母亲对麦村阴雨连绵的天气和弥漫的空气中的稻草气息的抱怨以及对往昔时日的刻骨留恋也感染了“我”,“我”日益被一种颓伤和忧郁的情绪所包围。父母之间的隔膜和隐隐的仇恨也时时加剧着“我”的孤独和寂寞。父亲的病死和母亲与徐复观私通的场景更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和伤害。“我”眼中的麦村到处充满了灾难和死亡的气息,尤其当我目睹了宋癫子姐姐的驱鬼仪式、花儿莫名其妙的吊死和母亲的临终叫喊之后,不但一种对于生命经久不散的忧伤无法排解,而且“我”的身体也开始向生命的边缘滑行。“我”患上了越来越重的失眠症和梦游症,最后,虽然徐复观以“大粪”治好了“我”的病,但“我”对于麦村的恐惧和逃离已是无可避免。无论是母亲的死亡,还是和杜鹃的结婚、和小扣的私通都无法阻挡“我”突围而出的决心。在“我”的印象中,麦村正是借助于仇恨和恐惧完成了对“我”人生的最初洗礼和放逐。一方面,“我”无法摆脱弥漫于麦村各个角落的仇恨和敌意。如果说徐复观对“我”的仇恨源于对母亲欲望受挫后的报复心理、母亲对小扣的仇恨源于女人之间近乎天生的嫉妒的话,那么宋癫子对“我”的仇恨以及父母亲到麦村后的相互仇恨则似乎莫名其妙。另一方面,“我”的童年稚拙而脆弱的想象中又充满了对于麦村世界的深深恐惧。“我”的幻觉中“窗外的世界浩瀚而不可理喻,它奥妙无穷,令人战栗”,并最终凝聚为一种恐惧的征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麦村的逃离,正是一次对灾难和痛苦的抛弃与告别,是一次精神涅盘般的自我拯救。只不过,此时,“我”忽视了自己与麦村似乎命定般的联系,因而没有意识到正在踏上的只是一条虚妄的救赎之途。 其二,军旅生涯。对于“我”来说,信阳的军校生活无疑揭开了人生的崭新一页,但这一页尚未完全打开却又急遽地合拢了。“在充满火药味的战争气息”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与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灾难和罪恶狭路相逢。虽然,对于军校大兵奸淫乡村女子丑剧身不由己的目睹与参与使“我”度过了三个月的禁闭生活,那几个大兵也终于被处决,但惩罚并不能真正消泯那笼罩和折磨“我”灵魂的罪恶恐怖,这种恐怖几乎一直伴在“我”此后的人生路途上。军校毕业后,“我”上前线投入了战争,并把战争视为“我的身体对于沉睡而无所适从的心灵的一次小小的拯救”。然而,战争却以其残酷和荒诞对人与生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戏弄,并彻底摧毁了“拯救”的妄想。一方面,战争以接二连三的死亡作为成果表现出对生命最大程度的轻蔑和不屑一顾。如果说霍乱伤员被活活烧死,仲月楼关于这件小事的解释多少还能使“我”信服的话,那么当“我”所在的三团“也许只是为了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或者仅仅是为了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而在进攻中“象被收割的庄稼一样一排一排地倒在河边”,大规模的潜伏部队竟无动于衷时,战争的残酷本性和狰狞面目则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