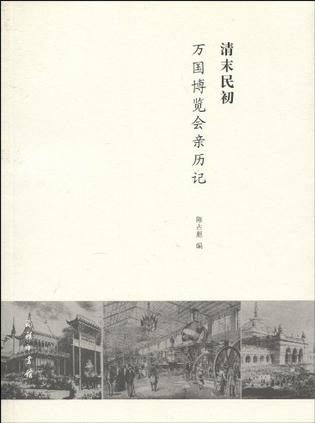博覽會的政治學
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
【內容簡介】
世界,一直被「發現」。
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大發現」,其實是一種視線(まなざし〔gaze〕)的發現,歷時幾個世紀的擴張,編成一套完全覆蓋地球的視線,而歐洲則恆常占據視線主體的特權位置,將博物學視線場域當成新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機制親自演出,而博覽會的時代也就出現在這個時刻。
本書的觀點在於捕捉人們聚集於博覽會的體驗史。亦即,在博覽會的場域中,誰被吸引?看見什麼?觸發什麼?人們的經驗結構是否發生變化?博覽會從一開始就是由國家和資本共同演出、人民被動吸引和接受的制度性存在,但博覽會的經驗結構絕非這些編劇企畫者所能片面決定,移動自己身體前去參加的人,仍是這個特殊經驗的最終表演者。過去將博覽會定位在技術、設計與工業發展史的一環,以發展史及風格演進來看待其角色,然而博覽會是個複雜交錯的多層次文本,單以新工業技術展示場的角度加以解讀,顯然有所不足。
於20世紀邁向巔峰的博覽會,融合了帝國主義、消費社會與大眾娛樂三個要素,不但是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制,也是商品世界不停誘惑消費者的廣告機制。本書一方面以「帝國」的展示、「商品」的展示及「見世物」三個主題作為博覽會的縱軸,另一方面則以歐美萬國博覽會和日本國內博覽會的參照關係為橫軸,試著解明博覽會如何動員並重新整編現代大眾的感覺和欲望。
【台灣版序文】
〈致台灣版讀者〉
吉見俊哉
拙著《博覧会の政治学》經由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四位教授的努力在臺灣出版,我由衷感到光榮。1992年本書在「中公新書」書系出版,有幸獲得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美術史等領域內關心博覽會、博物館、展示歷史的諸多研究者和學子閱讀。先前在2003年已有韓國版譯本刊行,現在再有臺灣版譯本問世,使本書能夠呈現給更多亞洲的讀者,令我十分欣喜。
大約二十年前本書甫出版時,日本已經走過1980年代末期,雖然泡沫經濟已走到尾聲,卻難以預料長久之後會是如何嚴竣的未來。場景回到本書初面世的1992年,三年前有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一年前蘇聯垮臺,時代由「冷戰」旋即轉變為「後冷戰」,日本社會將被迫轉向何方,仍無從展望。因此,日本在隔年1993年出現非自民黨執政的細川政權,很快就短命終結,之後政治與經濟的混沌迷亂不僅一直持續,而且愈加深刻。
談些與博覽會有關的事,那一年剛好也是西班牙塞維亞(Serville)舉辦萬國博覽會。本書終章提過,我認為以「紀念新大陸發現五百年」為名而開辦的塞維亞萬博,應該是「博覽會時代」終了的象徵。之後漢諾瓦萬國博覽會的大筆赤字、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混亂一場,其實都是時代潮流的大勢所趨。「博覽會時代」終了,就是「發現的時代」終了,帝國主義的視線擴張到整個地球,將世界編入符號秩序中加以排列,歷經數個世紀後也已終了。現代一直不斷在終了——我們對現代的信心逐漸在動搖,卻渾然不知再來的歷史要如何展開。
從那時算起,二十年很快就過去了。其間日本經歷過阪神淡路大地震、奧姆真理教事件;經濟陷入長長的停滯、政治走進重重的亂局;新自由主義被貫徹實行、社會安定性基礎被連根拔起,這是日本前進的方向。社會的變化也波及到人們的意識,2005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三十五年後舉辦的「再一次的日本萬國博覽會」,不再可能像那樣成為代表經濟成長期的國家大事了。
日本在此二十年間,正是領受「崩壞」與「停滯」反覆發生的「失落時代」。但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從1990年代以後的二十年間非但未曾「停滯」,反而是在「躍進」。整個1980年代,韓國與臺灣有民主運動在普及,各國也都能看到經濟在發展,首爾並在1988年舉辦奧運會。1990年代後半,變化的中心逐漸移向中國,在東亞的整體秩序裡,中國的比重也不斷增加。反觀日本,在20世紀前半是東亞帝國並將周邊國家殖民化,20世紀後半是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到了21世紀,日本已不再扮演如20世紀的特別角色。
今年,2010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已四十載,上海就要舉辦中國首次的萬國博覽會了。上海萬博與兩年前的北京奧運是成雙出現的事件,這種組合很像四十幾年前的東京奧運和大阪萬博,也很像二十幾年前的首爾奧運和大田萬博。合稱東北亞三國的日本、韓國、中國,恰好以間隔二十年的速度相繼利用「奧運」和「萬博」作為經濟成長的象徵。這些組合的比較研究,期望今後也能由相關的年輕研究者以更好的方法進行。如果參考日本的過程,大阪萬博經歷四十年歲月方成為「過去」,那麼真正的歷史研究工作也才正要開始。
本書原是我某個研究計畫的一部分,主要探討19世紀末日本國家的事件演出與民眾意識自發動員的關係。在1980年代後期,我關注的議題除了本書處理的內國博覽會,還包括中小學的運動會、明治天皇的地方巡行、近代的伊勢參拜(團體旅行)等等,亦即現代國家將國民當作一般大眾而組織起來的各種儀禮性活動。我試著藉由這些活動解明,常民的日常意識及身體感覺,與國家的身體戰略其實有所關聯。
這種關注延續自我的處女作《都市のドラマトウルギー——東京.盛り場の社会史》(弘文堂 1987,文庫版 河出文庫 2008),書中處理了都市鬧區集結人群的意識與資本和國家的空間戰略之關係。這是我在1980年代後半的嘗試,以過去都市空間為基礎,討論集體儀式與現代權力之間的動能,並放到國民國家或帝國之類的更大脈絡來思考。
經過這樣的思考作業,繼之浮現出來的主題,就是博覽會與殖民主義的緊密關係。適巧1980年代後半,海外也出現許多以殖民主義意識形態來探討19世紀末萬國博覽會的重要著作。由於這些研究行動的先行,本書的思考因而聚焦於更為早期的問題,亦即在現代日本的博覽會中,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如何再現的問題。這種觀點在本書出版後的1990年代後半開始急速暈染開來,而今博覽會與帝國主義的各種討論,已有諸多優秀的研究者在各個領域從事精緻的分析。
本書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博覽會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本書雖以博覽會這種具體的群集空間為焦點,但更在思考博覽會與國民國家、帝國主義及消費社會之間的關係。現代都市出現過的無數視覺消費空間—例如百貨公司、主題樂園、博物館、廣告,其原型就是博覽會。由這個觀點出發,本書分析了歐美的商業主義如何滲透到博覽會,以及日本的百貨公司和報社何以要主辦博覽會。從今天看來,這種觀點可說是一種「殖民地性的現代」,是涉及摩登女郎、消費文化、殖民主義、商業主義等各種主題的研究。
這二十年來,伴隨社會的鉅變,學術界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對我本身而言,1990年代下半之後的最大變化,是與許許多多亞洲各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廣大交流,以及自己執教大學裡學生國籍的多樣化。本書寫作時是以概念上的殖民主義作為問題的切入點,我則尚未與亞洲各國友人共享相同的問題意識或共同進行研究。然而今天,我自己的疑問已深切與亞洲、太平洋、美國、歐洲的友人所共享。當然,在研究日本的脈絡時,我也不再認為只以日本當作唯一的核心對象就足夠,也不再視之為不證自明的前提。
在這種全新的跨國性知識文脈下,本書或許還能因開啟一些新的批判性洞察視野而有所貢獻吧!就如前述,日本、韓國、中國等,有可能針對歌頌經濟成長而舉辦的國家慶典進行比較研究。果若如此,本書的觀點或許多少有所用處。對殖民時期曾在臺灣、朝鮮半島、滿洲舉辦博覽會的相關研究,也可能是本書研究的延長線。
我也期待本書的讀者,不要只將目光直接對準博覽會的研究。除了博覽會,博物館、美術館、百貨公司、電影院、劇場、書店、圖書館等各種現代的(=modern)空間,都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大量出現在東京、大阪,也出現在首爾、臺北、上海、香港等亞洲都市。這些空間也可能以稍稍縮小的規模,出現在同時代的地方性都市,甚至以移動的形式出現在農村的學校、寺廟及神社。若以此來思考現代性空間,最重要的關注點,應該就是群聚的人們與空間所交織的視線集體組織化的歷史。在博覽會;在博物館和美術館;在電影院、百貨公司、圖書館,走過「現代」的人們體驗了什麼樣的視線變化?在這種變化中又如何被新的社會集體性所組織起來?這些問題,實已超越了美術史、電影史、文學史、建築史等既存學科領域的界限。就我本身的立場,我認為新的文化史就是最廣義的媒介理論或文化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當然這種說法也可以有不同見解。
然而,我仍想對那些不同見解提出我的期待,希望本書讀者參考本書的提示,不要完全只使用自己在「美術史」、「日本史」、「建築史」、「電影史」、「媒介史」等學科框架內熟習的知識,而要試著跨越框架並試著培養打破框架的攻擊意志。
對人們的經驗進行重新整編的,不只是博覽會、美術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作為現代視線的空間;大學與各種學術性知識的機制(包括這本翻譯書本身),也都是作為現代視線場域的一部分而被組織起來。歷史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文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現代性的學術體系,不會永遠維持不變的內容,傅柯(Michel Foucault)早已經清楚指出這點,它們是透過現代媒介與論述秩序的組織過程而產生。
是以《博覽會的政治學》的「政治學」,就不是造成政治影響力那種意義下的政治學,也不完全是操弄博覽會那種微觀政治學意義的政治學。當然,後面這種微觀政治學的觀點是貫穿本書最重要的部分,甚者,能夠記述微觀政治學的論述場域,亦即各種學科領域的結構,也都與博覽會一樣是種現代視線的秩序。探討博覽會,也就是在探討你我身邊的許多事物,例如身處的大學、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地點,以及作為教師、學生、讀者、觀眾、消費者等身分。這並不是要否定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的意義,而是要先打造一個「去領域」的基地 ,以將知識結構由內部顛覆、相對化乃至提出全新的認識觀。
今日,網際網路與各式各樣的數位媒介,對於大學、圖書館、博物館,乃至書店與百貨公司等現代性的空間秩序,莫不帶來劇烈的變化。所有現代視線的空間,在這個巨大的數位衝擊下幾乎也都腳步踉蹌。在21世紀初,我們不只生活在冷戰變成後冷戰的全球板塊移動(Global Shift)中,我們也體驗到現代性視線空間變成後現代資訊空間的數位板塊移動(Digital Shift)。這麼看來,博覽會這樣的現代性空間,難道只能是歷史性分析的對象嗎?本書由初版刊行至今已經歷二十年,現在的我對本書提出的問題,一方面因身處中國崛起的東亞歷史中,另一方面則因身處面對新式數位衝擊的現代性空間全體變化中,確實感到有重提新架構的必要。
如果前述的問題意識,能因這次臺灣版的刊行而獲得更多共同思考東亞現代性的讀者之助,實為個人之所幸也。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