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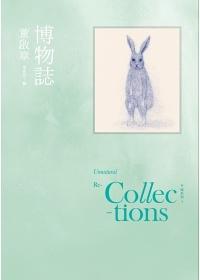
博物誌
向《山海經》、《博物志》、《搜神記》、《聊齋誌異》致敬! V城系列四部曲之《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之後 各大文學獎、好書獎得主,香港知名作家董啟章,聯合香港插畫家梁偉恩跨界跨域首度合作 以文字和插圖呈現21世紀博物學大全 董啟章的新作《博物誌》,其構思來自於中國傳統志怪小說如《山海經》、《博物志》、《搜神記》、《聊齋誌異》等,但它的創意和想像力之豐富巨大比起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全書以極短篇或筆記小說方式,通過人和物的關係來寫香港V城,人和自然物(也有少量人為物)的交感並生,開展出變化無數的「人—物」關係,敘述了香港V城內77個不可思議、離奇詭譎、但又極富人性和人情的故事。 《博物誌》既是董啟章V城系列的完結篇,在書寫上更像是一本《怪物大全》。 何謂怪物?在董啟章心目中的「怪物」,永遠是異質事物的混合體。人其實也不是單一的,而是異質的,所以人本身便已經是作者想像中的典型「怪物」了。在《博物誌》裡,77個故事中的「人物」,是人和物的結合,又或者物在人中、人在物裡,人和物互為表裡,把人和物的關係推到更想像性和寓言性的層次。怪物通常被認為是異常的,但怪物之怪又是那麼的順理成章。怪物有怪物的邏輯和美學。而怪物又往往和鬼魂靈異之事相提並論。鬼者,人之死後形態也,其實也是人之另一面。鬼怪世界和人的世界互為鏡像,同樣有其可解和不可解之處。 香港插畫家梁偉恩特別為本書繪製77幅具有代表性意義的黑白插畫 小說家VS.畫家,除了對中國傳統志怪小說致敬 也是緬懷昔日香港的人與物,或揣想未來香港的人與物,更是小說諧仿怪物的有趣實驗。 從《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到《博物誌》,董啟章這位V城書寫者,採用了「未來的考古學」,把香港V城的未來當成已經發生的事實,把香港V城的過去變成未發生的可能,在書寫上已被肯定是香港文學的奇觀。 -

愛蓮說
「我寫《愛蓮說》完全是因為有話要說。不過倘若仔細思量,情況或許兩樣,因為有許多話其實不必說,如果一定要說那就應該好好的說。」 -

夢華錄
潮流來又去,繁華夢未醒; 入時的造作,成就過時的美學。 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紅樓夢獎決審團獎、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得主、 香港知名作家董啟章99個短篇,說盡物事人情 獨立漫畫家李智海33幅插圖,繪出浮世風景 時間是1997年以後 1998至1999年,晚期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後的香港 香港已回歸中國大陸 50年不變的諾言 在世紀末的華麗前變色 成為升斗小民的茶餘飯後話題 香港知名作家董啟章繼V城系列1《地圖集》後,為香港城市寫下V城系列2《夢華錄》 《夢華錄》體例近似於筆記小說或極短篇,寓言的寫法,風格近似帶點黑色的瘋言誑語, 收入了99個1999年香港的流行事物, 香港知名獨立漫畫家李智海特別為《夢華錄》繪製33幅具有重要意義的漫畫插圖 人的故事,物的故事,異人異物,日常生活與奇想 繁華的物質世界,孤寂的難以捉摸的感情,通過人和物的關係來看香港 《夢華錄》寫盡了物欲洪流中,一切事物不一定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作者董啟章反而逆道而行,通過小說書寫把香港社會中大量生產的、無個性的、非人的商品化為己用,成為獨特的生命體驗印記。新與舊,流行與退潮,先進與落後,當時的可嘆與可美,今天可能如小丑之可笑可憐,故事主角全都是年輕男女,性格乖僻怪誕,或平凡無奈,對於在香港的生存都是懷有一種痴狂。 《夢華錄》每篇小說文字不及千字,幾乎交代整個人的成長,但又寄託於幾個代表性的生活切片,環繞著一件「物品」開展其存在意義。 -

蝙蝠與告別者
隨《明報周刊》2298期附送的二十三頁別冊。 -

我城
本書為西西傳誦二十餘年之出名鉅著,風格獨特,無論結構、筆路、章法,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其中寄託著青年的開放、進取、和各種成長之潛力充滿可能性,則小說本身之形式與內容也步趨呼應,鯱斷摸索、調整,構成了文學閱讀經驗中知性與感性的最大挑戰。洪範版《我城》經作者增補萬餘言,為最完整之新版本,有別於前此付梓者。 -

烈佬傳
黃碧雲在《烈佬傳》的封底文字這樣寫著: 小說叫《烈佬傳》,對應我的《烈女圖》。小說也可以叫《黑暗的孩子》,如果有一個全知並且慈悲的,微物之神,他所見的這一群人,都是黑暗中的孩子。小說當初叫《此處那處彼處》,以空間寫時間與命運,對我來說,是哲學命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裡面,人的本性就是命運。時間令我們看得更清楚。 我曾經以為命運與歷史,沉重而嚴厲。我的烈佬,以一己必壞之身,不說難,也不說意志,但坦然的面對命運,我懾於其無火之烈,所以只能寫《烈佬傳》,正如《烈女圖》,寫的不是我,而是那個活著又會死去,說到有趣時不時會笑起來,口中無牙,心中無怨,微小而又與物同生,因此是一個又是人類所有;烈佬如果聽到,烈佬不讀書不寫字,他會說,你說甚麼呀,說得那麼複雜,做人哪有那麼複雜,很快就過---以輕取難,以微容大,至烈而無烈,在我們生長的土地,他的是灣仔,而我們的是香港,飄搖之島,我為之描圖寫傳的,不過是那麼一個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