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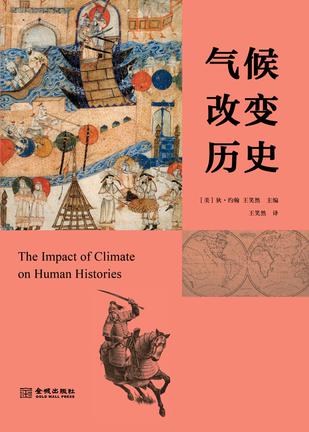
气候改变历史
★ 全球著名史学家亨廷顿、许倬云等关于气候改变历史的代表作,首次结集,独家引进出版。 ★ 成吉思汗征服了欧洲,最终却被气候征服;17世纪中国(明朝)和世界的普遍危机,气候居然是罪魁祸首……大师条分缕析,讲述气候角度的世界史。 ★ 雾霾等恶劣天气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本书将给予现代人以历史学家的思考与启迪。 ★ 历史研究者、历史院系学生、历史爱好者,了解世界环境历史最新成果的必读书。 环境历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界限,让人回归到自然中,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人类历史。《气候改变历史》一书遴选了气候影响历史的代表性文章,话题涉及全球范围。以环境历史的开山人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起点,分别介绍世界气候的历史变化、气候对世界格局和文明形成的影响、气候对西方殖民历史的影响、中亚少数民族的大举迁移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在复杂性社会瞬间崩塌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等。本书入选作者,除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学大师亨廷顿、汤因比,其他人亦称当代重量级的环境历史学家,特别是约翰•F•理查兹(John F. Richards)、阿尔弗烈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马立博(Robert Marks)几位,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台湾学者许倬云,都在环境历史上富有建树,他们叙述历史的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这本书的选译宗旨在,向读者展现一个更为新颖、更为宽广的史学天地,让历史爱好者可以通过环境历史这一全新角度,去重新认识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何兹全文集(全六册)
本书共收有何兹全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秦汉史略》、《三国史》、《中国文化六讲》、《爱国一书生》等六部专著和散见各报章、杂志的论文数百篇,集中了作者一生的学术成就。何先生是我国魏晋封建说的创始者和代表者。 -

中国通史选读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本书拣选春秋战国的历史,注目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本书为修订版,增添了一篇关于历史社会学学术脉络的解读。 -

楚亡:从项羽到韩信
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 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书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