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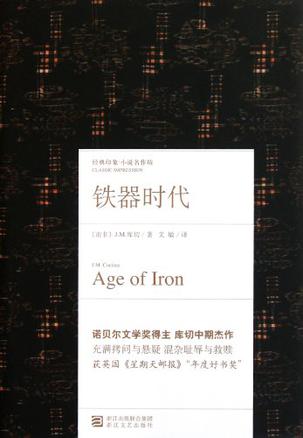
铁器时代
的确,库切——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作品——常常会让我们想到铁。他像铁一样冷酷,坚硬,不动声色。但与其说这是出于天性,不如说更是出于需要,出于一种抵抗这个世界的需要。通过文学和虚构,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库切式的抵抗风格,而这本书就是这种风格最成熟最炽烈的表现:库切的中期杰作——《铁器时代》。一起来翻阅《铁器时代》吧! -

内陆深处
这是一部相当诗意化的小说。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他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那一系列事情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惟有从她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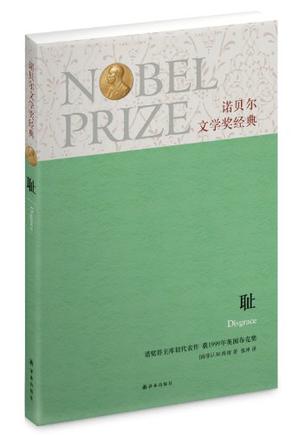
耻
瑞典学院前常务秘书贺拉斯•恩达尔作序推荐 独家收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受奖词 本书《耻》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南非的社会矛盾和往日的种族冲突,触及了当代对浪漫激情与伦理道德的态度。“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他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库切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为南非文学大师库切的重要作品。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与一位女学生的艳遇而被逐出学界。他躲避在25岁的女儿露西的农场里,却无法与女儿沟通,还得与从前不屑一顾的人打交道,干从前不愿干的活。不久,农场遭黑人抢劫,女儿被强奸…… 我喜欢把我的写作意图隐藏起来,而要创造一种情景,让受众自己去深思、去做道德思考或自己下结论。 ——库切 库切小说的特色,包括精致的结构、意义深长的对话,以及精彩绝伦的分析。同时他又是个追根究底的怀疑者,对西方文明罔顾人性的合理化企图以及粉饰太平的道德观,提出无情的抨击。他基于知性,力求诚实,破坏了一切抚平伤痕的可能,并杜绝任何卖弄忏悔与认罪的廉价戏剧。 ——瑞典学院 -

耻
《耻》是一本极具可读性,且从内容到寓意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层次的作品。主人公卢里在种族、性、中年、亲情种种漩涡中载浮载沉,小说命名“耻”,其为“道德之耻”(卢里的数桩风流韵事所指的道德堕落),“个人之耻”(女儿遭强暴抢劫),“历史之耻”(身为殖民者或其后代的白人最终“沦落”到要以名誉和身体为代价,在当地黑人的庇护下生存)。小说反映了南非的社会矛盾和往日的种族冲突,触及了当代对浪漫激情与伦理道德的态度。 -

青春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青春》不同凡响,写法特别。它并非采用这类作品常见的第一人称途述,主人公也是一位名叫约翰的年轻人,但库切总是称之为“他”。库切写“他”十九岁到二十四岁几年间的生活经历,一个南非大学生跑到伦敦做了计算机初级程序员,朝九晚五的公司职员,饭碗不用担心,却还是郁闷。这个岁数的年轻人不是意气风发就是躁动不安,却玩不出轰轰烈烈的名堂,由于生性缺少热情,干不成大事也惹不出乱子。他也需要被爱抚的感觉,但性爱从来没有给他带来生命的光辉,只是在吞噬时间和精力……这种内敛的性格,这般平淡无奇的生存状态,还能做出什么样的文章呢?可是,库切就有这样的本事,一段春梦无痕的人生就让他写得楚楚动人。他把年轻时的自己作为他者来观照,再度审视青春的彷徨之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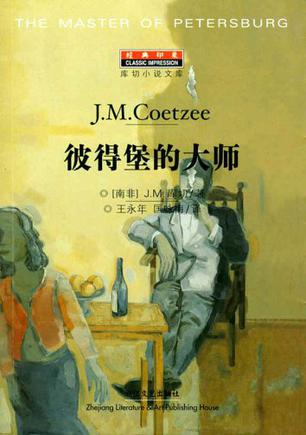
彼得堡的大师
《彼得堡的大师》在另一个向度上,库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人和其他作品的人物也邀请到1869年的彼得堡,让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地下室”、“火”等属于陀思安耶夫斯基话语的场景里,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中去。小说中,库切多采用现在进行时,并用他(he)来叙述,形成作品中的共时性。情节在共时性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自由行动处在一种关键时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库切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迫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正如巴赫金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些思想家式的人物:具有伟大而尚未解决的思想的小人物。那么,在《彼得堡的大师》中,库切创造了思想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这样,不仅是陀思安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具有开放的、鲜活的他人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拥有完全独立的声音,发出价值十足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说陀思安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的,那么《彼得堡的大师》是复调的复调。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以及那些有着特殊意味的场景 经过库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调,呈现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折射出丰富的寓意。 1971年,库切回到南非,后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其间,他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做过陀思安耶夫斯基专题。库切是喜欢实验的,也许在研究中,遗世独立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还引起了他的共鸣,一种慢慢相借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小说,当然用的是他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来表达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敬意。在对人的命题的探险历程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中,库切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是同行与对话者。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所经历的革命的俄国生活有着异形同构的特质。所以,库切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等待野蛮人》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彼得堡的大师》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彼得堡的大师》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彼得堡的大师》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