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见古代
一本有趣的书,只言片语便把我们拉进古今交融的世界。学问居然做得这么好玩。——吴思 几百年黄土地上动人的声音,靠一个北京知青,找回了被埋没的形体。——史铁生 作者在陕北多年,发现陕北方言中保留有大量的古代词汇。作者花费十年时间,翻阅了许多古籍,找出陕北方言中古语遗存的来源。书中不仅用古籍来印证方言,也通过方言展示了陕北特有的民俗。 本书记录的陕北特色口语词语,有3900条。记录的原则是作者自己听到的、作者个人生活中用到的,并且普通话口语不用的词语,书里看到的不算。书中收录的陕北词语和语句,一些是作者跟延安、榆林等地的干部、职工和农民聊天所得,很多则出自余家沟村的几十位农民之中。书里的陕北词语,作者依自己对陕北生活的感觉,分为“陕北的古代人称人身词汇、表述行为的陕北古老动词、陕北日常生活中的古人词语、陕北古老的人际交往词语、有关婚丧信仰精神寄托的陕北古词、陕北关于天地自然的古老用词、陕北话里的古代虚词”7个方在,和“亲属,叫了一千五百年的‘大’”、“劳作:造字之前‘耕’就叫‘耤’等42类,不合方言调查规范分类。作者还将所拍照片230多幅插在文,以便帮助了解词义,或帮助了解陕北。文后附有拼音索引和笔画索引。 -

最后的远行
中央台的原生态民歌唱响大江南北,大西北原生态小说会让人回味无穷。 本书为作者的“大西北三部曲”第三部,是一部集传统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于一身,具有极强可读性与文学欣赏价值的长篇力作。小说以一纸民间契约“回头约”为契机,展现了一具女尸被从坟墓里盗出,在高原古道上经过七天七夜的奇异行程,最后被送回前夫身边的故事。 那静静地伫立于天宇之下的,那喧嚣于时间流程之中的,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的歌声的,是我的陕北,我的亲爱的父母之邦吗?哦,这一块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土地,这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产物,这隶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中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这个黄金高原。 哦,陕北,我的竖琴是如此热烈地为你而弹响,我的脚步是如此地行色匆匆,你觉察到我心灵的悸动吗?你看见我挂在腮边的泪花吗?哦,陕北,我以儿子对于母亲一般的深情,向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的你注目以礼。你像一架雍容华贵的太阳神驾驭的天车,威仪地行进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的流程中。你深藏不露地微笑着向前滚动,在半天云外显露着你的身姿,芸芸众生像蚂蚁一样出没在你的庞大的支离破碎的身躯上,希望着和失望着,失望着和希望着。哦,陕北! ——引自《最后一个匈奴》 传统在消失,古典精神在消失,昨天的文化在消失。张家山这样的人物,也许是游荡在高原的最后的骑士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孩子们大约只能从老祖母讲的童话中,见识这一类人物了。 这是一个大智慧,一个大幽默,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他的胸膛里,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善良”。因为这个,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一层苦涩的意蕴。 张家山这个人物,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是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高贵而善良,精明又愚蠢,都试图怀着中世纪梦想,去匡正社会。只是,较之唐·吉诃德,我们的张家山的时代,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瘦骨棱棱的、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因此,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圆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 “今天,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姑娘们翩翩起舞,大家都在传递着一个动人的消息:他们中有一个人要去出发,征服世界了!”——这是人们,用给唐·吉诃德的话。如果人们同样地将这话用给张家山,我将感激他。 ——引自《最后的民间》 注:本书为作者的签名版。 -

最后一个匈奴
《最后一个匈奴(绘图典藏版)》是一部高原的史诗,陕北这块曾经让匈奴民族留下深深足迹的土地上,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主人公一家三代人,背负着历史的重负繁衍生息,艰难生存。他们见证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坎坷命运,也见证了红色革命的火种在此保存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历史。新时代来临之际,作者依旧在这里寻觅那个古老民族的遗踪? -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为路遥的中短篇小说全集,收录中短篇作品十八篇。包括《基石》、《优胜红旗》、《父子俩》、《不会作诗的人》、《在新生活面前》、《匆匆过客》、《青松与小红花》、《惊心动魄的一幕》、《月夜静悄悄》等。 -

最后的民间
中央台的原生态民歌唱响大江南北,大西北原生态小说会让人回味无穷。 《最后的民间》是我国著名作家高建群继《最后一个匈奴》之后推出的“大西北三部曲”的第二部,原名《六六镇》,该书初版于1994年,当时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此次作者将它重新修订,易名出版。 小说主人公张家山在六六镇上开办民事调节所,为周围百姓调解民事纠纷为主线,展开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小到夫妻不合,偷鸡摸狗,招夫养夫,大到“心脏开花”开棺验尸的人命大案,将陕西农村发生的奇人奇事用张家山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串在一起,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勾勒出了一幅原生态的人类生存图景,被业内外人事称为原生态小说。 张家山的前庭饱满,四阁方圆,相对应的,后脑把子很平。陕北人的这种头型和脸形,一半的原因得于遗传,一半的原因得于后天的抚弄。孩子出生后,到满月这一段时间,家长要给他的脑后枕一个用小米缝制的枕头,头的两边再放两个,令头不要乱动。那两条腿,则用绳子捆紧。这样一个月下来,脑把是平的了,额颅则高挺起来,两条腿则一生都是笔直的。陕北人走到人面前,有一种“高贵”的感觉,这与他们月子里的这一番抚弄,不无关系。 张家山的大脸盘子,大约与匈奴人有关。我们知道,匈奴人在陕北这块地面上,留下了深深的踪迹。而他那大鼻梁子,则与党项人有关。陕北高原在一个时期,曾是这些从青海过来的党项人的老巢。而在西夏王朝灭亡后,相信有不少的流民重新回到这里。据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有三十多个游牧民族从这块地面潮水一样漫过。所以一张陕北人的脸,就是一部陕北高原史,一部仍然鲜活的二十四史。 张家山那大鼻子,在年轻的时候大约生过螨虫。如今连螨虫也不再光顾这一张老脸了,或者换言之,这酒糟鼻子好了,不再红了。但是,那个蒜头上还有一些痕迹,而鼻子以至整个脸面,毛孔很粗,见两口酒以后,发红发亮。 他的嘴很大,正是老百姓说的“男人嘴大吃四方”的那种。那嘴里长着一个大舌头,这大舌头正是为“说白”“道黑”用的。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满嘴跑大舌头”。不过小说中“红嘴白牙”这句话没有说准,因为在我们的小说所写的这个年代里,张家山的嘴里,已经没有几颗牙了。 他还长着两只招风大耳。 那张家山的服饰,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他当过村干部,所以这上衣通常会有个口袋,那口袋上还会有一支笔。这笔用不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着,以示和别的拦羊老汉之类,有所区别。陕北人的服饰,还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北京知青来了以后。这变化反映在张家山身上,是在脚,那脚上的那双鞋,知青叫它“懒人鞋”。 不过张家山在年轻的时候,穿过一件叫“百衲衣”的上衣。那衣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棉袄。但是这棉袄,是像纳鞋底一样用倒勾针的纳法密密匝匝地纳过一遍的。这种衣服实受,一件要穿人老几辈。用它背柴,不怕挂了,耕地累了随便往地上一个连身躺,也不怕脏。时代不同了,这衣服不要说穿,现在连见过它的人,恐怕都不多了。 张家山这个人物,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是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高贵而善良、精明又愚蠢,都试图怀着中世纪的梦想,去匡正社会。只是,较之唐·吉诃德,张家山的时代,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连瘦骨嶙峋的、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因此,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深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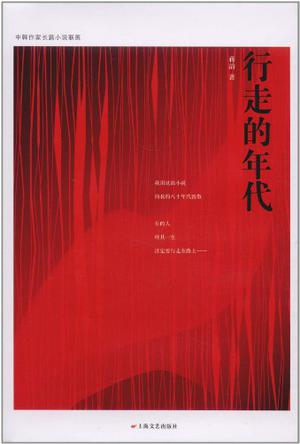
行走的年代
我用这部小说向我的八十年代致敬。对我而言,八十年代永远是一个诗的年代:青春、自由、浪漫、天真、激情似火、酷烈,一切都是新鲜和强烈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同时,它也是一个最虚幻的年代,因为,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 有的人终其一生注定要行走在路上。他们是我们的翅膀。 ——蒋韵